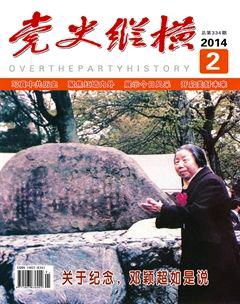抗美援朝第六次戰(zhàn)役緣何撤消
夏明星+肖鵬+鄭麗霞
1959年8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彭德懷,“會議對彭德懷揭發(fā)和批判的問題是極其廣泛的,從平江起義的思想動機到廬山上書的政治目的;從抗日戰(zhàn)爭戰(zhàn)略方針的貫徹執(zhí)行到1958年炮擊金門時的組織指揮;從紅一、三軍團的關(guān)系問題到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活動等等,無一不加以追查和批判。”其中,也涉及到抗美援朝戰(zhàn)爭。有人說,彭德懷擅自制定了抗美援朝第六次戰(zhàn)役計劃,“違背了毛主席確定的打小殲滅戰(zhàn)的方針,脫離了當時我軍的實際,‘搞左傾軍事冒險,并以此定為彭總‘與中央對立的罪狀之一。”時至今天,彭德懷冤案雖已平反,但關(guān)于第六次戰(zhàn)役仍然眾說紛紜。筆者通過搜集大量資料,冀望還原這段歷史真相。
斯大林首先提出抗美援朝的第六次戰(zhàn)役問題
從1950年10月25日到1951年5月21日,經(jīng)過抗美援朝連續(xù)五次戰(zhàn)役的較量,中國高層領(lǐng)導人逐漸認識到:美英軍不易對付,朝鮮戰(zhàn)事必須從長計議。
1951年5月26日,正當中國人民志愿軍結(jié)束第五次戰(zhàn)役收兵轉(zhuǎn)移之時,毛澤東總結(jié)抗美援朝連續(xù)五次戰(zhàn)役的經(jīng)驗,致電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提出了對美英軍打小殲滅戰(zhàn)的方針:
歷次戰(zhàn)役證明我軍實行戰(zhàn)略或戰(zhàn)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圍美軍幾個師,或一個整師,甚至一個整團,都難達到殲滅任務。……這就是說,打美英軍和打偽軍(注:南朝鮮軍)不同,打偽軍可以實行戰(zhàn)略或戰(zhàn)役的大包圍,打美英軍則在幾個月內(nèi)還不要實行這種大包圍,只實行戰(zhàn)術(shù)的小包圍,即每軍每次只精心選擇敵軍一個營或略多一點為對象而全部地包圍殲滅之。這樣,再打三四個戰(zhàn)役,即每個美英師,都再有三四整營被干凈殲滅,則其士氣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動搖不可,那時就可以作一次殲敵一個整師,或兩三個整師的計劃了。過去我們打蔣介石的新一軍、新六軍、五軍、十八軍和桂系的第七軍,就是經(jīng)過這種小殲滅到大殲滅的過程的。……還須經(jīng)幾次戰(zhàn)役才能完成小殲滅戰(zhàn)的階段,進到大殲滅戰(zhàn)的階段。至于打的地點,只要敵人肯進,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過平壤、元山線就行了。
5月27日,毛澤東將上述電示彭德懷的內(nèi)容通報了蘇聯(lián)領(lǐng)導人約瑟夫·斯大林。但斯大林顯然對這個電報產(chǎn)生了誤解,5月29日,他復電毛澤東指出,這個方針是“冒險的”,很易被美英軍識破,“拿蔣介石軍隊作類比,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一旦美英軍向北推進并建立一道道防線,你們突破防線就會付出巨大損失”。出于上述擔心,斯大林提出建議:“看來你們將要準備一次重大的戰(zhàn)役,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局部機動,而是為了給美英軍以沉重打擊。”
可以說,是斯大林首先提出抗美援朝的第六次戰(zhàn)役問題。不過,“毛澤東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并未接受斯大林的建議,而根據(jù)戰(zhàn)爭的實際情況,按打小殲滅戰(zhàn)方針對部隊進行了教育和部署。”5月30日,彭德懷曾欲致信朝鮮人民軍總指揮金雄(這封信經(jīng)毛澤東批示沒有發(fā)出),強調(diào):
一、從歷次戰(zhàn)役來看,美英軍還保持著相當高的戰(zhàn)斗意志。我們現(xiàn)有條件,每次戰(zhàn)役要求消滅其一兩個師是困難的,即消滅其一兩個整團亦屬不易。然而,偽軍的戰(zhàn)斗意志是薄弱的,一次消滅其兩三個師是可能的。把美英軍的戰(zhàn)斗意志削弱到現(xiàn)在偽軍的低度還須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準備半年至一年)。志愿軍在今后三個月內(nèi),一般(特殊情況在外)對美英軍不擬組織全面的大戰(zhàn)役,以兵團為單位不斷進行小戰(zhàn)役,爭取一個軍每月平均消滅美軍一個整營(擊傷除外)。假如志愿軍經(jīng)常以八至九個軍作戰(zhàn)計,每月即可消滅其八至九個建制營,再加上人民軍經(jīng)常以兩個軍團計,每月消滅美軍兩個營,即可每月消滅美英軍十至十一個營。如此,有三至六個月,美英軍戰(zhàn)斗意志必然逐漸降低,那時大規(guī)模地消滅美英軍的客觀條件就將成熟。同時,目前主觀方面每月組織一次大戰(zhàn)役,我之供應運輸和兵員補充也來不及(今后一個戰(zhàn)役需四萬五千至六萬人的補充)。目前迫切需要改善運輸條件,加強新兵訓練,克服各種困難,準備長期作戰(zhàn)是必要的。
二、我之優(yōu)勢是正義和人力,敵之優(yōu)勢是裝備技術(shù)。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是爭取勝利的基本方針。由于我技術(shù)條件不如敵人,因此一次不能大量地消滅敵人,因此必須采取削弱敵人,一股一股逐漸地消滅,然后進行大規(guī)模地殲滅之。……在這樣的方針下,暫時讓出一些地方給敵人,縮短我后方供應線,不僅與我無害,反而有益。
彭德懷起草信稿后,立即電呈毛澤東,聽取毛澤東的意見。而這時,金日成正要赴北京與毛澤東討論戰(zhàn)爭形勢和方針問題,故毛澤東指示此信暫不發(fā)。“6月2日,彭德懷將此信內(nèi)容轉(zhuǎn)發(fā)志愿軍在第二線的各軍、志愿軍空軍和后勤部門,要求按此布置工作。”
可以說,“今后三個月內(nèi),一般(特殊情況在外)對美英軍不擬組織全面的大戰(zhàn)役”,是彭德懷的最初考慮。不但如此,他還設(shè)想“暫時讓出一些地方給敵人,縮短我后方供應線”,以誘敵深入,后發(fā)制人。
中朝雙方“準備八月進行一次有把握的穩(wěn)打穩(wěn)扎的反攻”
巧的是,就在1951年5月30日,朝鮮領(lǐng)導人金日成致信彭德懷,專門就如何能夠爭取較短時期內(nèi)戰(zhàn)勝敵人的問題,提出在6月末或7月中旬對敵進行一次大的反攻行動——第六次戰(zhàn)役的建議。在這封信中,金日成鄭重指出:“朝鮮戰(zhàn)爭由于美干涉者日增其武裝力量,而戰(zhàn)爭更加困難,增加殘酷性和長期性是無容隱諱的事實。”“當然,在朝鮮延長軍事行動,這一點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均對我不利。”因此,“我之軍事行動,我意不必延長。”他最后建議,“總攻擊日期可預定為6月末或7月中旬”;應充分利用雨季,在雨季開始前10日進行攻擊;擬將朝鮮人民軍3個機械化師編成1個獨立機械化軍團,配屬中朝聯(lián)合司令部之下使用;將必要的糧食彈藥聚積于三八線一帶,繼續(xù)收集糧食至少保障20天的供應;以航空掩護這次反攻行動。
作為朝鮮領(lǐng)導人,金日成希望中朝聯(lián)軍盡早反攻,早日實現(xiàn)國土統(tǒng)一,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彭德懷本意“今后三個月內(nèi),一般(特殊情況在外)對美英軍不擬組織全面的大戰(zhàn)役”,故對金日成的建議很難贊成,遂將其來信轉(zhuǎn)報毛澤東。endprint
5月31日,美國國務院派喬治·凱南向蘇聯(lián)駐聯(lián)合國代表馬立克表明,美國愿意通過談判沿三八線一帶實現(xiàn)停火。蘇聯(lián)將這一情況向中國和朝鮮作了通報。6月3日,金日成火速來到北京,與毛澤東討論戰(zhàn)爭形勢問題,確定邊打邊談的方針,“充分準備持久作戰(zhàn)和爭取和談達到結(jié)束戰(zhàn)爭”。會談中,毛澤東對發(fā)動大的進攻行動問題與金日成進行了磋商。6月1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告知關(guān)于作戰(zhàn)問題與金日成會談的結(jié)果:“已和金日成同志談好目前兩個月不進行大的反攻戰(zhàn)役,準備八月進行一次有把握的穩(wěn)打穩(wěn)扎的反攻。”“六七兩個月內(nèi)如不發(fā)生意外變化(即登陸),我們必須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積極防御的方法堅持鐵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線,不使敵人超過伊川線;乙、迅速補充三兵團及十九兵團至每軍四萬五千人,并有相當訓練;丙、十三兵團各軍休整完畢;丁、加強各軍師火力,特別是反坦克反空軍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寧遠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條,最好有兩條,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區(qū)屯積相當數(shù)量的糧食,以備萬一之用。”
就是說,經(jīng)過毛澤東、金日成的最高級會談,中朝雙方互有妥協(xié):中方放棄了“三個月內(nèi),一般(特殊情況在外)對美英軍不擬組織全面的大戰(zhàn)役”的主張,朝方不再堅持“總攻擊日期可預定為6月末或7月中旬”,雙方一致同意“準備八月進行一次有把握的穩(wěn)打穩(wěn)扎的反攻。”
6月30日,“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馬修·李奇微發(fā)表聲明,表示愿意通過談判結(jié)束朝鮮戰(zhàn)爭。7月1日,金日成、彭德懷復電李奇微:“我們受權(quán)向你聲明,我們同意為舉行關(guān)于停止軍事行動和建立和平的談判而和你的代表會晤。”
而在6月29日,即停戰(zhàn)談判即將開始的情況下,毛澤東致電金日成并告彭德懷,指出在準備同敵人談判的同時,“人民軍和志愿軍應當積極注意作戰(zhàn),不使敵人乘機獲逞。”7月1日18時,在和金日成共同聲明愿意進行停戰(zhàn)談判的當天下午,彭德懷根據(jù)“不使敵人乘機獲逞”的指示,致電毛澤東匯報了為配合停戰(zhàn)談判,著手計劃第六次戰(zhàn)役的設(shè)想:
充分準備、持久作戰(zhàn)和爭取和談達到結(jié)束戰(zhàn)爭的方針是完全必須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幟,對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均有利。堅持以三八線為界,雙方均過得去,如美國堅持現(xiàn)在占領(lǐng)區(qū),我即準備八月反擊,在反擊前還須放他前進數(shù)十里,使軍事上、政治上于我更有利些。再爭取一兩個或兩三個軍事上較大勝利,將影響所謂聯(lián)合國全部的可能分裂,美軍戰(zhàn)斗意志的必然降低。
根據(jù)電報中“如美國堅持現(xiàn)在占領(lǐng)區(qū),我即準備八月反擊”可以看出,彭德懷是把擬定中的第六次戰(zhàn)役,直接服務于停戰(zhàn)談判的,即以戰(zhàn)逼和。
鄧華、解方提出談判要“戰(zhàn)斗勝利相配合才更為有利”
1951年7月2日,就在朝鮮戰(zhàn)場雙方協(xié)商停戰(zhàn)談判的時間、地點等問題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高崗、金日成,要求對談判有關(guān)事宜作出部署,同時進一步提醒志愿軍領(lǐng)導:“我第一線各軍,必須準備對付在談判前及談判期內(nèi)敵軍可能對我來一次大的攻擊,在后方,則舉行大規(guī)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訂立城下之盟。如遇敵軍大舉進攻時,我軍必須大舉反攻,將其打敗。”毛澤東的這份指示,吹響了積極準備第六次戰(zhàn)役以配合停戰(zhàn)談判的號角。
7月8日,志愿軍司令部向各部首長下達了戰(zhàn)役準備工作指示,在分析第五次戰(zhàn)役后敵情特點的基礎(chǔ)上,針對第六次戰(zhàn)役將面臨的陣地攻堅和連續(xù)縱深突破作戰(zhàn)的新情況,強調(diào)要與過去攻堅作戰(zhàn)經(jīng)驗相結(jié)合,在部隊中展開對敵縱深攻堅突破學習的浪潮,求得第六次戰(zhàn)役更多地殲滅敵人,7月底或8月初前教育準備完畢,隨時待命出動作戰(zhàn)。
7月10日,朝鮮戰(zhàn)爭停戰(zhàn)談判開始,但由于美方不愿公平合理地解決朝鮮問題,直到7月24日竟連談判議程問題也未能達成協(xié)議。于是,第六次戰(zhàn)役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
7月16日,彭德懷致電中方談判人員李克農(nóng)、鄧華、解方,指出:“如果沒有和平攻勢(和談)的政治斗爭,只有單純的軍事斗爭,要想迅速孤立美國,迅速結(jié)束朝鮮戰(zhàn)爭是不可能的。……但和談并不一定是順利的,可能遇著很多困難,甚至曲折過程,可能還需要經(jīng)過嚴重的軍事斗爭。再有兩三次較大的軍事勝利,才能使敵人知難而退。”同時,他通報了志愿軍和人民軍積極進行第六次戰(zhàn)役戰(zhàn)術(shù)演習教育和具體準備工作情況。
7月24日,由于美方一直消極談判,彭德懷就組織戰(zhàn)役反擊以配合談判問題致電毛澤東,談了自己的打算:“我再有幾次勝利戰(zhàn)役,打至三八線以南,然后再撤回三八線為界進行和談,按比例逐步撤出在朝外國軍隊,堅持有理有節(jié),經(jīng)過復雜斗爭,爭取和平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從全局觀點來看,和的好處多,戰(zhàn)亦不怕。……我于八月中爭取完成戰(zhàn)役反擊的準備,如敵不進攻,則至九月舉行。最好是待敵進攻,我則依靠陣地出擊為有利。”
從7月中旬到8月中旬,“由于停戰(zhàn)談判開始,雙方作戰(zhàn)均較謹慎,多屬于小部隊的前哨戰(zhàn)斗,因此,戰(zhàn)線無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設(shè)想的誘敵深入、防守反擊難以實行,遂建議“如敵不進攻,則至九月舉行”反攻。這就初步改變了“我即準備八月反擊”的原定計劃。
7月26日,毛澤東復電彭德懷,肯定其意見:“敵人是否真想停戰(zhàn)議和,待開城會議再進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戰(zhàn)協(xié)定沒有簽訂,戰(zhàn)爭沒有真正停止以前,我軍積極準備九月的攻勢作戰(zhàn)是完全必要的。”這樣,原定的“八月反攻”改為了“九月攻勢(或九月戰(zhàn)役)”。
不過,事情又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7月27日,在停戰(zhàn)談判進入軍事分界線問題的實質(zhì)性討論后,美方首席代表、美國遠東海軍司令特納·喬埃中將更加傲慢,不但絲毫沒有讓步的表示,而且狂妄地炫耀海空軍優(yōu)勢,并無理要求這種優(yōu)勢要在軍事分界線的確定上得到“補償”,要求中朝兩軍不戰(zhàn)而退出1.2萬平方公里的地區(qū)。7月31日,鑒于這種談判形勢,志愿軍談判代表鄧華、解方致電彭德懷等志愿軍領(lǐng)導人,滿腔怒火地建議:“爭取和談來結(jié)束朝鮮作戰(zhàn)的方針是正確的,但目前談判時機不恰當,加之我們在談判上的某些讓步,敵已發(fā)生錯覺,故談判時敵之氣焰甚高,借口海空優(yōu)勢吃了虧而在陸地來補償?shù)恼擖c,把分界線及非軍事區(qū)都要推到我方地區(qū)以內(nèi),數(shù)天來的爭論,敵毫無讓步,據(jù)我們估計,至多只能讓到現(xiàn)地停戰(zhàn)。如果沒有外部的動力(如蘇聯(lián)壓力、英法等國的矛盾、特別是我之戰(zhàn)斗勝利等),要想敵人撤回三八線以南十公里是極端困難的。談判需要戰(zhàn)斗勝利配合,并須作破裂之軍事準備,為此建議:……戰(zhàn)役準備,爭取八月十五以前完成,準備破裂后的反擊以八月內(nèi)動作為宜……如談判仍在持續(xù),最好是乘敵進攻時予以有力地打擊……或者我舉行地區(qū)性的主動攻擊敵人。總之,談判需要政治攻勢,特別是戰(zhàn)斗勝利相配合才更為有利。”鄧華和解方還對戰(zhàn)役的兵力部署(包括使用已入朝的坦克部隊)、戰(zhàn)役的組織和作戰(zhàn)目標提出了建議。endprint
“八月反擊”,似乎就要名符其實了!
彭德懷發(fā)布預令動員全軍“積極準備作戰(zhàn)”
1951年8月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對“九月戰(zhàn)役”的兵力部署和糧彈儲備問題作了原則指示,實際上否決了鄧華、解方的建議。同日,中央軍委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致電彭德懷,報告空軍參戰(zhàn)準備情況。
8月8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并告高崗,報告了第六次戰(zhàn)役的作戰(zhàn)意圖和基本設(shè)想:
擬以第十九兵團3個軍加上第47、第42軍,以2個軍牽制英國、加拿大、土耳其共4個旅,以3個軍附炮兵、坦克,爭取消滅漣川、鐵原線之美騎兵第1師;
擬以第九兵團2個軍牽制金化之美第24、第25、第3師及南朝鮮軍第2、第9師,求得殲敵一部;
擬以第二十兵團2個軍沿北漢江兩岸突破南朝鮮第6師防線,向山陽里、華川迂回攻擊;
北漢江以東至海岸由人民軍2個軍團進行牽制攻擊。
以上共計志愿軍9個軍、人民軍2個軍團。
另,以第40、第38軍及第三兵團3個軍共5個軍為戰(zhàn)役二梯隊,以便機動使用;第39、第20軍分別擔任東、西海岸預備隊;空軍聯(lián)合司令部應于8月20日移至平壤,準備參戰(zhàn)之空軍技術(shù)熟練的10個團于9月8日進入平壤機場。
如無意外變故,擬于9月10日下午發(fā)起戰(zhàn)役攻擊。下一戰(zhàn)役無論進攻或反擊,準備連續(xù)激戰(zhàn)20天至一個月。如我第一線傷亡嚴重,不能再繼續(xù)作戰(zhàn)時,將二梯隊5個軍及第20、第39軍共7個軍和人民軍2個軍團,適時投入戰(zhàn)斗,再持續(xù)一個月攻勢。我能堅持兩個月的連續(xù)攻擊,打破我以往6~7天的短時攻擊。每月消耗敵4萬人左右,美帝似有可能屈服求和,以三八線為界,撤退在朝外國軍隊。
電報同時指出,“如敵在8月底或9月初向我進攻,則在現(xiàn)陣地以逸待勞,適時舉行反擊最為有利。”言下之意,一旦敵人主動大規(guī)模出擊,“九月戰(zhàn)役”將推遲。
8月9日,彭德懷致電劉亞樓:
8月1日電共有空軍22個團于9月初參戰(zhàn),甚為欣慰。空聯(lián)司最好8月20日左右移平壤,并盼你于8月底或9月初來平壤主持如何?
8月17日,在8月8日關(guān)于戰(zhàn)役意圖和基本設(shè)想的基礎(chǔ)上,彭德懷以志愿軍司令部和中朝聯(lián)軍司令部名義向部隊下達了作戰(zhàn)預令,同時報金日成、中央軍委和東北軍區(qū)。這一預令與8月8日的基本設(shè)想略有不同,朝鮮人民軍多了2個軍團參戰(zhàn),殲敵對象也由美騎兵第1師變?yōu)槊赖?師、美第25師,其基本部署是:
戰(zhàn)役第一梯隊為志愿軍8個軍,以第十九兵團3個軍牽制鐵原至臨津江西岸之敵,堅決阻擊鐵原以南之敵向北增援;集中第47、第42兩軍包圍殲滅鐵原地區(qū)的美第3師。
以第26軍和第二十兵團2個軍除各一部牽制當面之敵外,集中主力突破,然后視情況,殲滅金化東西地區(qū)的美第25師(2個團)和南朝鮮軍第2師。
第二梯隊志愿軍第三兵團3個軍,第38、第40軍,共5個軍,于戰(zhàn)役開始后開進到指定地點,視情況投入作戰(zhàn),繼續(xù)擴大戰(zhàn)果。
人民軍4個軍團在北漢江以東至東海岸,分兩番配合志愿軍作戰(zhàn)。
預令要求各攻擊部隊務于9月10日前完成連續(xù)縱深攻堅戰(zhàn)斗的充分準備,各兵團和軍于8月25日前研究出具體的作戰(zhàn)方案。擔任戰(zhàn)役第二梯隊各部根據(jù)距離遠近不同,于8月28日前作出開進計劃。第9兵團(欠第26軍)應隨時策應元山方面和南線主力方面作戰(zhàn)。特種兵的配屬將另以補充命令下達(預計參戰(zhàn)炮兵,榴彈炮3個師,戰(zhàn)防炮1個師,火箭炮1個師,坦克3個團,連同隊屬炮兵的火炮在內(nèi),共有各種火炮2119門)。
彭德懷在電報最后指出:“以上系預定方案,請根據(jù)實際情況提出補充和修改意見,并請金日成總司令提出意見。”同時,他將預案發(fā)給在開城談判的鄧華和解方,征求他們的意見。鄧華和解方分別對17日的預案提出了具體的補充完善意見。
8月24日,彭德懷在給鄧華、解方的電報中,進一步闡明了戰(zhàn)役意圖,并強調(diào)指出:“17日預備命令,是要把全軍動員起來,積極準備作戰(zhàn),而非具體部署。”
志愿軍政治部下發(fā)“第六次戰(zhàn)役的政治工作指示”
早在1951年5月17日,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批準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5號文件,第一次明確“聯(lián)合國軍”的作戰(zhàn)不再以實現(xiàn)軍事占領(lǐng)全朝鮮為目標。6月上旬,“聯(lián)合國軍”全線轉(zhuǎn)入戰(zhàn)略防御,并進行各種軍事準備。為應對中朝軍隊的進攻,“聯(lián)合國軍”加強了陣地工事。到7月下旬,基本完成了“堪薩斯——懷俄明線”的工事構(gòu)筑。
“堪薩斯線”西起臨津江口南岸,沿江而上,經(jīng)積城、道城峴、華川湖南岸、楊口至東海岸桿城以北馬達里一線,全長約230余公里,是“聯(lián)合國軍”的主抵抗線;“懷俄明線”,西起臨津江口北岸,向東北延伸,經(jīng)鐵原、金化到華川湖南岸與“堪薩斯線”相接,全長約150公里,是“堪薩斯線”在西部地區(qū)的一道屏護線。為此,7月間,“聯(lián)合國軍”調(diào)用南朝鮮3個國民警衛(wèi)師構(gòu)筑“堪薩斯——懷俄明線”的陣地工事,用圓木、沙袋構(gòu)筑了各類堅固的掩體,包括坦克、火炮、機槍、步槍等各種火器掩體,并有塹壕相連接,且陣地前均設(shè)有大量地雷和鐵絲網(wǎng),在“懷俄明線”還構(gòu)筑有永久工事。
不言而喻,“聯(lián)合國軍”的縱深防御明顯加強,是“八月反擊”推遲為“九月戰(zhàn)役”的重要因素。由于“九月戰(zhàn)役”將是陣地攻堅的縱深作戰(zhàn),所以彭德懷不能不慎之又慎。由于這次參戰(zhàn)兵種較多,遂在部隊中進行了攻堅突破的教育和準備,結(jié)合各種地形進行攻堅突破演習,組織了步兵、炮兵、坦克部隊之間的戰(zhàn)術(shù)協(xié)同和通信聯(lián)絡(luò)教育,著手攻堅突破的器材及作戰(zhàn)所需糧食彈藥的準備。7月29日,志愿軍司令部轉(zhuǎn)發(fā)了第64軍進行攻堅突破教育情況,以促使各部隊科學組織,正確施教,切實提高效果。次日,又以中朝聯(lián)軍司令部名義,將第三兵團成立戰(zhàn)術(shù)研究會及其活動的做法通報各部隊“依照辦理”。根據(jù)志愿軍司令部指示,志愿軍炮兵下達了機動炮兵調(diào)整方案,要求進行充分的準備和油彈糧食的囤積,積極配合部隊作戰(zhàn)役性質(zhì)的偵察,認真了解掌握預定進攻方向的敵情道路情況。endprint
8月18日,為查明“聯(lián)合國軍”前沿陣地及其縱深情況,中朝聯(lián)軍司令部指示第一線各部隊,不放過有利機會,殲滅在前沿探索和進擾的小股之敵,詢問情況;以精干的兵力,對敵兵力不多、陣地不堅的突出的前哨陣地實施攻擊,力求奪取之。8月中旬,中朝聯(lián)軍還派出了戰(zhàn)役偵察。
8月21日,為把全軍動員起來,積極準備作戰(zhàn),志愿軍政治部專門就“九月戰(zhàn)役”下發(fā)了“第六次戰(zhàn)役的政治工作指示”,提綱挈領(lǐng)地指出:第六次戰(zhàn)役是再度給敵人以重大打擊,取得這次戰(zhàn)役的勝利,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都有偉大意義,并從而徹底揭破美帝在最近和平談判中的陰謀詭計。要取得勝利,必須估計到敵人是有準備的,這是一場激烈的持續(xù)攻堅戰(zhàn)。
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和東北軍區(qū)也為“九月戰(zhàn)役”做了必要的準備,主要是:一、決定調(diào)第二十三兵團2個軍共3.5萬人,在修建新的機場的同時,兼在后方反特和反敵空降任務;2個火箭炮團、2個榴彈炮團和1個重榴彈炮團,待命入朝;二、“九月戰(zhàn)役”各種主要彈藥己運到前方,并有超過;三、志愿軍冬季服裝擬于9月、10月、11月運入前方;四、9月份所需糧食,決于8月底前運完,準備9月上半月?lián)屵\戰(zhàn)役發(fā)起后的10月份用糧;五、從關(guān)內(nèi)抽調(diào)500個車皮專供加強在朝鮮的運輸。另決9月份補充前方汽車1700輛,以后按每月消耗撥補;六、準備新兵17萬人于9月底前集中東北整訓待補。
中朝聯(lián)軍司令部關(guān)于“九月戰(zhàn)役”的預備命令下達后,志愿軍各兵團各軍按照預令要求,認真研究制定出作戰(zhàn)行動方案和開進計劃,并按時上報聯(lián)軍司令部。人民軍亦詳細研究了上級意圖和敵我情況,擬訂出具體作戰(zhàn)方案,上報聯(lián)軍司令部。
誠如中國軍方組織編寫的《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所言,“從7月8日志愿軍發(fā)出第六次戰(zhàn)役準備工作指示后,各部隊即結(jié)合貫徹持久作戰(zhàn)方針,開始了第六次戰(zhàn)役的準備工作。”
不過,準備工作也有不足之處。8月4日、5日,周恩來攜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同蘇聯(lián)駐中國軍事總顧問克拉索夫斯基,就中國、蘇聯(lián)空軍進駐朝鮮的時間和進駐前機場增建問題進行了研究,因機場的修建要到11月份才能完成,因此“我空軍出動和作戰(zhàn)必須推遲到11月份才能實現(xiàn)”。
空軍推遲入朝,不能不影響“九月戰(zhàn)役”的發(fā)動。
中央軍委建議第六戰(zhàn)役“可否改為加緊準備而不發(fā)動”
無論是“八月反擊”還是“九月戰(zhàn)役”,第六次戰(zhàn)役都是旨在配合停戰(zhàn)談判,爭取早日實現(xiàn)停戰(zhàn)。但是,何時發(fā)起攻擊,發(fā)起攻擊以后能否順利發(fā)展,這些必須從是否對談判有利來考慮。在接到彭德懷8月8日關(guān)于第六次戰(zhàn)役的作戰(zhàn)意圖和基本設(shè)想的電報后,毛澤東于8月10日批示:“請周、聶迅即集會研究,提出意見。”10日夜間,周恩來邀集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炮兵司令員陳錫聯(lián)、總后勤部部長楊立三、軍委作戰(zhàn)部部長李濤等,對彭德懷8日來電進行了研究,與會者研究認為:
根據(jù)目前朝鮮雨季情況,九月份鐵路、橋梁、公路不一定能完全修好,即使預計的九月份全月糧食能于八月中旬搶過鴨綠江,但不一定都能運過清川江(橋梁全斷)。如果糧食不足,彈藥有損(潮濕一部是可能的,前方尚未查清),便決定大打,而空軍又確定不能參加,在敵人又已確定堅守的條件下,恐很難連續(xù)作戰(zhàn)二十日至一個月。同時,在政治上,九月如仍在繼續(xù)談判,我便發(fā)動大打,亦不甚有利,如再不能大勝,則影響更不好。從種種方面看,我以加緊準備,推遲發(fā)動大打為有刊。九月談判如破裂,則十月便須準備大打;如敵不進,則九、十兩月可在沿線尋找小戰(zhàn),不斷給敵以殺傷,至十一月再大打,空軍或有配合的可能。
就是說,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傾向于緩打:“九月戰(zhàn)役”推遲為“十月戰(zhàn)役”甚至“十一月戰(zhàn)役”。
8月11日早晨,周恩來將討論情況書面報告毛澤東。但“關(guān)于空軍參戰(zhàn)的機場尚未準備好,中央軍委決定空軍參戰(zhàn)時間推遲到11月份,征求斯大林的意見還未得到答復,因此上述研究意見未及時通報給彭德懷。”所以,彭德懷仍然堅持“九月戰(zhàn)役”,志愿軍司令部遂于8月17日下達了作戰(zhàn)預令。接到彭德懷8月17日下達的作戰(zhàn)預令電稿后,周恩來起草了中央軍委給彭德懷并告高崗的電報,經(jīng)毛澤東親自閱改后,于8月19日發(fā)出。
首先,這份電報分析說,美國不敢徹底破裂和談:
敵人對于朝鮮談判,只打算實現(xiàn)軍事休戰(zhàn)而不妨礙他的世界緊張政策,故他反對以三八線為分界線,政治原因大過軍事原因。其拖延談判,一方面企圖以此逼我讓步,另方面也為拖過舊金山會議(注:解決所謂對日“和約”問題)及便利其國會通過預算和加稅。敵人敢于這樣拖延,自然是因為了解我們正在誠意謀和。但敵人也怕負起談判破裂的責任,其原因由于他們了解我們在朝鮮的力量已在加強,如果破裂后大打起來,問題依然不能解決,如因此而將戰(zhàn)火擴張至中國大陸,可能又遇到英、法的反對。
接著,這份電報詳細分析了發(fā)動“九月戰(zhàn)役”的不利因素,建議“可否改為加緊準備而不發(fā)動”:
但從現(xiàn)在具體情況看來,不僅空軍在九月份不能參戰(zhàn)并也不能掩護清川江以南的運輸,而且其他方面也不易使我們這次戰(zhàn)役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首先,朝鮮雨季八月底才能結(jié)束,清川江、大同江、新成川、富城幾座橋梁尚未修通,清川江以北堆積的糧車最快恐需至八月底才能倒裝完畢,因之,連續(xù)作戰(zhàn)一個月的糧食在九月份得不到完全保證。彈藥從現(xiàn)在前方儲量計算可供一個月作戰(zhàn)消耗,但雨水浸蝕的程度不知檢查結(jié)果如何,有些倉庫距離前線較遠,尚不能供應及時。且戰(zhàn)役發(fā)起后,不論勝利大小,均有使戰(zhàn)役繼續(xù)發(fā)展可能,我們糧彈儲備只有一月,而后方運輸又未修暢,設(shè)敵人窺破此點,我將陷入被動。次之,從戰(zhàn)術(shù)上看,在九月份談判中,敵人向我進攻的可能是較少的,因此,我軍出擊必須攻堅,而作戰(zhàn)正面不寬,敵人縱深較強,其彼此策應亦便。我第一線又只能使用八個軍突入,……(敵)有十六個師旅可供呼應,即使我在戰(zhàn)役開始時,殲敵一部,但突入后迂回滲透,擴張戰(zhàn)果及推進陣地,則須經(jīng)過反復激戰(zhàn),時間拖長的可能極大,結(jié)果對談判可能起不利作用。現(xiàn)在我們握有重兵在手,空軍、炮兵逐步加強,敵人在談判中對此不能不有顧慮。設(shè)若戰(zhàn)而不勝,反易暴露弱點。如談判在分界線及非軍事區(qū)問題上,在九月份尚有妥協(xié)可能,亦以不發(fā)起戰(zhàn)役為能掌握主動。據(jù)此種種,望你對九月戰(zhàn)役計劃再行考慮,可否改為加緊準備而不發(fā)動,如此,既可預防敵人挑釁和破裂,又可加強前線訓練和后勤準備。endprint
8月21日,中央軍委又將國內(nèi)為原定“九月戰(zhàn)役”所做的有關(guān)部隊調(diào)動、機場修建、兵員補充、物資供應及運輸?shù)雀黜棞蕚淝闆r電告了彭德懷,表明“加緊準備”有條不紊。
彭德懷最終決定“大戰(zhàn)役反擊在無空軍配合情況下暫不進行”
而早在7月初,“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就擔心,“中朝聯(lián)軍會利用談判時機聚集起強大的進攻力量,一旦談判破裂,就能夠發(fā)動強大的攻勢。”對此,美國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也“極為擔心”。“李奇微并從有關(guān)方面獲知,志愿軍將于8月底發(fā)動‘第六次戰(zhàn)役。”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軍方策劃,決定對朝鮮北方實施“空中封鎖交通線戰(zhàn)役”,即所謂的“絞殺戰(zhàn)”,目的“一、阻止敵人在北朝鮮建立重要的空軍基地;二、阻斷敵人的供應,使他們不能發(fā)動及維持一個大規(guī)模的地面攻勢;三、以空軍壓力傷害敵人,以影響停戰(zhàn)談判。”
8月18日,出乎中央軍委8月19日電報的意料(“在九月份談判中,敵人向我進攻的可能是較少的”),“聯(lián)合國軍”以其地面部隊發(fā)動了夏季攻勢;同一天,“聯(lián)合國軍”以其空軍(美國空軍為主)發(fā)動了“絞殺戰(zhàn)”。
正當美軍開始“絞殺戰(zhàn)”時,朝鮮北方爆發(fā)了40年來罕見的特大洪水,美國人狂呼“老天也幫了轟炸機指揮部的忙”。8月間至9月中旬,美國第五航空隊每天為其每個戰(zhàn)斗轟炸機大隊規(guī)定一段15至30英里長的鐵路,由他們前去轟炸。美戰(zhàn)斗機大隊一般以大隊編隊方式,以32機到64機的大機群出動,對京義線沙里院以北和整個滿浦線進行轟炸;轟炸機指揮部的B–29戰(zhàn)略轟炸機,對平壤以北正在修建的機場和幾座主要鐵路橋梁進行轟炸;海軍艦載航空兵對朝鮮東海岸的鐵路進行轟炸。由于美軍“絞殺戰(zhàn)”和洪水的雙重破壞,到8月底,朝鮮北方1200余公里長的鐵路中,能通車的線路僅有290公里,整個鐵路交通處于前后不通中間通的狀態(tài)。
本來志愿軍運輸能力弱又沒有空軍掩護,戰(zhàn)場運輸相當困難,“絞殺戰(zhàn)”一來更如雪上加霜。對此困境,彭德懷當機立斷,于8月21日、22日兩次致電中央軍委,表示鑒于“空軍九月不能入朝參戰(zhàn),運輸物資又無保障”,“同意將九月戰(zhàn)役進攻,改為積極準備”。“九月戰(zhàn)役改為積極備戰(zhàn),防敵進攻,準備適當時機反擊,如敵暫不進攻,待十月再決”。
9月初,志愿軍前線部隊出現(xiàn)了食物短缺狀況,且冬寒將至,棉衣尚未運到。9月7日,彭德懷在給聶榮臻的電報中有一段話反映了當時前方的困難:“早晚秋風襲人,戰(zhàn)士單著,近旬病員大增,洪水沖,敵機炸,橋斷路崩,存物已空,糧食感困難,冬衣如何適時運到,實在逼人。”
與此同時,就在8月18日,即“聯(lián)合國軍”發(fā)動1951年夏季攻勢當天,鄧華在給彭德懷并轉(zhuǎn)毛澤東的電報中,仍然主張以軍事勝利配合談判:“在軍事上我應有所準備,縱目前不進行戰(zhàn)役反擊,也當盡可能作戰(zhàn)術(shù)的反擊,收復些地方,推前接觸線,更好地了解敵人陣地及其堅固程度。”8月2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請他考慮鄧華的建議:“我認為這個意見值得認真考慮,請你計劃一下,九月份能否進行此種戰(zhàn)術(shù)反擊,如何進行法,須用多少兵力,勝利把握如何,敵人的反應將會如何,請就這幾點考慮電告。”8月23日,彭德懷復電毛澤東,說:“九月不舉行大的戰(zhàn)役進攻時,可選擇偽軍突出部隊舉行局部進攻。”最終,在8月18日至9月18日的粉碎“聯(lián)合國軍”夏季攻勢、10月1日至10月22日的粉碎“聯(lián)合國軍”秋季攻勢中,中朝聯(lián)軍相繼殲敵7.8萬人和7.9萬人,證明依托陣地舉行戰(zhàn)術(shù)性的反擊作戰(zhàn),更有利于大量殲敵,更有利于戰(zhàn)線的穩(wěn)定,對堅持持久作戰(zhàn)更有利。因此,到了10月下旬,彭德懷最終決定,“大戰(zhàn)役反擊在無空軍配合情況下暫不進行”,“十一月甚至今年底(除特別有利情況在外),擬不準備進行全線大反擊戰(zhàn)役,根據(jù)九、十月經(jīng)驗,采取積極防御方針,敵人消耗很大,敵對我亦甚恐懼”。
至此,第六次戰(zhàn)役計劃遂告撤銷。
第六次戰(zhàn)役計劃雖未實施,但這一戰(zhàn)役計劃是根據(jù)停戰(zhàn)談判的需要而提出的,也是根據(jù)停戰(zhàn)談判的需要而放棄的。第六次戰(zhàn)役計劃的擬定與取消,完全是在毛澤東的過問下,根本不是彭德懷擅自制定的,甚至一開始他是反對第六次戰(zhàn)役的——“一般(特殊情況在外)對美英軍不擬組織全面的大戰(zhàn)役!”同時,第六次戰(zhàn)役的準備,在軍事上對1951年粉碎“聯(lián)合國軍”夏秋季攻勢作戰(zhàn)和堅持持久作戰(zhàn)方針,具有直接的積極的作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