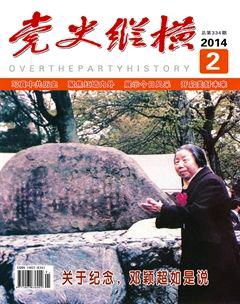詩人何其芳感知的賀龍將軍
楊建民
何其芳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一位有成就的詩人。1934年,他出版了著名散文集《畫夢錄》。這本散文集,在1936年被《大公報》授予“文藝獎金”。由朱自清、沈從文、朱光潛、葉圣陶、巴金、林徽因等組成的裁判委員會對其評價是:“《畫夢錄》是一種獨立的藝術制作,有它超達深淵的情趣。”1938年,何其芳與詩人卞之琳、小說家沙汀一起奔赴延安。在那里,他詩風文風大變,寫出了《我歌唱延安》《我為少男少女歌唱》等作品。期間,他曾隨部隊到晉西北和冀中根據(jù)地實踐,與數(shù)位軍中將領有接觸,并留下深刻印象。一代名將賀龍,就是何其芳感佩一生,難以忘懷者之一。
一
何其芳第一次見到賀龍,是在1939年9月。那是賀龍到魯迅藝術學院演講,何其芳正在那里任教,聽說這位傳奇將軍來演講,自然趕去聆聽。當時在何其芳的眼里,賀龍是這樣的形象:“厚篤篤的身體使他顯得魁梧。寬大的臉上有著兩道濃眉,而又蓄著黑色的短鬚。就外表看,是一個很威嚴的將領。”但是,賀龍講起話來,卻使聽眾不斷發(fā)出笑聲。
賀龍給大家講了自己部隊在前方作戰(zhàn)的事。他說一二〇師初到山西時,看到當時通鋪路上火車開得極慢。慢的程度,他用戰(zhàn)士的話形容是:“我們跳下去解個小手還趕得上。”還是火車,賀龍講,一次一個連去襲擊敵人的火車。敵人潰敗逃跑時,一個戰(zhàn)士居然可以抓住一個日本兵的腳,把他從火車上拉下來俘虜了。這就把火車之慢講得生動可感。
就算講到戰(zhàn)利品的成績,賀龍也不用枯燥的數(shù)字。他說,去年過黃河,戰(zhàn)士每支槍只有5排子彈,一人只3顆手榴彈,到太原打了幾仗,就從敵人處“領”了十幾萬子彈手榴彈;望遠鏡過去是稀罕物,師部才有一個,現(xiàn)在營以上都有了,而且連照相機也有了。賀龍用一句話總結:“希望慢慢地在前線把裝備都換好。”詼諧的話語中透著堅定和自信。
對于這次聽演講的感受,何其芳后來這樣總括:“……他一開口講起話來卻充滿了詼諧,使聽眾不斷地發(fā)出笑聲。這與外國紳士們所說的什么幽默完全不同。這是一種充滿了活力的中國勞動人民所原有的詼諧,在紳士與淑女們聽來也許會感到粗魯?shù)脑溨C。而在賀龍將軍身上,這更帶著這樣一種特點:經(jīng)過了千百次艱難困苦然而從未失掉自信和勇氣的樂觀。”
那時,何其芳與小說家沙汀正準備到前方去體驗,賀龍的演講吸引了他們,他們決定跟隨賀龍去晉西北地區(qū)。為協(xié)商此事,他們?nèi)ベR龍住處了一趟。賀龍當時住在延安一排三間的窯洞里。這里除賀龍外,還住著一二0師政委關向應及鄧小平、楊尚昆等人,所以不大的窯洞塞滿了床和桌子。有意思的是,大約他們不習慣睡土炕,窯洞里的土炕上還架著木床,這使窯洞顯得更狹小紊亂了。
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何其芳見到的賀龍,依然不失生龍活虎的氣概。賀龍拿出梨來招呼客人。看他們是文人,賀龍就談起了美國作家斯諾寫的享有盛譽的《西行漫記》,說斯諾寫“過草地”,沒有把草地好的一方面寫出來。他說,草地里有很好的出產(chǎn),如金銀。那里的居民有的修有很漂亮的洋房,有的居民家里還是漆過的地板。部隊經(jīng)過的一些河流魚很多,因為很少有外人驚擾,所以“傻”得很。賀龍喜歡釣魚,所以說起釣魚很是興奮。他指著跟前的關向應政委笑道:他釣魚總是把釣線挨著河邊吊下去,看見魚不過來吃釣餌,他就用魚竿把魚戳一下,魚就過來吃了。賀龍用的湖南方言,“戳”讀“多”,這使四川人何其芳印象深刻。
小說家沙汀當時準備寫一篇印象記,所以詢問賀龍的革命經(jīng)歷。這時候,賀龍嚴肅起來。他簡單敘述了革命中多次受挫,又多次站立起來的經(jīng)歷。其中,他特別提到他的姐姐賀英。在賀龍隊伍被打散之后,是賀英又為他拉起一支農(nóng)民武裝交給他。講到這里,賀龍感到有些沉重,他走出窯洞,站在臺階的柱子旁,帶著悲痛和惋惜說,這位姐姐后來被國民黨殺害了。何其芳后來描述:“他的臉上顯出一種沉浸到憤恨的回憶里的神氣,兩道黑色的濃眉蹙了起來。”
賀龍的這位姐姐賀英,就是后來《洪湖赤衛(wèi)隊》中韓英的原型。這部劇作在“文革”中被批判,被宣布為“毒草”,就與要打倒賀龍相關。這些抹殺拋頭顱,撒鮮血的惡行,是人們不能接受容忍的。
告辭時,沙汀想知道一下賀龍對自己的看法,便問道:有人說你是中國的夏伯陽,你覺得怎么樣?夏伯陽是蘇聯(lián)國內(nèi)戰(zhàn)爭時期一個有豐富經(jīng)歷,同時有鮮明個性的紅軍指揮官,因為當時已有寫他的文學作品在中國出版,因此廣為國人所知。賀龍沒有立刻回答,他想一想,似乎有些“困惑”地說:恐怕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出了門,何其芳與沙汀理論起來,他一再舉證賀龍與夏伯陽之間的差異。這,應該是受到賀龍感染的一種表現(xiàn)吧?
二
這樣的接觸感受,使得何其芳等人更堅定了去賀龍部隊的決心。幾天后一個大雪的日子,何其芳與沙汀以及“魯藝”的20多位同學隨著賀龍一起從延安出發(fā)了。他們乘坐的是延安當時僅有的兩輛卡車。當時已是11月,開始落雪了。在路上,賀龍面對遠處的山頭,拍拍何其芳的肩說:詩人,我指一樣東西問問你,這里的氣候為啥這么特別,半個山頭下雪,半個山頭不下雪?何其芳扶扶眼鏡想不出來。賀龍對著車上人說:不是這里的氣候特別,也不是雪下得不勻,實際是一面坡向陽,地上溫度高,下的雪很快就化了;陰坡的地溫低,雪化得慢。冬天在前方作戰(zhàn),可以靠它來識別方向。戰(zhàn)場上一草一木,都是很重要的物象,都應該仔細觀察。
車到米脂,換騎騾馬。“魯藝”師生雖然多次有人墜落馬下,可這批懷著熱情甚至好奇的文藝師生,還是跌跌撞撞走了5天,趕到了賀龍所率一二〇師司令部所在晉西北的嵐縣。何其芳與沙汀住進了司令部附近的一戶老百姓家里。這家條件較好,給他們住的房間很大,炕壁上還有封神榜故事的彩繪。住在了這樣一個安靜的“前方中的后方”,何其芳和沙汀馬上投入了工作,時常去采訪一些軍政干部。沙汀還是準備寫賀龍傳記,所以兩人有時也一起去司令部聽賀龍談他的家鄉(xiāng)和少年時的生活;賀龍有時也到兩位文學家這里來聊聊坐坐。
何其芳許久后還記得賀龍有一次來他們住所的情形。那天晚上,夜已經(jīng)很深,天氣很冷。他們正在一支“洋蠟”下整理材料,賀龍一下子推門進來,一個衛(wèi)士也沒帶。坐下來,他告訴何其芳沙汀,最近敵人企圖打通同蒲路,正在修補被破壞的鐵路,我們要努力阻止。他還告訴他倆自己頭天去拜訪了山西軍隊中抗戰(zhàn)將領趙承綬。當時國共合作,賀龍所率一二0師歸趙統(tǒng)一指揮。這次會面,賀龍與趙承綬在戰(zhàn)略形勢方面進行了討論,賀龍的信心和對軍事的熟稔,給了趙承綬很強烈的印象。這也為雙方之后聯(lián)手作戰(zhàn),并取得了突出的戰(zhàn)績打下了基礎。endprint
賀龍在談這些時,依然是用樸實簡潔和生動的語言。當他用寬厚的手掌在桌上比劃戰(zhàn)局時,何其芳他們雖不懂,可也能感受到他寬闊的視野和決勝的信念。說完這些話,賀龍又一個人走了出去。門外極黑,走出不幾步,他們就看不見賀龍的身影了。認識了這樣一位有膽識,又富于智慧的將軍,他們愈發(fā)堅定了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心。
當年12月,何其芳沙汀等又隨賀龍向河北進軍。這是一次距離長遠的行軍——過同蒲路,平漢路,進冀中平原……剛剛到達,就遇上日寇大掃蕩,又是不斷地戰(zhàn)斗,不停地夜行軍。槍炮聲總是在不遠處響起……終于,賀龍部與冀中的呂正操部會合了。
那天,何其芳等宿營在高陽縣的惠北口。吃完晚飯,賀龍派人通知,讓何其芳與沙汀到冀中軍區(qū)政治部去。到了才知道,這是為一二〇師與呂正操所率第三縱隊會合召開的聯(lián)歡晚會。何其芳與沙汀被安排在來賓席位,可以清楚看到由幾盞汽燈照亮的搭建舞臺。晚會開始,賀龍首先致辭。他說,日本鬼子有坦克,可我們第三縱隊創(chuàng)造了“坦克舞”。剛才得到消息,日本鬼子的坦克,開到我們埋設的地雷上,有兩輛就“跳起舞”來,然后就歇下來不動彈了。他還說,三十里外就是敵人,可我們卻在這里開晚會慶祝第三縱隊與一二〇師的會合,還要看戲。他的自信感染、鼓舞了所有在場官兵。
此時,有偵察兵來報,敵人的“掃蕩”正在逼近。但是,一二〇師戰(zhàn)斗劇社編演的三個獨幕劇依然上演著。因為特別,事后何其芳還記得其中一個劇目,是根據(jù)愛爾蘭格里戈瑞夫人的《月亮上升》改編的《軍火船》。晚會結束,大家才趕緊撤退。大約因為忙亂,這次賀龍和何其芳都出了一點小岔子。賀龍是在騎馬越一個坑時,馬失前蹄,把他摔了下來,口腔出血。何其芳卻是因為騎一匹生馬,剛出村口,馬突然亂蹦亂跳起來,把何其芳重重摔在地上。這一跤,把右胳膊摔脫了臼。到了住處請來醫(yī)生,醫(yī)生使勁硬將脫臼處拉直復原并掛上繃帶,何其芳又跟上了行軍隊伍。
不過,賀龍這一跤摔得可不輕,居然幾天沒出得了門。過了兩天,何其芳和沙汀去看望賀龍。只見賀龍?zhí)稍诖采希行┌l(fā)燒。他對何其芳和沙汀說:這兩天沒出大門,這在我是很少有的。我好動。看何其芳手臂摔了,他說了一句諺語:“乘船騎馬三分憂。”他說騎馬要經(jīng)過三個階段,起初膽小,后來膽大,出了亂子后又會小心起來。可以看得出來,賀龍是一個很善于在生活中總結經(jīng)驗的人。這種人,看去似乎沒讀過多少書,可卻是非常的聰慧。
接下來幾個月,部隊不停地在冀中與敵人戰(zhàn)斗。略微安靜下來,何其芳他們覺著老跟著司令部,總跟作客似的,便向賀龍要求具體工作。按照特長,他們被安排在了政治部宣傳部的編委會,主要是和幾個“魯藝”學生給部隊編教材和油印報。工作不忙時,他們?nèi)匀怀3Hニ玖畈咳ァR淮危R龍談到了在這里工作的加拿大醫(yī)生白求恩。他說,白求恩手術很好,并且工作很緊張,有時一個晚上要給十幾個傷員做鋸腿的手術。這些傷員大都不愿意把腿鋸掉,有的人哭叫,寧愿死也不愿手術。可是沒有辦法,這是救他們命的唯一的路子。說到這里,賀龍深長地說:你們文學家,應該去看看給這些傷兵鋸腿的情形!
賀龍這話的意思,是說文學家應該去看看,并表現(xiàn)生活中殘酷的一面。賀龍的這番話,師政委關向應也曾向何其芳等表達過。他說:戰(zhàn)爭,你們是應該去看看呵。戰(zhàn)爭是什么,戰(zhàn)爭是明知道那里是死,卻仍然要向那里沖過去。賀龍和關向應之所以說這些話,與他們看到這些文化人的弱點有關。
盡管如此,何其芳等文化人的弱點仍然顯露了出來。當最初的熱情隨時間消散,艱苦而單調(diào)的生活,頻繁的作戰(zhàn)行軍,讓“魯藝”的學員們吃不消了。他們多數(shù)提出要返回延安。這一舉動使得干部戰(zhàn)士感到不滿。這些長久以來一直戰(zhàn)斗在前線的工農(nóng)干部認為,要求回延安就等于怕艱苦。可“魯藝”師生卻解釋:文藝工作有兩種方式,一是一直在前方,為將來寫長篇小說搜集素材;一是來前方體驗生活,然后到后方寫作。他們就這樣以“藝術”的名義與工農(nóng)干部辯論。這在當時似乎都難說服另一方,可許久之后何其芳卻反思:我們忽視了抗日戰(zhàn)爭的前方需要文化人做宣傳工作,隊伍需要豐富的文化內(nèi)容給予滋養(yǎng),我們卻以“藝術”的名義逃脫開了。
三
1940年4月中旬,何其芳、沙汀及“魯藝”文學系的幾位同學離開了一二〇師。當他們?nèi)ハ蛸R龍道別時,賀龍明顯少了先前的熱情。他們離開前線的時候,正是敵人新的掃蕩期間,槍炮聲在不遠處轟響著,敵人燒毀村莊的火光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在這樣的背景下,何其芳一行,如同他后來描述的:“我們像打了敗仗的兵士一樣,踏上了歸途。”他們走到晉察冀,聽說一二0師在河間打了一場較大的戰(zhàn)斗,他們還聽到賀龍中了敵人毒氣的消息。
這次離開,一直到1942年,何其芳沒有機會再見到賀龍。可他聽說,賀龍有一次回到延安,表達了對文藝界的意見。賀龍對負責“魯藝”的周揚說,他不滿意“魯藝”當時的關門提高方式,把好學生好干部都留在學校里,不派到前方去;對于派到前方去的學生不夠關心,和他們聯(lián)系少,研究和解決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碰到的藝術上,生活上的問題不足。賀龍還親自到另一文藝機構“文協(xié)”去拜訪,歡迎那里的作家到部隊去……
賀龍的這些看法,何其芳是在經(jīng)歷了延安整風之后才比較明了的。他后來在一篇文章中說:“原來他是代表了無產(chǎn)階級和它的軍隊來向我們文藝工作者提出要求,來對我們這些小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提出抗議。”
當然,經(jīng)歷過生死戰(zhàn)火考驗的將軍,胸懷寬闊,并不會過多糾纏舊賬。不久,何其芳在一次聽報告時見到賀龍,他急忙向賀龍表達自己內(nèi)心的歉意,說先前在前方工作得不太好。賀龍卻大度地說:你們工作得很好嘛!
1945年春,聽說賀龍在柳樹店養(yǎng)病,何其芳與陳荒煤、舒群、嚴文井等幾位文學界同仁前去看望。賀龍很高興地接待。談著談著,賀龍說到了文藝家的本行。他說,你們“魯藝”過去的方針不對,后來搞秧歌劇,這就搞對了。現(xiàn)在是不是又稍微有點偏呢?只是搞秧歌劇,話劇搞得太少了。還有,秧歌也還要提高才行。他舉例說,當年春節(jié)看到“魯藝”演出的3個小秧歌戲,水平似乎沒有多少提高。
當時延安正在演出《三打祝家莊》。這是平劇院利用舊劇形式排出的一出新劇。賀龍說到自己的觀感:我去看過了,那真是人山人海,擠得很啊。你們看,這么長的戲,要演兩個晚上,為什么大家還是遠遠近近地搶著去看呢?這證明干部們需要看戲,需要看能娛樂又能獲得教益的戲。賀龍還談了一種情況,當時延安戲劇工作委員會在報上發(fā)表決議,不讓再演舊平劇。可賀龍在一些部隊中,仍然看到演出舊平劇的情形。他認為,只是不準演舊劇是不行的,要有新的劇本來代替。他并且希望何其芳等能把他的意見帶給“魯藝”負責人周揚。就在今天看來,賀龍的見解是樸素卻合適的。不顧群眾正當需求,強行排斥某些在人民中已經(jīng)有深入影響的活動,而沒有好的新的東西替代,這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
這大約是何其芳在延安期間最后一次見到賀龍。1945年12月,敵對勢力不斷在報紙上造謠說賀龍“負傷”甚至“戰(zhàn)死”,這令不久前與賀龍接觸過的何其芳十分憤慨。于是,他提筆寫下一篇《記賀龍將軍》的文章,記述了賀龍的精神情態(tài)及他人不及的能力。文章結尾,何其芳說:“我希望我這草率的敘述也能多少讓人看見,這個為食人的兩腳獸們所恐懼,因而就企圖用謠言來把他涂染得使一般人恐懼的賀龍將軍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然而,“謠言”只能惑眾,而迫害卻真正將一個活生生的肉體消滅。“文革”結束后的1977年,何其芳寫出一篇《我想起您,我們的司令員——懷念賀龍同志》的紀念文章,表達了對這位杰出的軍事領袖和革命家的由衷懷想。回顧何其芳與賀龍在那段特殊歲月的交往,應該說,賀龍的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相當深地影響了何其芳。他之后脫開了早期婉約的文風,寫出雄奇開闊的詩作,應該與此相關。賀龍對何其芳等人的歡迎接納,亦表現(xiàn)了對文化的尊重……這是那一時代人們的追求,表現(xiàn)了人類向往和平幸福的永恒渴望,這一更高層面的含義,也許更值得今天人們體味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