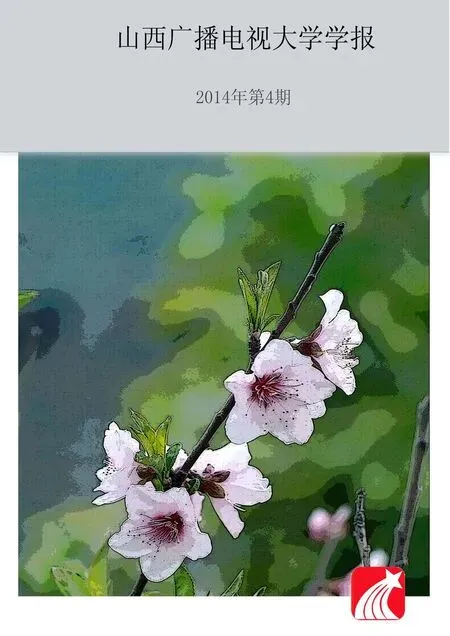《白鹿原》性別政治背后的民族命運——以田小娥形象為中心
□翟楊莉,胡嫣然
(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8)
“《白鹿原》的思想意蘊要用最簡括的話來說,就是正面觀照中華文化精神和這種文化培養的人格,進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運。”著名評論家雷達在小說問世不久,就如是精準評說了它的基本意蘊,作家本人也說自己的寫作是出于“關于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思考”,我們發現“作品中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形象的光彩之處恰在于她的矛盾性,或曰不徹底性,她不僅是小說中段重要的關聯性人物,不僅是具有反抗傳統的新人,同時也是傳統文化精神的產兒,考察這一“新”人形象身上的守舊性因素,辨析其中凸顯的性別政治關系與文化精神,不僅有助于我們對這一人物形象的深入理解,也能窺一斑而見全豹,進一步深入由作者提出的對“民族文化命運”的再思考。
一、被物化和打入另冊的“妖女”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開始關注“新人”形象,其“新”主要在于對舊世界、舊制度的反抗,就這點而言,田小娥不乏新人性,有論者就認為“她完全是一個蔑視封建舊道德的新的形象”,但這個人物形象復雜矛盾的一面更突出,她并非徹底的時代新人,而是新舊交替時期攜帶大量傳統文化“舊”原型基因的不徹底的“新人”,辨析其背后的文化原型,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外來妖女”、“依附男性的女人”、“婦人之仁”以及“復仇女鬼”等幾種,這些文化原型是這個人物形象的復雜性所在,原型之間錯綜復雜的對話關系也暗示著主人公所身處的社會文化走向的復雜性。
雷達先生認為貫穿全書的大動脈是由文化沖突所激起的人性沖突,具體表現為禮教與人性、天理與人欲、靈與肉的沖突。就田小娥而言,她身上突出的是自然人性、人欲、肉欲色彩,她的悲劇性命運從她作為女子誕生在這個世界上時就已開始。
無論是小娥的父親——屢試不第的田秀才,還是她的丈夫——年過七旬的郭舉人在對待她的態度上,和后來小娥命運的決定者白嘉軒、鹿三一樣,都是封建禮教文化堅定的守護者。他們信奉婚姻的存在就是為了生殖繁衍,為了傳宗接代,同時為了生育后代,借種也是這種文化默許的,只要面子上不難看就行。不獨如此,婚姻的存在還受傳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制約,而這二者又是基于門當戶對、條件相當的前提的,在這樣一種文化傳統中,女性就是“物”的存在,她的價值衡量標準就是婚嫁時換取她們的糧食棉花的多少。
小娥不能見容于這樣的文化傳統,一方面是她追求自然欲望滿足的私通行為傷風敗俗,挑戰了上述儒家文化倫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罕見的漂亮”這一原罪,這就是“‘美女禍水’的傳統性別歧視觀念在作祟了。田小娥僅因其外表就會被白嘉軒視為不是居家過日子的女人”,她的外形對男性形成了致命的誘惑,這種誘惑難免會引向人的自然本能的激情與放縱,這些對于信奉儒家節制為上的道德原則的白嘉軒之流來說是一種威脅,對付這種威脅的最好手段就是將之打入另冊,眼不見為凈。
我們這里不妨引入“性別政治”這個伴隨婦女解放運動和女權主義思想誕生的概念,一般認為,性別政治是“廣義層面上對兩性關系作正式闡述的名詞”,可認為是“兩大性別集團之間的權利關系和結構”,在中國傳統男權制的背景下,性別政治特指“將女性排斥于公共政治生活之外,并逐步形成的一系列使女性與政治隔離的禮法、規則與政令等正式制度”,具體表現在“男主外女主內”、“男公女私”以及“男尊女卑”等習慣性觀念。這種剝奪女性公眾政治生活權利的常用手段就是動用意識形態工具將之打入另冊,隔離于主流社會之外,小娥的遭遇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更可怕的是,這種觀念會潛移默化在受害者身上,后者即便有機會進入公共政治領域,仍然擺脫不了這種傳統影響。
二、對男性世界的依附
田小娥就是擺脫不了這種傳統影響的女性之一,這不僅表現在她傳統家庭生活的向往,她對男性世界的依附是這種傳統守舊性更突出的表現,她反抗這個世界的不徹底性歸根結底也是因為對性別的依賴。
換句話說,田小娥是不徹底的新人,“新”的一面是她身上源于天性以及自然本性的對個人不公命運的非理性反抗,這一反抗由將郭舉人的養生妙藥扔進尿壺開始,到魂魄借鹿三之嘴的控訴達到高潮。我們不妨考察被迫逃亡后小娥在原上的生存經歷,不難發現這時主導她命運的還是她身上根深蒂固的“舊人”性,作為女性她以為男人天然是自己的依靠:不論是與黑娃吃糠咽菜、鬧農運,還是對黑娃和白孝文那句動情的“你走了我咋辦”,抑或是黑娃逃亡后委身鹿子霖,都體現出這種依附性。依附男性世界的資本就是她作為女性的身體和美貌:黑娃農運失敗,被迫逃亡,她想用自己的美貌賄賂鹿子霖換取黑娃的安全,被鹿子霖一步步引入圈套后,又試圖用性來拴住鹿子霖,把他作為自己的靠山,保障自己的安全。在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時,她自覺把自己擺在了“破罐子破摔”的位置上,這何嘗不是對傳統文化秩序的認可呢?成功勾引白孝文之后,二人同病相憐,在饑饉中的世外破窯狂歡,充其量是對將二人排除在外的文化制度的消極抵抗。小娥這些依附男人的行為充分體現出“社會性別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借助道德信仰、風俗習慣、主流意識形態等傳承和延續的載體,使男尊女卑、男公女私、男外女內的性別價值觀不斷深入人心,成為人們心目中定型化的性別觀念,也使女性更加默認自身的卑賤地位與身份”。歸根結底“田小娥本質上是一個傳統女人,她渴望守婦道,但社會、時代、家族、命運都不給她機會。她只能用極端的方式反抗:用自己的肉體去誘惑、破壞那貌似神圣的禮教。但在破壞的過程中她時時又回到傳統女性的狀態,只是這狀態維持不久,又被外在的壓力擊碎。”
三、善與“惡”的交織
田小娥不乏傳統女性的善良,更不乏天真。善良之處在郭舉人家對待眾長工的舉止就可見出一斑,作為工具被鹿子霖利用并成功地抹下了族長繼承人白孝文的褲子之后的舉動更能見出她的善良:她同情對方什么也沒做卻喪失了包括名譽在內的一切,白孝文之后的墮落,小娥最初受人蠱惑的誘惑和二人之后同病相憐在墮落之路上的共同下滑,對白孝文的終極命運而言只不過是一個推手罷了。田小娥是傳統性別政治的產兒,她身上不乏傳統女性因為大門不邁二門不出而導致的善良天真無知的一面,她對白孝文的啟蒙(沉迷大煙,不要臉就行)更多是出于天真的無知,男性如白孝文之流,卻由于自己對政治事務的天生敏感與參與,自會從這種啟蒙中舉一反三。
田小娥身上還有天真的“惡”的一面,小說第25章,她借鹿三的身體聲言席卷原上的瘟疫是她的復仇之舉,這一轟轟烈烈的反抗行動顯然攜帶著大量傳統“女鬼復仇”原型基因,但不同與傳統的女鬼報復對象主要指向迫害自己的具體人物,田小娥的打擊面要廣得多,就算白鹿原上的男女老少都不拿正眼看她,是迫害她的愚昧“大眾”,用瘟疫奪去他們的性命也著實殘忍;尤其當我們思及文中詳細敘述的鹿惠氏、仙草之死時,是不是有“相煎何太急”之感呢?
再者,如果說白嘉軒用“一座六棱磚塔”把小娥的尸骨“燒成灰壓在塔底下,叫她永世不得見天日”,是“男權至上的思想對女性生命力、女性自主精神的壓抑與摧殘”的話,我們不應忘記小娥借鹿三的口提出的要求,尤其其中“修廟塑身”的要求,更是體現出復雜的文化心理。這個要求激怒了白嘉軒和朱先生,因為這動搖了他們敬神敬祖的傳統和他們秩序井然的價值體系,也難怪二人會想出“鎮妖塔”這個主意。在我們文化傳統中,最有名的鎮妖塔是法海加在白娘子身上的雷峰塔,但環顧整個白娘子的傳說,白娘子只不過是以妖的身份渴慕人間的生活,從來不曾想過要修廟塑身,將自己神化。所以我們不妨說,田小娥命運悲劇中確實不少令人唏噓之處,但她也是浸淫了封建社會的惡的,生前的自輕自賤與死后借助超自然力量欲求“修廟塑身”是一對矛盾,也是她身上惡的體現之一。
無可否認,小娥的打擊報復浸潤著她對自己屈辱一生的憤怒,看似邪惡,卻體現出她孩子般的天真。我們不妨說,這種天真的報復恰恰反映出她反抗的不自覺,正如魯迅在《熱風·隨感錄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中的精辟論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很慰安。”活著飽受封建禮教摧殘,變成鬼便想嘗嘗那種被尊敬甚至被崇拜的快感。
我們不否認田小娥這個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身上具有反抗性的“新人”的一面,但當我們無條件地肯定她的抗爭行為的合理性的時候,甚至認為她是一個“一定要活成一個心理、人格獨立而完整的女人”,并因此指責作者基于男性立場的偏頗和虐待時,我們不應忘記這個人物形象身上折射出的帶有濃厚傳統和時代特色的性別政治色彩,這也是陳涌先生概括白鹿原“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方式意義所在,與其說《白鹿原》是文化保守主義,為儒家傳統文化招魂,不如說它表現出了作者對儒家文化頗為復雜的態度:既有對傳統文化的贊賞和惋悼,也不乏對傳統劣根性的批判。而田小娥以及小說中眾多女性人物最終的悲劇結局,以及象征著白鹿原上封建禮教旗幟的白嘉軒的存活,是作者在昭告我們,民族命運的改變需要外來的力量,傳統內部的反叛攜帶著過多舊世界似是而非的因素,注定是無效的。
[1]雷達.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J].文學評論,1993,(6):108.
[2]陳忠實.白鹿原創作漫談[J].當代作家評論,1993,(4):20.
[3]朱寨.評《白鹿原》[J].文藝爭鳴,1994,(7).
[4][11]楊一鐸.“女性”的在場“女人”的缺席——《白鹿原》女性形象解讀[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14,(1):62.
[5]王國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權思想——基于“性別政治”視角的解讀[J].福建論壇,2011,(12):21.
[6]李曉廣.論傳統中國性別政治關系的制度演進——一項基于新制度主義的分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13,(1):92-98.
[7]李曉廣論傳統中國性別政治關系的制度演進——一項基于新制度主義的分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13,(1):92-98.
[8]楊光祖.田小娥論[J].小說評論,2008,(4):95.
[9]田煒,孟慶千.男權意識下女性的悲劇——淺析《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J].菏澤學院學報,2008,(4):24.
[10]魯迅.熱風[M].南京 :譯林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