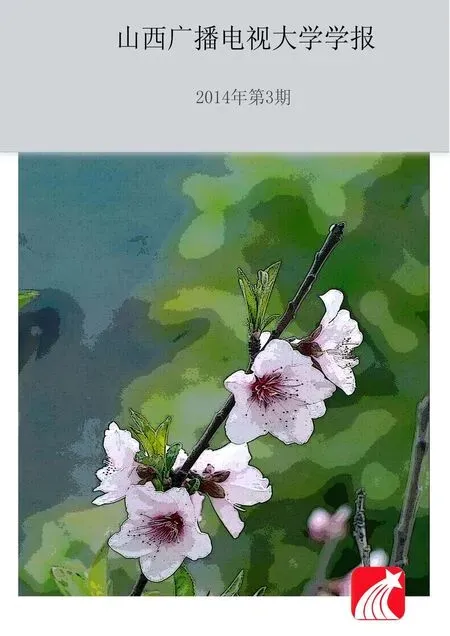公共空間與話語權的選擇—— 《莽原》周刊的緣起與莽原社的形成
□張 勇,陳 歡
(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1331)
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僅因其小說和雜文創作而引人注目,事實上,魯迅創作的大量雜文得益于他致力于編輯和創辦的期刊。“魯迅一生編輯過的刊物共有十九種之多。”[1]留學日本期間創辦的《新生》因各種原因以失敗而告終,新文化運動興起,魯迅參與《新青年》、《語絲》等期刊的編輯出版活動,直到1925年4月24日由魯迅主編的《莽原》周刊正式創刊,作為魯迅實踐編輯思想與辦刊方針的第一個刊物,他非常重視《莽原》的編輯與出版,在與許廣平的通信中,魯迅常常提及近來因為編輯刊物的事弄得疲憊不堪,原因在于除了自己要撰稿外,許多來稿還得親自動筆修改。《莽原》時期,魯迅發表了《燈下漫筆》、《春末閑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答KS君》等重要雜文,他的小說《弟兄》、《鑄劍》和《奔月》以及《朝花夕拾》集子里面的文章都曾發表于《莽原》。《莽原》為魯迅早期國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和雜文文類形成提供了話語空間。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自敘莽原社及《莽原》周刊的產生的原因時說:“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現,這其實不過是不滿于《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群,另設《莽原》周刊,卻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2]p88。根據魯迅先生的說法,《莽原》周刊作為對《京報副刊》編輯群的不滿而產生的刊物,卻仍附《京報》發行,仔細探究個中緣由,其實是關于創辦《莽原》周刊,魯迅先生當時還在計劃之中,而《京報》卻倉促的刊登了出版廣告,并把魯迅先生編輯的刊物稱之為改造青年思想的利器,雖然魯迅先生后來又親自撰寫了一份《莽原》出版預告進行刊載,《京報》編輯部卻妄加案語,更加導致魯迅對《京報》編輯部的不滿。頗為吊詭是,《莽原》周刊對《京報》編輯群的不滿的產物,卻仍能附《京報》發行,這與《京報》的創辦者邵飄萍開放的辦刊思想密不可分。邵飄萍獨立自主的辦刊方針是《莽原》周刊形成的前提條件,聚集在魯迅周圍的一批文學青年提供了人才,魯迅對改革社會現狀的思考與對當時期刊現狀的不滿都是《莽原》周刊的緣起與莽原社的形成原因。
孫伏園因抽稿風波憤而辭去《晨報副刊》的編輯一職,當時《京報》的編輯邵飄萍聽說這件事后就來找孫伏園,準備在《京報》辦一個副刊,“我覺得《京報》的發行量不抵《晨報》,日常不過三四千份(《晨報》近萬份),社會地位也不如《晨報》,很不想去。但魯迅先生卻竭力主張我去《京報》,他說,一定要出這口氣,非把《京報副刊》辦好不可。”[3]p35在魯迅的支持下,孫伏園接手《京報副刊》,果然不負魯迅期望,由于孫伏園的組織和努力,《京報副刊》有了一個相對穩定,自成一家的作者群,如文學撰稿人有魯迅、周作人、許欽文、荊有麟等人。隨著《京報副刊》的影響與日俱增,發行量也隨之擴大,甚至一天出現增加兩千戶以上的訂戶,印廠不得不加班趕印,隨時增加送報人的情況。在這樣的情形下,邵飄萍及時創辦了二十多種副刊,涉及文學藝術、社會問題、經濟研究、教育、語言文字等領域,適時擴大了《京報》的影響范圍。孫伏園出于對《晨報副刊》的反擊而答應編輯《京報副刊》,正是因為他出色的編輯實踐使得《京報》能重振旗鼓。在孫伏園的編輯下,《京報副刊》一躍而起與當時的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晨報副鐫》并稱為五四時期的“四大副刊”。為了搶占更多的公共空間,掌握主導話語權,邵飄萍邀請當時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團體或社會賢達如魯迅等知名人士一起主辦刊物。同時他也大肆宣揚其開明自由的辦刊宗旨:“邵飄萍辦副刊,之所以堅持副刊言論自由,無須與京報一致原則,一方面是他始終持一種新聞觀點,即認為報紙是‘社會公共機關’,是國民輿論機構,因此,‘社會各方面之思想言論無一致之必要’。同時也是為了擴展思路,‘乃欲使讀者擴其思想眼界,勿為一方意見所囿,故必須發揮各團體思想言論之特色,以供讀者之詳參。’而最重要的,則是開辟新的陣地,為新文化運動鼓與呼,為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鼓與呼,造成進步的輿論聲勢,以沖擊反動的、腐朽的輿論氛圍。”[3]p35《莽原》周刊作為《京報》附刊而非《京報副刊》,從而具有相對獨立的自由的編輯思想及體例與邵飄萍“各種附刊上之言論,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與本刊無須一致,本報編輯部從不對于各附刊上參加一字”[4]p40的辦刊思想密切相關。依附于《京報》發行而不必執行《京報》編輯者的思想的主導,依靠《京報》充足的經濟實力支援,魯迅和高長虹、向培良等能自由的實踐著自己的編輯思想。可以說正是邵飄萍這樣“集合在民主、科學、自由、獨立等寬泛而模糊的旗幟下從事啟蒙事業的”[5]p133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報人的影響,《莽原》周刊才得以有存在的前提條件。《莽原》除隨《京報》附送外,還由《京報》增印了3000份,由北新書局和李少峰代賣,賣的錢即作為撰稿人的稿酬。《京報》為《莽原》周刊提供了實踐場域,邵飄萍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之所以要創辦《莽原》周刊,魯迅后來回憶說因為有幾位青年文學愛好者的文章不能在副刊盡量發表“所以另外創立一個周刊,附在《京報》上。”[6]p95魯迅素來與青年來往密切。不僅對青年的創作進行悉心指導,還在生活方面給予青年有力的幫助。當時團結在魯迅身邊的青年有高長虹、高歌、尚鉞、向培良、荊有麟、韋素園、葦叢蕪、李霽野等人,高長虹自1925年與魯迅結識后,深得魯迅賞識,直到和魯迅交惡之前的一年多時間里,曾去過魯迅家七十多次,可見他與魯迅關系的密切。從生理年齡來看,這群文學青年中高長虹當時27歲、向培良20歲、章依萍25歲、韋素園23歲。他們都是剛剛步入社會的文學愛好者,在當時北京文學傳播的公共空間尚無立足之地。高長虹本來有出國的打算,曾經試圖求援于孫伏園,迫于窘困只得作罷,而韋素園等人則常被迫賣文和典當衣物以解斷炊之虞。這群青年很希望魯迅出來“做點事”,他們想借魯迅當時在北京出版界的名望希望獲得一席話語空間,使得他們的創作能自由地發表,而就是這些剛踏上社會的純真富于活力的文學青年,這群對黑暗現狀的挑戰者成了魯迅理想中的破壞者。這正符合了魯迅的想法,魯迅不僅想自己編輯一個刊物的愿望,他對當時刊物的現狀也不滿意,他理想中的刊物應以“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實踐為主,而當時的刊物如《京報》的有些周刊多載關于花草或旦角之類,已入于無聊庸俗一流了。于1925年3月間創刊的《猛進周刊》倒不失其勇,而談論新聞政治的文字卻又太多。加之投稿到報館也很不順暢,稿子投到報館,能不能刊發多半要靠運氣,魯迅道出了其中的緣由“一者編輯先生總有些糊涂,二者投稿一多,確也使人頭昏眼花。”[7]p471-472北京的出版物,使魯迅真正滿意的很少。因此,他決意自己動手編輯一本刊物,意在踐行“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以撕去舊社會的假面,打破“黑染缸”。有了戰斗者和辦刊的想法。《莽原》周刊就自然順勢而生。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當時被稱為“語絲”主將,卻仍然另外創辦了一個刊物,除了上面提及的原因外,還與魯迅與當時《語絲》的關系有關,魯迅多次給許廣平的信中表示自己只是作為《語絲》的投稿者而存在,并沒有實質上的編輯權利,而且語絲同人每月的聚會魯迅也一次都未參加,這自然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魯迅與語絲同人關系的疏遠,其實魯迅與《語絲》關系頗為復雜,魯迅雖然身為《語絲》的發起人之一,然而魯迅對于人們給他的“語絲主將”的稱號是很反感的,原因之一大概在于此:實質上《語絲》還是“他們的”。魯迅曾經推薦幾篇青年作者的稿件到《語絲》,最終無果而終,可見魯迅并沒有多少話語權。從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與傳媒的關系看,五四時期正因為有了《新青年》、《申報》、《語絲》、《莽原》等等大量報刊,知識分子才有了發言的陣地。“五四”先驅通過報刊雜志宣傳自己的自由民主獨立觀念,魯迅也正是通過創辦《莽原》周刊實踐“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的編輯思想。《莽原》周刊的成立對于魯迅來說,意義不僅在于是他編輯思想的完整實踐,也是他批評話語空間開創的實踐,雖然之前的《新青年》、《語絲》《京報副刊》等都是廣泛意義上的魯迅批評話語實踐的實踐場域,實際上,魯迅對這些刊物是不太滿意的。他理想中的刊物是專以“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為職事,倡導一種“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的韌性戰斗精神,呼吁打破“酷烈的沉默”,讓真的憤怒“像火山巖漿般地爆發出來”。“跟著《語絲》《莽原》的出版,魯迅戰斗的姿態,越來越顯明起來。”[8]p472從莽原時期開始,魯迅更深入地實踐了關于國民性的思考與批判。
莽原社相伴著《莽原》周刊的產生而形成一個松散的群體,并無統一的集社和宗旨,主要成員是當時團結在魯迅身邊的一群文學青年,這群青年有部分作為積極撰稿人而存在,隨著《莽原》周刊的停辦莽原社解體也在所難免,《莽原》周刊于1925年11月停刊,1926年1月,魯迅再辦《莽原》半月刊,改由未名社出版,遂與《京報》脫離了關系。同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后,《莽原》交給了韋素園編輯,莽原內部發生了“稿件風波”,向培良的稿子投到《莽原》半月刊未被主編刊發,隨后高長虹寫了一系列文章責罵魯迅,導致了“亞拉藉夫與綏惠略夫”的交惡,最終《莽原》半月刊于1927年12月終刊。《莽原》周刊創辦后,不僅發表本社同人的作品,而且也注重發表一批名不見經傳的青年文學愛好者的作品,先后發表了文炳(廢名)的《河上柳》、靜農(臺靜農)的《死者》、《鐵棚之外》;許欽文的《老婦和少年》;劉夢葦的《竹林深處》、《倚門的女郎》、詩人朱大枏、章衣萍、景宋(許廣平)等人的多篇作品。莽原的開放性為青年文學愛好者提供了一個話語表達的空間,培養了高長虹、高歌、向培良等有影響的青年作家,這批青年知識分子的參與也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成果。《莽原》周刊雖然辦刊時間比較短暫,然而《莽原》是新文學青年獲取話語權與公共空間的一個典范,現代文學的產生與傳媒緊密相關,而文學傳媒的實質就是話語權的爭奪,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如果從爭取‘公共領域’和知識分子話語權的角度來看,20年代的魯迅更愿意通過報刊參與激烈的思想文化斗爭中,在話語權的爭奪中實現自己的文化理想。”[9]p165值得注意的是,《莽原》是文學青年為了爭取話語權而創辦的一個刊物,它的解體也是因為莽原社內部成員之間為爭奪話語權,這一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個典型的文學與傳媒即公共空間與話語權的選擇的范本,考察《莽原》周刊成立的原因,使我們對于文學傳播的實質—公共空間與話語權有了深刻的認識。
[1]劉增人.論魯迅系列文學期刊[J].魯迅研究月刊,2005,(10).
[2]劉運峰.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3]孫伏園,孫福熙.魯迅和當年北京的幾個副刊.孫氏兄弟談魯迅[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4]孫曉陽.附刊上言論之完全自由.邵飄萍[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5.
[5]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M].北京:三聯出版社,2006.
[6]許廣平.魯迅和青年們[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7]魯迅.魯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8]陳漱渝主編.一個都不饒恕—魯迅和他的論敵[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
[9]周海波,等.傳媒與現代文學之間[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