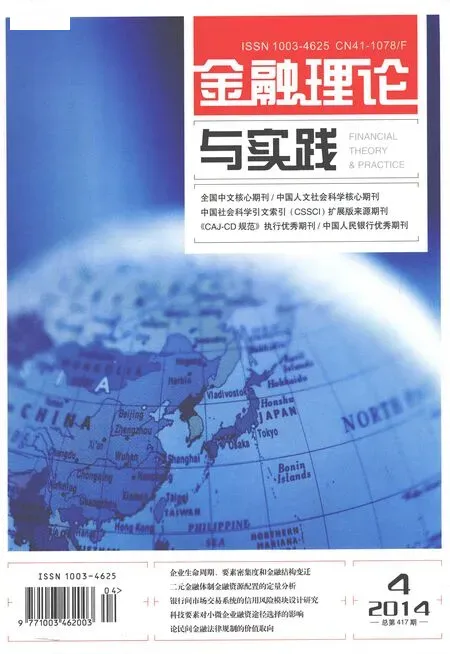結構轉型與中國潛在增長率變動分析
管曉明
(中國人民銀行 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800)
潛在增長率和產出缺口是宏觀經濟學中的重要概念,對于評估經濟形勢、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社會轉型加快等多種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增速呈現回落態勢,有關潛在增長率是否已步入下行通道的討論日趨激烈。由于理論界對潛在增長率的概念尚未達成統一,測算方法也不同,導致測算結果存在較大差異。
一、潛在增長率內涵及測度方法
(一)潛在增長率的定義及理論基礎
通常認為,潛在增長率是一國(或地區)各種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情況下經濟實現最大產出時達到的增長率,其高低僅取決于供給方面。由于對資源充分利用的理解不同,導致對潛在增長率的界定也不同。Okun(1962)[1]將資源充分利用與失業率相聯系,認為潛在增長率是勞動力充分就業時的產出增長率。Phelps(1967)[2]、Kuttner(1994)[3]將資源是否充分利用與通貨膨脹相聯系,將潛在增長率界定為通貨膨脹水平比較穩定或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狀態下的產出增長率。Masi(1997)[4]等將潛在增長率看作不引發通貨膨脹情況下經濟所能取得的可持續的最大產出增長率,它反映了經濟供給方面的情況。近年來,學者們傾向于同時考慮供給和需求因素的影響,將潛在增長率定義為供求平衡時的產出增長率。如Mishkin(2007)[5]從美聯儲維護價格穩定和最大可持續就業雙重目標角度,將潛在增長率看作與最大可持續就業水平一致時的產出增長率,此時經濟中包括總供求在內的所有變量均處于平衡狀態,通貨膨脹趨于其長期期望值。現代經濟學理論則將均衡增長路徑即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水平和趨勢水平視作潛在增長率。
對潛在增長率的不同定義,源自宏觀經濟理論對經濟周期波動的不同理解。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中總供給相對穩定,“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使實際產出小于充分就業時的產出,將潛在增長率看作經濟中各種投入要素充分利用,特別是失業率僅為摩擦性失業率時的最大產出對應的增長率水平,該增長率僅取決于供給方面。新古典理論在理性預期、價格完全彈性、市場能連續出清等假設下,認為潛在增長率是在給定實際約束條件和不引起通脹率改變條件下經濟能持續實現的產出對應的增長率,可以從供需兩方面界定。如Darren Gibbs(1995)將潛在增長率看作通脹率穩定狀態下總供求相等時對應的產出增長率水平,動態看經濟潛在增長率與可持續增長率通常可以互用,產出缺口則體現了經濟富裕生產能力或可擴張能力,此外實際經濟周期及技術水平變動都會使潛在產出發生變動。新凱恩斯主義理論認為,價格和工資粘性使其不能迅速及時地隨總需求變動而調整,市場出現供求失衡后,產品和勞動市場難以迅速調整到市場出清水平,經濟處于持續非均衡狀態。Frederic(2007)基于新凱恩斯主義DSGE模型將潛在增長率界定為當不存在工資和價格粘性即具有完全彈性時的產出增長率。長期內工資和價格將趨于均衡水平,因此DSGE模型與通脹水平不變的潛在增長率定義基本一致。

表1 潛在增長率測算方法比較
(二)潛在增長率測算方法
由于對潛在產出的定義、依據的理論模型以及具體技術方法上各不相同,測算潛在增長率的方法也存在差異,常用方法如表1所示。
從表1可知,估計潛在增長率的各種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優劣。考慮到生產函數法不僅有相應的理論基礎,而且能分別考察不同生產要素對潛在產出的影響并進行結構分析,IMF、OECD、ECB[6]等主要國際機構大都采用生產函數法進行測算,國內學者也用生產函數法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階段的潛在增長率進行了研究測度(沈利生,1999[7];郭慶旺等,2004[8];黃梅波等,2010[9];楊國中等,2011[10];于洪菲等,2013[11])。由于生產函數法以生產技術、產業結構等宏觀經濟變量穩定為前提,潛在增長率僅受包括技術在內的要素供給端的影響,這對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生產要素發生深刻變化、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中國而言其局限性日益凸顯,用該法進行預測時更加值得商榷。因而,本文試圖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動力結構及產業結構變動、區域發展差異及城鎮化進程等結構性影響因素納入生產函數模型,以期對中國潛在增長率進行更加合理的預測。
二、對中國潛在增長率的測度
采用生產函數法對中國1952—2012年的潛在產出和潛在增長率進行估計,選取標準的C-D生產函數:Yt=。其中,Yt表示實際產出,Kt表示實際資本存量,Lt表示就業量,α和β分別表示資本產出彈性和勞動產出彈性。對上式兩邊取對數可得:lnYt=lnA+αlnKt+βlnLt。若生產函數滿足規模報酬不變特征,即α+β=1,則上式可改寫為:ln(Yt/Lt)=c+αln(Kt/Lt)+εt,其中殘差εt為全要素生產率。
運用生產函數法對潛在產出和潛在增長率進行估計,需首先對模型中的Kt、Lt和εt三個生產要素進行估計。
(一)資本存量的估計
永續盤存法(Goldsmith,1951)作為測度資本存量的基本方法,被OECD國家廣泛采用,國內學者也大都采用該法,基本公式為:Kt=It+(1-δt)Kt-1。其中,K、I和δ分別表示對應年份的資本存量、新增投資和資本折舊率,對投資進行不變價格折算,可得:Kt=It/Pt+(1-δt)Kt-1,其中Pt為固定資產折算指數。
由于中國固定資本存量數據未納入統計,因而采用推算法確定。投資指標的選取,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王小魯、樊綱,2000)、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何楓,2003)、新增固定資產(Holz,2006)等不同口徑,這里選取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作為投資指標的替代,該指標既可涵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的投資,又有效避免了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測度上的偏差。對于折舊率δt的選取也存在分歧,如采用5%(王小魯、樊綱,2000)、9.6%(張軍,2004)、6%(李宏瑾,2008)、6.67%(黃梅波,2010)的折舊率,而 Holz(2006)則采取了折舊年限為15年的折舊率。針對我國經濟建設不同時期固定資產更新改造速率存在差異的特征,本文對δt采取分階段賦值方式,1952—1977年賦值0.07(折舊年限大約15年),1978—1991年賦值0.09(折舊年限大約12年),1992—2012年賦值0.10(折舊年限大約10年),這與新中國成立后不同歷史時期固定資產更新改造進程大致接近。對于固定資產折算指數Pt的選取,1990年以后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來表示,1952—1989年因無對應的統計指數,綜合比較后選取與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變動最為接近的第二產業GDP平減指數來替代,并統一折算為以1952年為基期的定基指數。
(二)潛在就業的估計

表2 1952—2012年標準生產函數回歸分析
此外,鑒于中國經濟受改革等制度變量影響顯著,在模型中加入Mt和Nt兩個虛擬變量,將整個時間序列劃分為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1978—1991年改革開放初期、1992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并不斷完善三個階段加以考察。這樣,計量模型可以寫為:lnYt=lnA+αlnKt+βlnLt+Mt+Nt+εt。將1952—2012年中國相應宏觀經濟數據代入模型用OLS法回歸,結果見表2(I)。
對上述模型進行Wald檢驗,接受α+β=1的假設,即可以斷定中國宏觀生產函數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特征,即ln(Yt/Lt)=c+αln(Kt/Lt)+Mt+Nt+εt。根據轉換后的模型重新進行回歸檢驗,結果見表2(II)。從(II)的回歸結果看,模型各參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DW值=0.2589,表明模型殘差存在序列相關。通過ADF單位根檢驗可知,該回歸結果殘差存在單位根,但二階差分后不存在單位根,表明該模型具有穩定的二階協整關系,在回歸模型中加入AR(1)和AR(2)重新回歸,結果見表2(III)。從(III)的回歸結果看,模型因變量回歸系數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提高,DW值=1.7238,自相關問題得以解決。由此可知,中國宏觀經濟中資本的產出彈性α=0.7996,勞動的產出彈性β=0.2004。值得注意的是,與不考慮自相關時資本的產出彈性α=0.6061相比,彈性明顯提高。
(三)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估計
根據回歸模型ln(Yt/Lt)=c+αln(Kt/Lt)+εt,得到TFP=e[ln(Yt/Lt)-0.7996ln(Kt/Lt)],代入相關年份對應數據,可得1952—2012年中國TFP時間序列數據(見圖1)。

圖1 1952—2012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變動趨勢圖

表3 1952—2012年中國潛在產出及潛在增長率估計情況
圖1顯示,1952—2012年期間中國TFP呈現周期性變動特征。從TFP的絕對值看,上世紀60年代之前,TFP處于歷史較高水平,這與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范圍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密切相關,這兩大措施極大地釋放了農業和城鎮工商業的生產力。歷經三年自然災害和“文革”對經濟的破壞,TFP在改革開放前降到歷史低值。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TFP重新步入上升軌道,并于2005年達到最高點,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TFP重新步入下行周期。從TFP變動率情況看,除三年自然災害和“文革”等個別年份外,1952年至1984年期間,中國TFP增長率大致呈上升態勢,而1985年以來,中國TFP則呈現持續回落態勢,特別是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TFP增長率呈現由正轉負的轉折,表明近年來TFP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趨于下降。
(四)潛在產出增長率的測算
根據上面估計出的實際資本存量、潛在就業量和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對中國1952—2012年潛在產出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3。
圖2顯示,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際經濟增速和潛在經濟增速均呈現高增長、高波動特征,經濟發展基礎不穩定,易受外部因素沖擊。改革開放后,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潛在增長率的穩定性顯著增強,表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經濟抵御外部擾動的能力也不斷提高。近年來,中國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并非勞動力增長下降造成的,相反,資本存量和潛在就業量仍呈現不斷增加態勢,反映技術進步和效率改善的TFP持續下降成為導致潛在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因素。因而,通過深化改革發揮制度紅利、提高技術進步及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成為避免未來潛在增長率大幅下行的重要途徑。
三、影響潛在產出的結構因素分析
前面從供給層面構建總量生產函數模型,分析了資本、勞動投入和以技術進步為標志的TFP變動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由于生產函數法要求經濟結構相對穩定,無法將生產和需求結構變動以及周期性因素納入模型,因而對處于經濟快速發展、產業結構面臨轉型升級、城市化步伐加快、勞動力供求結構發生顯著變化的中國而言,相關結論有待進一步商榷[12],這也是現有研究普遍忽視的問題。因而,下面著重分析結構變動因素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

圖2 1952—2012年中國潛在增長率及實際增長率變動趨勢圖
(一)經濟增長率在人均GDP達到一定高度后面臨回落壓力

表4 二戰后德國、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人均GDP與GDP增速變動情況
20世紀以來,世界上多數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地區)大都經歷了二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期,隨后轉入經濟增速明顯回落期。通過對這些國家(地區)經濟增速與人均GDP變動關系的歷史數據分析可知,各國(地區)通常在人均GDP達到1萬—1.1萬國際元(1990年國際元)前后經濟增速出現明顯回落。根據IMF預測,中國人均GDP將在2017年前后達到1萬國際元的臨界水平,按照發達國家(地區)一般規律,如果中國經濟不出現大的調整和不利沖擊,那么可以粗略預測,中國潛在增長率將在2017年前后出現由高速向中速回落的轉折。
(二)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轉換對潛在增速產生重要影響
一國經濟增長模式及增長動力結構的變動,長期內會通過需求方影響其經濟增長潛力。從中國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變動情況可知,改革開放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不斷上升態勢,2012年達到56%,較改革初提升了22個百分點,投資已超過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基礎設施薄弱、資本相對于勞動力短缺時增加投資可有效緩解相關瓶頸制約,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過度投資引發的產能過剩、投資邊際效率下降等問題,對傳統粗放型、以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提出挑戰。從凈出口看,此次金融危機前中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處于較高水平,1986—2005年間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超過10%。隨著加入世貿組織制度紅利消退及國內生產和出口成本的不斷提高,在生產率未根本提升的前提下,單純依靠低成本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將不可持續。從國內消費看,長期過度依賴投資和外需的發展模式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下降態勢,當前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一步抑制了居民收入增長和消費能力的提高,消費對國民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拉動作用難以釋放。

圖3 中國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三)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

表5 近年來中國三次產業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變動情況
經濟增速通常伴隨產業結構的變化呈階段性變動特征。經濟高速增長期,工業產出比重往往呈上升態勢并保持在較高水平;隨著工業產出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相應上升,經濟增速也相應經歷由升轉降的過程。二戰后,日本、韓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工業增加值比重都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經濟增速也相應呈現先高后低的變動軌跡。從中國三次產業比重情況看,近年來第二產業占比大致穩定在45%左右的水平,而第三產業則隨著第一產業比重下降呈顯著上升態勢。由于不同產業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不同,第三產業ICOR顯著高于第一產業,表明未來隨著第三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比重的不斷提高,經濟增速下滑的壓力也將不斷增大。此外,近年來中國三大產業ICOR總體均呈上升態勢,表明各產業投入產出效率已處于下降通道,在TFP難以大幅提高的背景下,經濟增長減速壓力加大。
(四)區域發展差異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潛在支撐

圖4 東部地區GDP比重及三大地區GDP名義增長率趨勢變動
中國作為地域廣闊的發展中大國,東、中、西部地區在資源稟賦、發展水平和條件上存在顯著差異。改革開放后,東部地區在政策和區位優勢下獲得率先發展,帶動了全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東部地區率先出現產業升級轉型,第三產業占比逐年上升使該地區經濟增速回落,而中西部地區承接了更多的東部轉移工業,第二產業產值比重顯著提升,為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提供了產業條件。此外,鑒于中西部地區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有更大的投資空間,2001年西部大開發以來,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趨勢性上升態勢更加顯著,2005年開始增速領先于東部,特別是伴隨東部地區GDP占比下降、中西部地區GDP占比不斷上升,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提速為中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仍保持較快增長提供了支撐。
(五)城市化進程是影響未來潛在增長率變動的又一重要因素
城市化通過帶動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引發產業升級、轉移就業、加快消費升級等效應對經濟增長產生持續性影響。從二戰后日本、韓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經驗看,各國城市化與工業化大致同步進行,城市化快速上升期也是經濟增長加速期,城市化水平停滯期則是經濟增速回落期。二元經濟下中國城市化長期滯后于工業化,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工業化放緩和城市化進程加速,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缺口已顯著收窄,但中國城市化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由此帶來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增加、傳統產業向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轉型升級以及就業結構轉移和消費需求升級等外生增長動力依然較大,城市化仍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四、對中國未來潛在增長率變動的預測及建議
上面考察了結構變動因素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因而,可以在對生產函數中各投入要素變動趨勢預測的基礎上,對中國未來10年潛在增長率進行估算,并結合結構變動因素對預測結果加以修正。各主要變量變動趨勢如下:
從勞動力變量看,未來10年中國潛在勞動人口總量將先穩中略增,2015年達到峰值后小幅減少。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人口出生率如果保持當前水平不變,中國15—64歲人口將在2015年達到9.95億人的峰值,2020年為9.89億,2025年為9.81億,2020年勞動人口占比僅比2015年下降1.75個百分點,但勞動力總量仍將比2010年增加1840萬人,考慮到中國已開始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勞動產出彈性相對較低、勞動技能效率及資本對勞動替代率將不斷提高等因素,未來10年中國勞動力數量變動對潛在產出的影響有限。
從資本存量變動看,中國當前較高的投資規模與應對危機的經濟政策有關,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但資本存量尤其是人均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考慮到未來5—10年中國將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產業結構的區域間轉移、節能高效產能對落后低效產能的替代等都將加快,城鎮化推進對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投資需求仍將保持強勁,技術進步將加快資本更新折舊速度,總投資水平短期內難以大幅放緩。鑒于近五年資本存量的平均增速為14.5%,因而可以預測未來10年中國資本存量增速將緩慢下降,但仍能保持較高水平。
從TFP變動情況看,2005年以來中國TFP呈現逐年下降態勢,近五年均值為0.3154,年均下降0.6%,“強政府、弱市場”型資源配置方式成為資源配置扭曲、要素使用效率低下、TFP逐年下滑的重要原因。隨著未來中國改革的不斷推進,制度進步將激發TFP上漲,但仍存在不確定性。如果未來改革效果不顯著,則TFP將延續繼續小幅下降趨勢,TFP均值將降至0.3000或更低;如果改革能釋放經濟活力,使資源配置得以優化、創新效率不斷提高,則未來TFP將可能重新進入上升區間,TFP均值可能提高到0.3500的水平,成為拉動潛在經濟增速維持較高水平的新動力。
綜合考慮生產要素、經濟結構以及改革效果等因素變動的情況下,可以得到用生產函數法測算的未來10年中國潛在增長率的變動趨勢值,其中2013—2017年,中國潛在增長率預計將介于7.15%~7.92%之間,均值為7.56%,而2018—2022年,中國潛在增長率預計將回落至6.58%~7.65%,均值為6.93%,仍處于較高水平。

表6 2003—2022年中國潛在增長率影響因素變動及預測
幾點結論及政策建議:
(1)未來10年,中國潛在增長率雖然會經歷一個下降過程,但總體看仍能維持在較高水平上。相對于勞動力和資本存量增速的下降,制度變革和技術創新及由此帶來的TFP變動將成為決定中國潛在增長率走勢的關鍵因素。因而,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釋放制度紅利,對于今后更好地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提高資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實現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2)結構調整因素對未來中國潛在增長率變動將產生重要影響。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包括粗放型發展模式面臨的產能過剩和資源約束調整、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轉換、區域間產業結構的轉移升級以及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等結構性因素,對未來中國潛在增長率的變動均產生重要影響。二元經濟下長期依賴低成本優勢、過度依賴投資和信貸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正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經濟金融再平衡過程將對中國今后潛在產出形成內在制約,因而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將成為推遲經濟增速“下臺階”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3)警惕因有效需求不足導致未來產出缺口擴大化的風險。盡管未來10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速仍能保持在較高水平之上,但如果居民就業及收入狀況未隨之改善,國內有效需求未能隨產能擴張而穩步增長,國際需求不確定性仍長期存在,實際產出持續低于潛在產出、產出缺口擴大化的風險將很可能持續。因而,今后應從擴大勞動力就業入手,切實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實現生產與需求在結構和規模上的大致匹配,避免需求從影響產出波動的短期因素固化為影響潛在產出變動的長期因素,力爭實現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基本一致。
[1]Okun,Arthur M.Potential GNP:Its Measurement and Significance[M].Proceedings of th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62:98-104.
[2]Phelps,Edmund S Phillips Curves.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and Optimal Inflation over Time[J].Economica,1967.Vol.(34):254-281.
[3]Kuttner,Kenneth N.Estimating Potential Output as a Latent Variable[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1994.Vol.(12):361-368.
[4]Paula R De Masi.IFM Estimates of Potential Output:Theory and Practice[P].IFM Working Paper,1997:1-14.
[5]Frederic SMishkin.Estimating PotentialOutput[P].At the Conference on Price Measurement for Monetary Polic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Texas,2007.May(24):1-6.
[6]ECB.Trends in Potential Output[P].ECB Monthly Bulletin,2011.January(1):73-85.
[7]沈利生.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變動趨勢估計[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9,(12):3-6.
[8]郭慶旺,賈俊雪.中國潛在產出與產出缺口的估算[J].經濟研究,2004,(5):31-39.
[9]黃梅波,呂朝鳳.中國潛在產出的估計與“自然率假說”的檢驗[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7):3-19.
[10]楊國中,李宏瑾.基于生產函數法的潛在產出估計、產出缺口及與通貨膨脹的關系:1978—2009[J].金融研究,2011,(3):42-50.
[11]于洪菲,田依民.中國1978—2011年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的再估算[J].財經科學,2013,(5):85-94.
[12]陳亮,陳霞,吳慧.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變動分析——基于日韓及金磚四國等典型國家1961—2010年的經驗比較[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2,(6):44-55.
[1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研究”課題組.中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轉折的時間窗口測算[EB/OL].國研網,2011-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