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之書
雷武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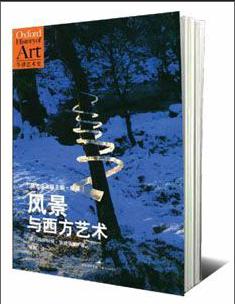
風景、自然、山水,這些詞在不同的歷史和現實場域中被使用。它們被我們當然地使用,它們所承載的含義似乎是自明的,但細想時卻發現又是糾纏復雜、含混不清的。這些詞的含義體現了人對自己、對所在的自然世界、以及和自然世界的關系的種種認識。而對這些詞的含義的辨析,或者說重新對它明確地加以界定,解釋,是我們認識自己和世界的重要方式。
在對什么是風景的問題上,有兩種相反的看法。歷史學家西蒙·沙瑪在其《風景和記憶》 是其中一種的典型代表。書中明確地宣稱自己的核心論點:“風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他主要是從歷史和精神角度,并且是民族、國家這種集體的歷史精神,也就是風景的象征意義、精神符號的角度,來看待風景。因此,他的這本書可以稱為是一本風景文化史。他把風景進行分類,分為木(森林),水(河流),石(山峰),來揭示它們的文化含義。在方法上,他在每一類風景中選用具體的例子,展示其歷史演變過程,對其做具體的精神分析;而不是對所有的一類風景做普遍的原理性分析。比如,在森林一類中他選取了波蘭、白俄羅斯、立陶宛邊境的比亞沃韋扎森林;在河流中,他選取了泰晤士河;在山峰中,他選了拉什莫爾山和阿爾卑斯山。在突出這些具體的典型中,兼顧到一些其他典型的歷史例子。在這些具體的例子中,通過具體的人物,來展示這些風景的文化意味(國家與民族的集體記憶的精神象征)。比如,比亞韋沃扎森林,早期立陶宛戰勝條頓騎士,后來屬于波蘭,19世紀俄國,一戰后屬波蘭,二戰初蘇德瓜分波蘭后被蘇聯占有,蘇德戰爭后被德國占領,二戰后被從中間劃分為波蘭和蘇聯部分,蘇聯解體后成為波蘭和白俄羅斯、立陶宛邊境。森林邊緣村莊曾經是猶太人棲居地,二戰時德國人把這里的猶太人徹底清除了。要把這座森林景觀也變成一看就是德意志式的。這里曾有沙皇的狩獵別墅,后來又有戈林的狩獵木屋,后來又有赫魯曉夫的狩獵度假區,現在成了體驗狩獵和吃野牛肉的旅游點。這是承載了沉重歷史的森林。
而在《風景與西方藝術》一書的結尾,加拿大藝術家邁克爾·斯諾秉持的是和沙瑪完全相反的看法:風景就是沒有人的自然,沒有任何人的介入。他要打破人的局限,人的視野。要取消人看自然的方式。他帶了一套復雜的攝影器材,攝影鏡頭可以縱、橫360度旋轉。在加拿大東北部的荒野中,拍攝了五天。他制作出一部電影,“天空、地平線、特寫的巖石地形、層疊的山脈、云層、日出、日落,在取景框里無情而緩慢地漂浮,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循環反復”。他要干什么?“這部影片成為了對一片荒野做出的絕對記錄,記錄地球最后存留的荒野。這部影片將被送入太空,作為曾經有過的自然面貌的紀念品”。
對沙瑪的風景文化論我想說的,一、作為精神的風景,不僅僅是集體記憶和象征,常常還是個人精神的表達和寄托。自然風景經常是個人逃避社會的寄居之地。二、風景有時候恰好是反文化、反歷史的。當我們面對一片自然風景時,它吸引我們,恰好在于它是外在于、超然于我們之外的存在和美。它震驚我們,讓我們從文化的、心理的、社會的、政治的、道德的重重重壓下脫離出來。感到一種自由,一種非人類社會規范、記憶、責任的絕對的自由。
對于斯諾的絕對的非人的風景論我們想說的是,風景從來就無法脫離人類而存在。它總是作為人類的概念,即使是那些人類足跡未到之處。斯諾本身的抱負,也是要拍出真正的,絕對的風景,是一種藝術活動。他要與偉大的風景畫家塞尚,桑普、柯羅的風景畫相比,他在制作這部電影時感覺聽到了巴赫的受難曲和彌撒曲一樣偉大莊重的宗教音樂。風景是人類精神的產物。
沙瑪是猶太人,背負著民族痛苦的歷史記憶。斯諾是加拿大人,歷史太輕,只有荒涼遼闊的自然。中國看到了太長太多的人的歷史,能輕松看待,而深切感到自然風景的永恒,與人生的短暫。深切體會到,在美麗的自然風景中笑談歷史的演變,是我們短暫人生最快樂的享受。
風景與記憶
作者: [英] 西蒙·沙瑪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副標題: 人文與社會譯叢
譯者: 胡淑陳 / 馮樨
出版年: 2013-10
頁數: 840
定價: 78.00
風景與西方藝術
作者: [英]馬爾科姆·安德魯斯
出版社: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landscape and western art
譯者: 張翔
出版年: 2014-1
頁數: 308
定價: 89.00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