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企業眼中的城市配送——與北京快行線食品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培軍一席談
文/本刊記者 李靜宇
物流企業眼中的城市配送——與北京快行線食品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培軍一席談
文/本刊記者 李靜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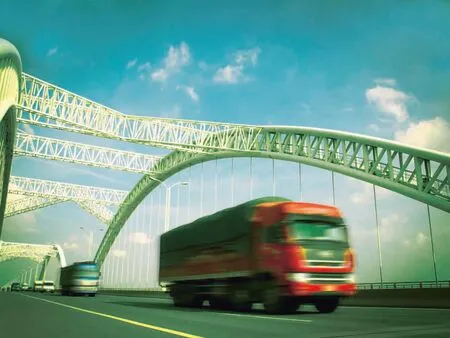
從事城市配送的物流企業面臨諸多難題,比如北京取消外地車長期進京通行證的同時,也對本市載貨汽車的禁行范圍由四環擴大到五環,這對于物流企業來講,無疑又一次加大了配送的成本。那么,物流企業此時是何感受呢?為此本刊記者采訪了北京快行線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培軍,請他談談企業的情況。
“證件”的困惑
作為一家專業的冷鏈物流解決方案提供商及運營商,快行線的業務已經擴大到冷鏈城市配送、冷鏈零擔業務和冷鏈宅配三大業務板塊,服務于超市供應商、超市配送中心、連鎖餐飲配送中心和生鮮電商等客戶群。
目前快行線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實現43個城市50000個超市的冷鏈生鮮配送和43個城市的冷鏈宅配。為了配合快行線的業務增長,提升客戶服務水平,快行線還將投入一千六百萬元打造統一的冷鏈物流管理平臺……
提及令人驕傲的數字,劉培軍笑了笑不置可否。他反而說,從事城市配送的物流企業都很脆弱,如今一張小小的貨車通行證也能成為物流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
“你有通行證的時候,你就可以做這個業務,若沒有這張通行證則寸步難行。之前有的司機還敢闖,交罰款也不在乎,現在一跟駕駛員的扣分聯系起來,再派司機去,司機都不去了。”劉培軍感慨道。
目前,北京四環以內的路段每天有大概有7.5萬輛運送貨物的車通行,而有貨車通行證的車輛不足兩萬,也就是說,北京每天至少有60%~70%的貨運車違規進入城區。
近些年來,北京市的貨運車輛通行證基本已經停止發放,好的物流企業有10%到30%的貨運車輛擁有通行證,一些新成立的物流企業基本無證。
對于快行線來講,有證的貨運車輛遠遠不能滿足業務量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業務的需要只能對外去租有貨運證的車輛。但是租用有證的貨運車輛成本太高,“租一輛有‘證’的車輛成本比我們自有車輛成本提高20%~30%,每個月光用于租‘證’成本支出就有十萬元,再加上罰款,那成本就增加了許多。”劉培軍說。
北京白天的道路太擁擠,那就改晚上實行配送,這是劉培軍想出的解決辦法。“跟客戶協商夜晚配送,有的客戶講,夜晚配送的前提是要降價。其實夜晚配送,我們的成本會增加,即使存在裝卸的擾民問題,還是可以規避的。”
目前貨運車輛沒有證不能進城,租有證的車輛又太貴,因此很多企業都用改裝的金杯“貨”車。據了解,對于改裝后的金杯“貨車”,雖然裝載率100%,但車小貨多,只好增加車輛。如果采用7米多長,裝載量為8噸的車型,一輛車就能裝到原有車輛的2到3倍,這樣進城的車輛會大為減少。

在劉培軍看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集約化的程度,一個8噸的車跑一趟能否裝滿貨,能否在一天的時間里將貨送到門店。如果不能做到集約化,那采用8噸貨車的車型也是一種浪費。
共同配送的糾結
有人提議,物流作為一種公共服務,不能受到這樣的待遇,一線城市應該像香港和臺灣那樣放開城市配送企業運送車輛。但對于目前北京擁有的貨運車輛,如果大幅度放開無疑會使北京道路更加擁堵。
因此為了破解一線城市配送這個難題,不少地方政府多年前開始倡導共同配送這個模式,而這也正是劉培軍一直推行的模式。
“發展共同配送,不但能夠提高單車的裝載量,也能夠提高在城市里的貨運車輛單車的使用效率。”劉培軍說:“顧名思義,共同配送是指一個客戶委托多個第三方,或是多個第三方之間聯合在一起。”
然而,政府在推廣,企業也在努力踐行,為什么共同配送就是發展不起來呢?面對疑問,劉培軍一語道破原因:“原因在于這個行業的分散性。”快行線現在全國7個城市有100%的全資子公司,在11個城市有51%股權的控股公司。”劉培軍說,“即使這樣我們一年的銷售額2個億都不到。”在他看來,每一個冷鏈公司規模都很小,形成不了氣候。
劉培軍做過一個調查,北京貨運車輛的裝載量有的是30%,有的是20%,還有的僅為10%,做得最好的企業也僅為70%到80%。車輛裝不滿也要跑一趟,這表明眾多資源閑置。物流是一個典型的“以量為王”的行業,有“量”什么都好說,而沒有“量”,就意味著成本攀升,企業生存艱難。
那么,共同配送模式的癥結究竟在哪里?
“因為眾多城市配送的第三方物流企業并不在同一起跑線上,這就使得共同配送不易實現。”劉培軍舉例說:“對于城市配送的企業來講,有多少輛車,有多少庫都不能算作是企業的競爭力,要看你有多少輛車擁有‘進城證’,有的物流企業有證,有的企業證很少或是根本沒有證,那大家不可能在一個平臺上去做共同配送這件事。”在他看來,有“證”車輛多的企業不可能與無“證”或是“證”少的配送企業聯合在一起,資源的不匹配也正是企業不能合作的原因。
但無論如何,共同配送仍是劉培軍堅持的方向。他說,這種模式不僅能提高車輛的裝載率,同時還能減少配送線路,“配送線路減少了就意味著車的裝載力會提升,在整個城市里跑的貨車就會減少。車輛少了,既緩解了交通擁堵,同時也減少了汽車尾氣排放對于城市空氣的污染。”
成本的壓力
曾幾何時物流企業以網絡為王,但今天“以量為王”成為了物流企業的口頭語,因為沒有量就意味著單批次利潤少,無法滿足配送所要支付的成本。
“實物成本也在增加,”劉培軍說,“我們服務的一些企業像灣仔、蒙牛、伊利、君樂寶等,這些生產性企業的采購成本也在增長,”因此對于涉及到的飲料、食品等快消品來講,單品的毛利也在逐年下降。
生產型企業采購成本的增加有一部分無疑要轉嫁到為其配送的第三方物流身上。“每年都會通過招標的形式把物流的配送費用向下壓。”各方都想“錢少花多干事”,這無疑考驗著物流企業城市配送的能力。
目前,商超和連鎖超市的配送模式,有自營配送或合作建立物流配送團隊,以及選擇第三方配送。劉培軍說,“物流模式沒有好與壞,只是說哪一種更適合。”
更多的商超企業和連鎖超市在自建物流團隊之后,銷售范圍也在逐漸擴大,但是范圍越大意味著單量越分散,那些單量集中的地方由自建團隊來配送,“而把很多單量很小的配送區域交給第三方配送企業來做,配送這些區域意味著配送的高成本。”劉培軍說。
對于城市配送另一個讓劉培軍頭疼的問題是貨物的交接,作為第三方配送物流企業要經過幾次交接。“供應商的商品到庫房,在我們內部有三次交接,這是可控的,因為我們企業內部有著嚴格而又規范的流程。”對于這三次內部交接,劉培軍用的是輕松和簡單來形容。但是對于司機配送到門店時的交接往往是不可控的。
“在這個交接過程中,第三方物流企業承擔著既是要驗貨的收貨方,同時又是送貨方的雙重角色。”在劉培軍看來,他非常理解超市的收貨部對那些生鮮、水果和肉、蛋、魚等所定下的嚴格的收貨標準。為了保證不出問題,對于送貨方送到他那里的貨,快行線有著嚴格的抽檢比例,一般是按10%的抽檢,因為這里面承擔著風險。但是在與門店交貨的時候,劉培軍從心里上希望抽檢比例低一些,因為這樣可以提高交貨的效率。而為了保證質量,超市對配送企業交貨程序也非常嚴格,這就造成了配送企業在交貨過程中時間的不可控,進而這種效率最終造成的是成本的居高不下。
“同樣是送貨,有的司機一天能送十五家門店,而有的司機一天只能送五六家門店。”在劉培軍看來,這是一個協同的問題,我們和收貨方要做好協同,要有這種意識,效率才能提升,成本才能降下來。
對于存在的問題,劉培軍也在尋找更為有效的解決方法,以求實現更為安全,更低成本的配送。對此,劉培軍的經驗是,簽定的合同契約要細,“合同能寫多細就寫多細。”劉培軍介紹說:“多年來,快行線與客戶合作的過程中合同內沒有界定清的問題都會不斷附加到新的合同里面做升級”,而快行線的文本合同從開始到現在已經升經了幾十個版本。
“每次與客戶發生爭議,如果是我方當初沒有約定清晰,那只好認賬,這個損失由我們買單”,劉培軍說,“但是如何去避免,怎么去規避,新的內容我會放在新的文本合同中。”
在很多人眼里城市配送是個苦行業,劉培軍也是這樣認為的。正是在這樣一種生存處境之下,他把“集”和“約”這兩個字看得格外重要——“集”就是想方設法把貨物集中到一個平臺上,約就是上下協同,提高配送和交接的速度與質量。
這并不只是說把價格降下來,你的利潤就會降低,“如果能用價格的優勢把客戶集過來,再能集到一個點,你的成本就會大幅度降低。”劉培軍說。
城市配送、冷鏈宅配、冷鏈零擔、冷鏈物流、冷鏈貿易,這是多年來快行線所涉及的業務范疇。劉培軍說,作為城市配送問題的存在與解決,他抱著等待的心里,過去10多年的時間里,快行線正是在這種種等待中頑強生存成長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