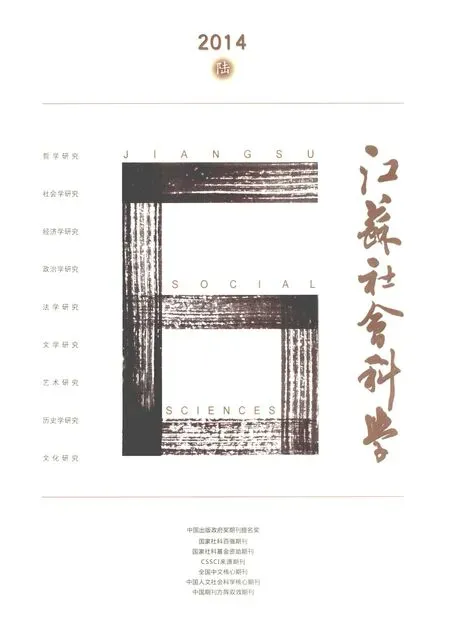論格式條款的成立與效力
吳一平
論格式條款的成立與效力
吳一平
在我國立法上,有關格式條款的規(guī)定相對粗疏,相關研究也不夠深入;由于其應用的廣泛性,實踐中出現(xiàn)的糾紛越來越多。文章在揭示格式條款本質(zhì)特征的基礎上,從格式條款訂入合同的要約和承諾兩方面分析其成立的特殊性,根據(jù)中外合同立法和學說,對格式條款的效力作了界定和評析,并結(jié)合最人民法院最新發(fā)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著重對格式條款的有效、無效與可撤銷進行了探討。
格式條款 成立 效力
吳一平,鹽城師范學院法政學院教授224051
一、格式條款及其特征
格式條款乃現(xiàn)代經(jīng)濟活動的必然產(chǎn)物,其主要優(yōu)勢在于簡化交易程序、減少交易成本以及交易結(jié)果的不可預測性。我國《合同法》第39條第2款規(guī)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xié)商的條款。”按照《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2.19條第2款的規(guī)定,標準條款是指一方為通常和重復使用的目的而預先準備的條款,并在實際使用時未與對方談判。理論上對格式條款的性質(zhì)有不同見解,主要包括命令行為說、合同說、規(guī)范說、規(guī)章說、事實合同說等[1]參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390頁。。本文贊同合同說,并認為格式條款只不過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合同,下面將進一步分析其特征所具有的法律意義。
其一,格式條款是由一方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準備的。《合同法》第39條第2款中的“預先擬定”應采用目的性解釋原則擴張解釋為“預先準備”(《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用語),因為格式條款的起草者并不限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當事人,否則將會使一部分應當屬于特別法律規(guī)范調(diào)整的格式條款排斥在調(diào)整范圍之外,不利于相對人保護。例如在我國,由建設行政部門擬定的商品房買賣合同文本,如果被開發(fā)商使用并向相對人提供,則當然屬于格式合同。有學者認為這里的“重復使用”是“預先擬定”的目的,是格式條款的經(jīng)濟功能,而不是其法律特征;并擔心如果特別強調(diào)格式條款重復使用的特點,則相對人在確定某一條款是否為格式條款時應當證明該條款已被重復使用的事實,這不免對舉證人過于苛刻[1]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頁。。筆者對此并不贊同。法律之所以對格式條款作特別規(guī)范并課以格式條款使用者較重的義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格式條款被不斷重復使用而涉及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如果不是為了重復使用,即便預先擬定的條款內(nèi)容不可協(xié)商也不能認定為格式條款,法律并無設置特別規(guī)范對相對人作傾斜保護之必要,只需個案處理;相反,如果是為了重復使用,即便預先擬定的條款只被使用了一次,也不妨礙其格式條款的認定。實際上相對人如要確定某一條款為格式條款無須證明“已被重復使用”而只須證明“為了重復使用”。事實上在德國法上“重復使用”即被作為格式條款的重要特征,有學者甚至將《德國民法典》第305條“格式條款指為多數(shù)合同預先擬定的合同條款”的“多數(shù)合同”解釋為必須是三個以上的合同[2]〔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債法總論》,杜景林、盧諶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頁。。不過此種觀點又顯得過于機械。
其二,格式條款是由一方當事人與不特定第三人所簽訂的。格式條款最重要的價值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如果格式條款僅為一方當事人與特定第三人而簽訂,反而會加大交易成本,而且與一般合同并無不同,法律無須設置特別規(guī)范。當然,不特定第三人一旦進入格式條款簽訂過程,則由不特定第三人變?yōu)樘囟ǖ谌硕蔀楦袷綏l款相對人。
其三,格式條款的內(nèi)容定型化。所謂內(nèi)容定型化,是指格式條款具有穩(wěn)定性和不變性,它將普遍適用于與格式條款提供者簽訂合同的不特定人。而且格式條款要約人和承諾人雙方的地位不變,不存在一般合同訂立過程中的要約與反要約的情形。故在此意義上我國臺灣地區(qū)將格式條款一般稱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但應當注意的是格式條款并不要求條款的形式定型化,例如《德國民法典》第305條就規(guī)定,一般交易條款以何種文字寫成,或者以何種形式體現(xiàn)并不重要,只要這些合同條款不是由當事人具體協(xié)商確定的,而是由當事人一方預先擬定的,就屬于一般交易條款。至于有學者所認為的格式條款在表現(xiàn)形式上均為書面形式,而不能是口頭形式或者默示方式[3]蘇號朋:《格式合同條款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頁。,筆者認為并無必要作此限制,事實上格式條款“不論其條款系獨立于契約之外、為契約之一部分,抑或載于契約書面之上,亦不論其范圍、字體或契約之方式如何均屬之。”[4]黃越欽:《私法論文集》,〔臺北〕世紀書局1980年版,第87頁。例如理發(fā)、自動售貨機售貨等交易均屬格式條款,當然主張者應負舉證責任。
其四,格式條款提供方在簽訂合同時就預先準備的條款不與對方協(xié)商。格式條款的提供人往往是經(jīng)濟上占優(yōu)勢地位的企業(yè),不特定相對人多為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相對人與條款的提供人雖然法律地位平等,但對格式條款只有概括接受或者拒絕的權(quán)利,“要么接受,要么走開”,相對人在簽訂格式條款時只能處于附從地位,正是在此意義上,法國、日本立法和學說均從合同的角度稱格式條款為“附和合同”。需要特別指出,“不與對方協(xié)商”指的是預先制訂的條款具有不可協(xié)商性,如果條款實際上可協(xié)商性而相對人誤以為條款不可協(xié)商性而未協(xié)商,即便該條款被多次重復使用也不能認為是格式條款,因為條款的使用人主觀上缺乏計劃性,可見我國《合同法》第39條第2款使用“未與對方協(xié)商”顯然不妥。當然,“不與對方協(xié)商”并非不能與對方協(xié)商,格式條款(個別交易條件)在個別情況下也可以成為個別協(xié)定并因此不再是格式條款,如果當事人就這種條款的具體內(nèi)容進行了磋商[5]〔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下冊),王曉曄、邵建東、陳建英、徐國建、謝懷栻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頁。。實踐中還有這樣一種情形,即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為了逃避格式條款特別規(guī)范的適用,往往表示愿意就格式條款中的某些條款進行磋商,并且向相對人提出了這些條款,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條款就成為個別協(xié)商的合同條款,因為相對人對這些行為往往難有作為[6]〔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頁。。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如果格式條款建立在有限協(xié)商的基礎上,由于談判地位不平等、談判情勢緊迫、示范條款設計過于精巧、談判技巧缺乏或者信息嚴重不對稱等原因,簽約過程中協(xié)商未必是完全、充分的,則格式條款立法也應當給予保護[1]向明華:《格式條款基本法律問題》,《廣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筆者認為,此種見解雖不無道理,但如果相對人不能證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磋商是“為了逃避格式條款特別規(guī)范的適用”而否定“不完全、不充分協(xié)商”的磋商性質(zhì),則難以準確界定格式條款,故不具有可操作性。
二、格式條款的成立
1.格式條款成立的形式
如前所述,格式條款文本本身并無法律意義,也就是說格式條款是否由提供方親自擬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格式條款訂入合同的行為才對格式條款的成立具有說明價值和法律意義。然而我國《合同法》并未對格式條款訂入合同問題作出系統(tǒng)、明確規(guī)定。許多學者認為格式條款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意思表示,“今日民法上之要約、承諾的觀點在此地卻顯得無意義。”[2]黃越欽:《論附和契約》,載鄭玉波主編:《民法債編論文選輯》(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18頁。“要約承諾式的締約制度所依據(jù)的價值觀念在此種情況下幾乎蕩然無存。”[3]蘇號朋:《格式合同條款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頁。美國學者格蘭特·吉爾莫甚至因此寫出了他的名著——《契約的死亡》。筆者認為此種論斷過于悲觀,格式條款的確對合同自由原則形成了強烈沖擊,但應當注意的是,雖相對人不能對格式條款的內(nèi)容作出任何修改,然要約人卻無權(quán)強迫相對人接受格式條款,相對人的合同自由并沒有完全被剝奪。正如德國學者梅迪庫斯所指出的:“一方當事人不堅持實現(xiàn)其對合同內(nèi)容的愿望,并不與合同自由或私法自治相矛盾。”[4][6]〔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頁,第294頁。
可見,格式條款在性質(zhì)上仍然是一種合同類型,格式條款的成立形式當然也要采用要約承諾方式,其訂立仍然要經(jīng)過要約和承諾階段,提供方明示格式條款屬于要約,相對人同意該格式條款訂入合同屬于承諾[5]杜軍:《格式合同研究》,〔北京〕群眾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頁。。只不過在格式條款訂入合同的要約和承諾“以一種變態(tài)的方式出現(xiàn)”[6]而已。“對于相對人來說,雖然他們不具有充分表達自己意志的自由,但從法律上看,他們?nèi)匀粦獙ο碛惺欠窠邮芨袷綏l款的權(quán)利,因此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所以格式條款的使用,也沒有完全否定合同自由原則。”[7]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頁。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人的承諾在這里表現(xiàn)為“整體性”的意愿,即既不經(jīng)過討價還價,也無須對各個細節(jié)分別予以確認,一方當事人便對合同從整體上表示同意[8]尹田:《法國現(xiàn)代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頁。。正如王澤鑒先生所言:“定型化契約條款系企業(yè)經(jīng)營者所自創(chuàng),雖大量使用,但不因此而具有法律性質(zhì),仍須經(jīng)由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的合致,始能成為契約的內(nèi)容。”[9]王澤鑒:《民法原理(一)》,〔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頁。可見雙方當事人的合意仍然是格式條款成立或者說格式條款訂入合同的形式。
2.格式條款訂入合同的要約
我國《合同法》第39條第1款規(guī)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quán)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該款通常被認為是我國合同法上格式條款訂入合同設定的一般規(guī)則,違反它則格式條款未訂入合同。然而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研究:
第一,格式條款訂入合同規(guī)則是否應對合同性質(zhì)或者類型加以區(qū)分?從《合同法》第39條第1款來看,該規(guī)定為格式條款訂入合同提供了一般規(guī)范,但未區(qū)分合同類型。筆者認為,我國《合同法》在設置格式條款特別規(guī)則時有必要區(qū)分消費合同與商業(yè)合同。
消費合同是消費者與經(jīng)營者之間所締結(jié)的合同,消費者與經(jīng)營者雖然法律地位平等但經(jīng)濟地位不同,交涉能力存在明顯差異,雙方之間如果訂立格式條款,需要借助于格式條款特別規(guī)則對消費者予以傾斜保護,自不待言。事實上保護消費者利益的立法所確認的原則,很多都可以直接適用于格式條款(附和合同),成為法律調(diào)整格式條款關系的最基本的原則[1]尹田:《法國現(xiàn)代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頁。。然而商業(yè)合同是經(jīng)營者之間基于商業(yè)目的而訂立的合同,如果雙方之間訂有格式條款,由于彼此之間經(jīng)濟地位相當,法律推定作為商人的相對人也有與格式條款提供人相當?shù)慕簧婺芰Γ蓪ζ洳o太多特別保護之必要,即使顯失公平亦屬商業(yè)風險。因此格式條款訂入商業(yè)合同的特別規(guī)則應與格式條款訂入消費合同有所不同,例如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當事人提示注意義務不應當象消費合同那樣過于嚴格,因為對當事人雙方而言,格式條款往往包含了交易習慣,而這些交易習慣一般不會影響當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而僅僅是簡化了磋商程序,如果提示注意義務過于嚴格,反而會阻礙格式條款功能和優(yōu)勢的發(fā)揮。
雖然筆者并不贊同格式條款特別規(guī)則一律不適用商業(yè)合同的觀點,但從其他國家或地區(qū)立法來看,格式條款特別規(guī)則主要適用于消費合同。例如《德國民法典》第305條明確規(guī)定一般條款訂入合同的規(guī)則不適用于商人之間訂立的合同,我國臺灣地區(qū)《消費者保護法》專為消費者提供特別保護。反觀我國《合同法》并不區(qū)分合同性質(zhì),對格式條款訂入不同合同適用相同規(guī)則,屬于立法的不周。我們認為,可以通過完善法律,一方面在《合同法》中設置一般規(guī)則,體現(xiàn)不同類型合同適用格式條款特別規(guī)則在要約人提示說明程度上的差異;另一方面在《消費者權(quán)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中特別加重要約人的提示義務以及違反該義務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一些地方性立法已做了有益的嘗試,如《上海市合同格式條款監(jiān)督條例》、《江蘇省合同監(jiān)督管理辦法》均有專門針對消費合同的條款。
第二,格式條款提供人是否僅就免責條款負有提請注意義務?從《合同法》第39條第1款字面含義來看,格式條款提供人僅就免責條款負有提請相對人注意義務。但筆者認為該規(guī)定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格式條款提供人提請注意義務并不限于格式免責條款,但法律對提供格式免責條款一方當事人提請注意義務的要求更高。惟應明確的應是格式條款提供方提請相對人注意格式條款訂入合同必須達到合理的程度,而我國合同法卻未有任何規(guī)定。
格式條款提請注意是否達到了合理的程度,英國普通法形成的判例規(guī)則值得參考[2]李永軍:《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頁。:(1)文件的外形。臺灣學者劉宗榮先生認為,“文件的外形須予人以該文件載有足以影響當事人權(quán)益之約款之印象,否則相對人收到該文件不予閱讀,使用人提請注意(通知或公告)即不充分。”[3]劉宗榮:《定型化契約論文專輯》,〔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版,第8頁。(2)條款內(nèi)容的清晰程度。要求文字、語言必須清晰明了,條款內(nèi)容應達到足以使相對人注意格式條款的程度。格式條款內(nèi)容如字體過小,印刷不清或被單位章、日期戳掩蓋,致使相對人難以注意其存在或難以辨別其內(nèi)容的應屬不清晰。例如在J.Spurling Ltd.v.Bradshaw一案中,丹寧勛爵就曾指出:“在我看來,有些條款須以紅色墨水印在文件上并以紅色手指標志指出,其提請注意才能被認作充分合理。”[4]韓世遠:《免責條款研究》,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頁。(3)提請注意的方法。根據(jù)交易的具體環(huán)境,格式條款提供方可以采取個別明示和公開明示(如公告)兩種方式,并應以個別明示為原則,公開明示為例外,只有個別提示有困難時才應使用公告明示的方式。其中公開明示應以使一般相對人可以察知、閱讀、理解為原則。最高院《合同法解釋(二)》第6條第1款規(guī)定:“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對格式條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內(nèi)容,在合同訂立時采用足以引起對方注意的文字、符號、字體等特別標識,并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格式條款予以說明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符合合同法第39條所稱‘采取合理的方式’”。(4)提請注意的時間。《歐洲合同法原則》第2:104條之(一)對格式條款提供方提請注意的時間的規(guī)定很明確,即提起相對人注意的行為,必須是在“合同達成之前或達成合同之時”,因為只有在合同訂立之前或者在合同訂立過程中,相對人才能據(jù)此決定是否訂立合同。(5)提請注意的程度。格式條款的提供方提請相對人注意的程度應達到足以使其注意格式條款的內(nèi)容為要,并且因格式條款當事人的身份不同、格式條款的不同性質(zhì)等有所差異。其一,格式條款越是對相對人不利或者相對人相關知識越欠缺,格式條款提供方提請注意的義務越重。當然,這里的“相對人”并非特定人,而是指以相關領域一般人的知識水平為標準的觀念上的人。例如消費者相對于作為相對人的其他經(jīng)營者而言知識水平顯然要低,故消費合同中的免責條款提請注意義務應當重于商業(yè)合同,而對于某些遵循商業(yè)慣例的商業(yè)合同來說這種提示注意義務甚至是多余的。再如聾啞人的識別和認知能力明顯低于普通人,格式條款提請聾啞人注意義務也應當高于普通人。其二,格式條款免責范圍越大、內(nèi)容越不合理,格式條款提供人提請相對人注意的義務越重。事實上格式條款免責范圍越大、內(nèi)容越不合理,對相對人越不利。英國相關判例認為,條款利用人僅僅把格式免責條款實際通知相對人是不夠的,還必須將格式免責條款合理地提請相對人注意,簡言之,提請注意必須達到合理的程度,或者說充分的程度[1]Park v.South Eastern Rly Co.,2C.P.D.416(1877).。正如丹寧勛爵所指出的:“免責條款越不合理,提請相對人注意所需要的通知程度越高。”[2]韓世遠:《免責條款研究》,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頁。其三,格式條款越是異乎尋常,格式條款提供人提請注意的義務越重。英美法上就確立了“告知程度與條款的不同尋常程度成比例”的原則[3]楊楨:《英美契約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頁。。因為格式條款越是異乎尋常,越是超出相對人對格式條款合理安排的正當期待。當格式條款達到過分異常的程度,以至于無法期待他方當事人預期該條款出現(xiàn)在格式條款所適用的交易種類中時,該條款視為未訂入合同[4]劉宗榮:《定型化契約論文專輯》,〔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版,第32頁。。另外,格式條款提供方提示注意義務的程度還因為格式條款的表現(xiàn)形式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電子合同作為一種新型格式條款交易方式,而且使用特別頻繁,相對于傳統(tǒng)合同來說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當事人交易過程互不謀面,雖然節(jié)省交易成本,但為減少交易風險,應課以格式條款提供方更重的提請注意義務。
3.格式條款訂入合同的承諾
格式條款訂入合同的承諾,即相對人同意將格式條款訂入合同。我國《合同法》未就格式條款訂入合同的承諾作任何規(guī)定,這不免給人以一種邏輯錯覺,似乎只要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當事人向相對人發(fā)出了要約,相對人就只能無條件接受,而無承諾與否可言。這不僅有違合同自由原則,而且對本來就喪失了決定合同內(nèi)容自由的相對人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筆者認為這是我國合同立法的一個重大失誤。我國臺灣《消費者保護法》第13條規(guī)定:“契約之一般條款未經(jīng)記載于定型化契約中者,企業(yè)經(jīng)營者應向消費者明示其內(nèi)容:明示其內(nèi)容顯有困難者,應以顯著之方式公告其內(nèi)容,并經(jīng)消費者同意受其拘束者,該條款即為契約之內(nèi)容。前項情形,企業(yè)經(jīng)營者經(jīng)消費者請求,應給與契約一般條款之影本或?qū)⒃撚氨靖綖樵撈跫s之附件。”該規(guī)定明確只有經(jīng)相對人同意格式條款方能訂入合同。
在解釋上,相對人表示同意之方式不應以明示為限,默示也可以[5]馮震宇、姜志俊:《消費者保護法解讀》,〔臺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頁。。明示同意,是以書面或言詞聲明將格式條款訂入合同,如果是以書面形式則通常是在合同文本上簽名。一經(jīng)在文本上簽名便認定格式條款成為合同的內(nèi)容。這似乎對相對人過于苛刻,但一般相對人在簽字時應盡到注意義務,仔細了解格式條款的內(nèi)容,如果他未做到這一點便有過失,不值得特別加以保護[1]崔建遠:《合同責任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頁。。默示同意,是指格式條款的提供者已明示格式條款,并已給予相對人合理機會了解條款內(nèi)容后,相對人沒有作出反對的意思表示,即視為同意該格式條款訂入合同。但是應當注意,默示同意是一種推定,相對人若有異議,須負反證責任。德國司法實務也認為,如果消費者被提醒注意并被給予合理機會而不為反對的意思表示,即推定其同意[2]劉宗榮:《定型化契約論文專輯》,〔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版,第32頁,第20頁。。
無論明示同意還是默示同意,格式條款一經(jīng)相對人同意訂入合同便宣告成立。當然,格式條款訂入合同僅僅表明格式條款的成立,是一種事實狀態(tài),但其是否有法律約束力,仍須視格式條款是否有效而定,這屬于格式條款的效力問題。
三、格式條款的效力
如果說格式條款的成立屬于一種事實判斷,著眼于合同關系是否存在,那么格式條款的效力則屬于法律對已經(jīng)成立的格式條款的價值判斷,著眼于格式條款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關于格式條款效力,有的國家通過民法典對格式條款的效力予以規(guī)定,有的國家則通過專門的立法予以規(guī)制。學理上既包括格式條款的有效、無效與可撤銷,也包括格式條款的生效、不生效與失效以及格式條款的效力待定等[3]吳一平:《論合同的效力》,〔上海〕《政治與法律》2005年第3期。。我國合同法關于格式條款的效力與普通合同并無太大差異,這里主要探討格式條款的有效、無效與可撤銷。
1.格式條款的有效
格式條款的有效,指的是一個業(yè)已成立的格式條款因其符合法律的規(guī)定,獲得了法律的肯定性評價,能夠產(chǎn)生當事人預期的效果,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格式條款是否有效,是代表國家意志的法律對體現(xiàn)個人意志的格式條款的審查和干預,當法律給予其予以肯定性評價時,格式條款有效;當法律給予其否定性評價時,格式條款無效。有效的格式條款受法律保護,無效的格式條款不受法律保護。
我國《合同法》對格式條款有效成立的構(gòu)成要件雖無明文規(guī)定。但《民法通則》第55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或社會公共利益。”合同法為民法之特別法,格式條款為合同之特殊形式,格式條款訂入合同的行為當然是法律行為,按照法律解釋規(guī)則,《民法通則》第55條關于法律行為有效要件的規(guī)定,自然也是格式條款的有效要件。因此,已成立的格式條款若具備以上三個構(gòu)要件即為有效,有效格式條款具有法律約束力:第一,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格式條款”,此為我國臺灣學者王澤鑒先生所講的契約之拘束力,即“當事人間合法締結(jié)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發(fā)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請求解約。”[4]王澤鑒:《民法原理(一)》,〔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頁。第二,“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此為格式條款履行效力的發(fā)生,不履行該條款構(gòu)成違約。
《民法通則》第55條規(guī)定的反面解釋包括三種情形:一是當事人不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成立的格式條款為效力待定的格式條款;二是當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實成立的格式條款為可撤銷的格式條款;三是當事人特別是格式條款提供人違反法律或公序良俗被而成立的格式條款為無效格式條款。
2.格式條款的無效
筆者認為,格式條款的無效仍然沒有超出《民法通則》第55條規(guī)范的三種情形:(1)當事人不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成立的格式條款而未被追認權(quán)人追認的格式條款。(2)當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實成立的可撤銷格式條款而被撤銷權(quán)人撤銷的格式條款。(3)當事人主要是格式條款提供人違反法律或公序良俗被認定無效的格式條款。
上述第(1)(2)兩種情形屬于相對無效,而第(3)種情形屬于絕對無效。對于格式條款絕對無效,《合同法》第40條進一步作了特別規(guī)定:“格式條款具有本法第52條和第53條規(guī)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quán)利的,該條款無效。”《合同法》第40條所列情形顯然屬于違反了《民法通則》第55條第3項的規(guī)定,屬于絕對無效,在有些國家被稱為“黑色條款”。普通合同無效的規(guī)定同樣適用于格式條款(筆者主張將合同絕對無效稱為無效合同以區(qū)別于合同的相對無效),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格式條款絕對無效的情形有三大類:(1)《合同法》第52條所列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2)《合同法》第53條所列“造成對方人身傷害”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chǎn)損失”兩種免責條款無效的情形;(3)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quán)利三種情形。
然而《合同法》第40條一直飽受學界詬病,許多學者批評《合同法》第40條與第39條第1款相互矛盾[1]《合同法》第39條規(guī)定,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并采取合理措施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這也就是說,雖然有免責條款,如果一方已經(jīng)用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或者向?qū)Ψ竭M行說明的話,該條款應該是有效的;而40條又說無效。這是直接的抵觸,典型的自相矛盾。參見梁慧星:《合同法的成功與不足》(下),〔北京〕《中外法學》2000年第1期。,因為該條為格式條款設定了公平原則的絕對標準,即只要“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quán)利”,格式條款絕對無效。而《合同法》第39條第1款又規(guī)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quán)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這就是說,如果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格式條款并不當然無效,從《合同法》第40條觀之,如果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則格式條款已屬絕對無效,根本不存在第39條“提請對方注意”的空間。
再看最高院《合同法解釋(二)》第9條的規(guī)定:“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法第39條第1款關于提示和說明義務的規(guī)定,導致對方?jīng)]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對方當事人申請撤銷該格式條款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該條解釋實際上為“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留下了“活路”,即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法》第39條第1款規(guī)定的提示和說明義務的“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并非當然、絕對無效,而是可撤銷的格式條款。事實上,《合同法》第40條將“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規(guī)定為絕對無效,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反映出立法者對免責條款的敵視態(tài)度,帶有明顯感情色彩。然而《合同法解釋(二)》第10條又規(guī)定:“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法第39條第1款的規(guī)定,并具有合同法第40條規(guī)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格式條款無效。”依該解釋,如果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法》第39條第1款的規(guī)定和提示和說明義務的,其“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quán)利”的條款當然、絕對無效。試問:在違反“提示和說明義務”的情形下,“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或者“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quán)利”條款到底是可撤銷還是無效?事實上《合同法解釋(二)》第9條與第10條表面上解決了《合同法》第39條第1款與第40條的矛盾,而該兩條解釋本身又是自相矛盾的,足見該司法解釋過于草率。另外,《合同法解釋(二)》第10條還有矯枉過正、畫蛇添足之嫌,因為《合同法》第40條所提及的第52條和第53條規(guī)定本來就是絕對無效的情形,而該條卻將整個《合同法》第40條“一網(wǎng)打盡”,不僅放寬了“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而且也放寬了另外兩種情形,這在邏輯上必然會導致人們對《合同法》第52條和第53條所規(guī)定的無可置疑的絕對無效情形的疑惑。其實,在筆者看來,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當事只要違反了提示和說明義務,格式條款應被判定未訂入合同,根本不存在需要作可撤銷還是無效的效力判斷,只不過是《合同法》第39條所隱含的格式條款訂入規(guī)則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而已。
3.格式條款的可撤銷
我國《合同法》第54條規(guī)定了可變更或撤銷的合同,但對于可變更或撤銷格式條款未有直接規(guī)定(《合同法解釋(二)》第9條的規(guī)定可謂開了可撤銷格式條款之先河,但筆者認為實屬不當)。有學者指出,為了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利益,當消費者認為將格式條款宣告無效對其不利而主張對其予以變更或撤消時,法院應支持主張[1]王利明:《對〈合同法〉格式條款規(guī)定的評析》,〔北京〕《政法論壇》1999年第6期。。這在有些國家通常被稱為“灰色條款”。《合同法》第39條只規(guī)定“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quán)利和義務”,而沒有規(guī)定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違反此義務的法律后果。事實上“話說半句”是我國民事立法的一個通病。筆者認為,格式條款在顯失公平的情況下的,完全可以適用《合同法》第54條關于可撤銷合同的規(guī)定。因為在實踐中絕大多數(shù)格式條款的爭議都涉及到條款的顯失公平的問題,而在許多情況下相對人可能并不愿意宣告格式條款無效,因為宣告格式條款無效有可能使其雪上加霜,或者格式條款只是輕微地加重了對方的責任,因此反而不利于公正地解決糾紛,況且也不排除個別情況下顯失公平恰恰是反向的。
格式條款的訂立屬于法律行為,而根據(jù)《民法通則》第55條的規(guī)定,當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實而成立的格式條款即為可撤銷的格式條款,同時格式條款屬于一種特殊類型的合同。因此,不僅顯失公平的格式條款可以適用《合同法》第54條關于合同變更或撤銷的有關規(guī)定,而且因重大誤解、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格式條款均可適用《合同法》第54條的規(guī)定。實際上《合同法》第40條雖然只規(guī)定了無效的格式合同的特別情形,目的在于充分保障格式條款相對人特別是消費者的合法利益,但該條款并沒有絕對排斥相對人請求變更和撤銷格式條款的權(quán)利[2]張翼杰、郭英杰、史利娟、劉國昱:《格式條款的成立及效力》,〔太原〕《理論探索》2004年第2期。。如果格式條款雖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但消費者基于利益權(quán)衡而不愿意宣告該條款無效,從尊重、保護消費者利益出發(fā),應當被允許。當然,如果相對人主張變更格式條款,而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也同意,法院也應尊重當事人選擇,體現(xiàn)意思自治,有利于案件的和諧處理。盡管筆者認為我國合同法上的合同可變更制度的設置并不科學,因為如果法院支持相對人變更合同的主張,無異于強令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當事人接受一個新合同,有違契約自由原則。但在目前的合同法框架下,格式條款有特別規(guī)則適用特別規(guī)則,無特別規(guī)則應適用合同一般規(guī)則。
格式條款普遍出現(xiàn)于當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其應用極其廣泛。英國學者A.G.蓋斯特甚至指出:“在目前普通人(非商人)訂立的合同總數(shù)中,格式合同的數(shù)量大約占到99%以上。很少有人會記得他們最后一次簽訂非格式合同是什么時候。恐怕實際情況是,除了格式合同,他們所簽訂的合同中只有少數(shù)口頭合同算是例外。”[3]Edited by A.G.Guest,Anson’s Law of Contract,Clarendon Press,1985,p.94.與國外立法相比,我國合同法對格式條款的規(guī)范僅涉及四個法條且過于粗略,學界對格式條款的研究也不夠充分,實踐中出現(xiàn)的許多糾紛難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決。筆者認為,我國應合理借鑒國外立法經(jīng)驗,在司法實踐和對格式條款充分研究的基礎上,及時歸納總結(jié)并可借助于民法典編纂的有利時機上升為立法規(guī)范,以便正確引導格式條款的訂立,合理解決因格式條款引發(fā)的糾紛,從而更好地保護當事人特別是格式條款相對人的合法權(quán)益。
〔責任編輯錢繼秋〕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法典視閾中的合同法熱點問題研究”(編號:13FXB00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