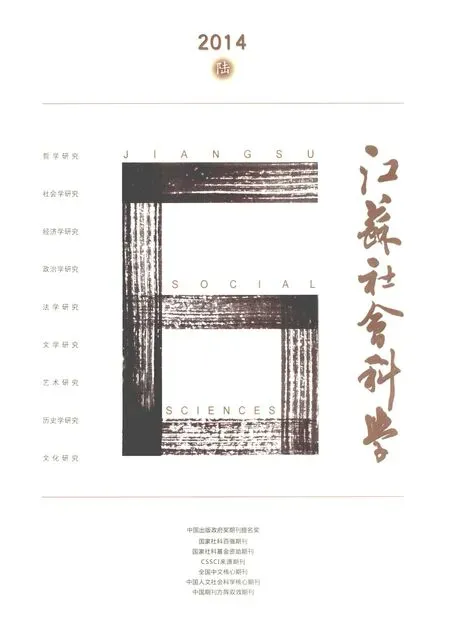倫理憂患及其文化形態(tài)
劉波
倫理憂患及其文化形態(tài)
劉波
人類精神生活及其同一性是人類生存的最后文化防線,這道文化防線以倫理憂患的方式伴隨著人類發(fā)展進(jìn)程。在文明史上,倫理憂患常以“道德咒語(yǔ)”的方式對(duì)歷史發(fā)展進(jìn)行反思。中西方文明中具有終極意義的倫理憂患是“如果沒(méi)有上帝,世界將會(huì)怎樣?”和“世風(fēng)日下,人心不古”。當(dāng)下的“后”意識(shí)是人類對(duì)自身延續(xù)的精神鏈和文化鏈的倫理憂患。倫理憂患作為一種文化形態(tài),對(duì)以物質(zhì)力量為主導(dǎo)的發(fā)展方式進(jìn)行倫理診斷、道德批評(píng)和文明預(yù)警,是人類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平衡力量。
倫理憂患 道德咒語(yǔ) “后”意識(shí) 文化形態(tài)
劉波,東南大學(xué)道德哲學(xué)與中國(guó)道德發(fā)展研究所副教授 210096
“我們?yōu)槭裁丛谝黄稹焙汀拔覀內(nèi)绾卧谝黄稹弊鳛槲拿鞯幕締?wèn)題,其核心是倫理憂患,對(duì)于這兩個(gè)透著幽遠(yuǎn)憂患意識(shí)的根源性問(wèn)題的探索與回答構(gòu)成人類的思想史精神之流,成為我們面對(duì)未來(lái)的文化后方和思想資源。人是一種文化存在,個(gè)體的人在其所構(gòu)筑的社會(huì)系統(tǒng)中尋求生存的理由與勇氣,安身立命,作為整體的社會(huì)則追求系統(tǒng)的秩序與公正,由此建構(gòu)一個(gè)精神的家園、文化的歸屬地,讓人的存在獲得意義。包爾生說(shuō)過(guò):“每種動(dòng)物都希望過(guò)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這種天賦性質(zhì)在沖動(dòng)中顯示自己,支配著動(dòng)物的行動(dòng)。這個(gè)公式同樣適合人,他希望過(guò)一種人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包含人的一切,也就是說(shuō),過(guò)一種精神的、歷史的生活,在這種生活里為所有屬于人的精神力量和性格留有活動(dòng)空間”[1]轉(zhuǎn)引自,何懷宏:《倫理學(xué)是什么》,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頁(yè)。。這一精神家園和文化屬地是作為個(gè)體的人和整體的社會(huì)的共同文化防線,其以倫理憂患的文化形態(tài)為表征,與社會(huì)的發(fā)展階段和人的生存狀況緊密關(guān)聯(lián)。
一、文明進(jìn)程中的倫理憂患
人類社會(huì)作為一種文化存在,是人在進(jìn)行物質(zhì)生產(chǎn)的同時(shí)又生產(chǎn)出的一套符號(hào)系統(tǒng),這一符號(hào)系統(tǒng)的構(gòu)成框架概括為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三足而立的文化世界。政治向度考量的是如何使人類的制度最優(yōu)化,從而實(shí)現(xiàn)人類社會(huì)的合理秩序;經(jīng)濟(jì)向度主要考量是如何分配和增加財(cái)富,最終提高人類的整體社會(huì)福利;而從文化向度則透視社會(huì)和人的存在,提供指導(dǎo)人類活動(dòng)的價(jià)值系統(tǒng)。按照丹尼爾·貝爾對(duì)文化的定義:“文化本身是為人類生命過(guò)程提供解釋系統(tǒng),幫助他們對(duì)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1]〔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版,第24頁(yè)。而倫理則是文化價(jià)值體系的核心,正如黑格爾所說(shuō),民族是倫理的實(shí)體,倫理是民族的精神。以倫理為核心的文化系統(tǒng)就是為人類個(gè)體的安身立命、人類整體的秩序安頓提供文化指導(dǎo)和干預(yù),進(jìn)行倫理診斷和道德評(píng)價(jià)。這一符號(hào)系統(tǒng)是人從事物質(zhì)文化生產(chǎn)時(shí)同時(shí)產(chǎn)生的價(jià)值系統(tǒng)和信仰系統(tǒng),不論何種文明體系,都有對(duì)至善的向往、對(duì)人性之善的肯定,并以此為前提為個(gè)體的生存與發(fā)展,為社會(huì)存在的合理性提供倫理診斷、道德批評(píng)和文化預(yù)警的文化,稱之為倫理型文化或文化的倫理向度。
倫理型文化是人類作為文化存在的一種情懷表達(dá),按照樊浩教授的分析,這樣的文化向度是針對(duì)人的生命過(guò)程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而尋找解釋系統(tǒng)以獲得存在的合理性,是試圖超越生命過(guò)程中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2]樊浩:《文化與安身立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頁(yè)。。這種努力在各種文明中都有體現(xiàn),或者說(shuō)古今中西之文明就是各個(gè)民族所特有的解釋系統(tǒng)和超越傾向,而倫理憂患意識(shí)則是一個(gè)重要標(biāo)志。
在原始社會(huì),人們靠狩獵生活,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處于實(shí)體狀態(tài),自然如同神靈,人們因無(wú)法解釋諸多自然現(xiàn)象而膜拜自然、對(duì)自然充滿敬畏之心。原始狩獵社會(huì)主要不是物質(zhì)社會(huì)或者說(shuō)主要不以物質(zhì)占有為核心價(jià)值觀。其時(shí),價(jià)值是一種精神上的、非物質(zhì)的存在,時(shí)間是一種獨(dú)特的主觀感受,各種傳奇、各種神話使人類的初年成為神話時(shí)期,人類在各種神話中安頓心靈、尋求寄托,人與人的彼此相處以神的旨意、神秘的力量為合理性的依據(jù)。
當(dāng)人類告別了刀耕火種、進(jìn)入農(nóng)業(yè)社會(huì)階段,也就開(kāi)始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生活方式是安居樂(lè)業(yè)型的,人們生活在穩(wěn)定的、一成不變的方式中,時(shí)間對(duì)于人的意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季節(jié)更迭、循環(huán)往復(fù)。在這樣的產(chǎn)業(yè)模式下,中西方文明沿著不同的路線發(fā)展出中西不同的文明體系。作為近現(xiàn)代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文明和希伯來(lái)文明均著眼于人以外的世界,古希臘取向于自然界,將世界劃分為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以尋求客觀世界的規(guī)律作為追求;希伯來(lái)文明取向于世界、自然的終極原因,是一種信仰主義,其締造了一個(gè)超越倫理道德情感、超越世俗權(quán)力、超越自然的上帝,古希臘文明與希伯來(lái)文明成為西方文化的源頭,締造了西方的宗教文化與科學(xué)、民主制度和理性精神。而中國(guó)文明則取向于人倫,世代定居的農(nóng)業(yè)文明所產(chǎn)生的以血緣關(guān)系網(wǎng)所衍生的宗法制,家國(guó)一體的倫理政治的社會(huì)治理模式,使中國(guó)文明成為以道德為主體的倫理型文化,中西文明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構(gòu)建精神同一性與文化同一性的出發(fā)點(diǎn)和運(yùn)行路徑。
18世紀(jì)中葉,肇事于英國(guó)的工業(yè)革命將人類推進(jìn)了工業(yè)時(shí)代。從這時(shí)起,人類開(kāi)始有了關(guān)于未來(lái)和進(jìn)步的想法,時(shí)間不再是循環(huán)式的、而是呈線性延伸的,未來(lái)是金色的,充滿希望的。中世紀(jì)農(nóng)業(yè)社會(huì)以及以前,人類在神話、宗教中安頓心靈、尋找依托,工業(yè)革命帶來(lái)的進(jìn)步主義思潮讓人類可以把希望寄托于未來(lái)而握在自己手中,工業(yè)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生活的物質(zhì)條件,為人類建立起了一個(gè)指向未來(lái)的時(shí)間體系,并建立了這樣的信念:事物的發(fā)展必將經(jīng)歷一條不平坦的路,不斷向前、向上發(fā)展,未來(lái)必定要超越現(xiàn)在,人類能夠創(chuàng)造自己的未來(lái)。從工業(yè)革命始,人類走出了以神話主導(dǎo)的原始社會(huì)、宗教主導(dǎo)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等精神力量為主導(dǎo)的傳統(tǒng)社會(huì)而進(jìn)入了以經(jīng)濟(jì)力量等物質(zhì)力量為核心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也開(kāi)啟了“人類精神保衛(wèi)戰(zhàn)”的進(jìn)程,其以文明的終極憂患為主要表達(dá)形式,以衛(wèi)道士和家園守護(hù)人的角色維護(hù)著人類精神生命及其同一性,從而守護(hù)著作為人的最后一道文化防線。
近兩個(gè)多世紀(jì)以來(lái),人類一直生活在以經(jīng)濟(jì)力量為主導(dǎo)的社會(huì)體系中。工業(yè)革命引發(fā)的技術(shù)革命的浪潮不斷沖擊和引導(dǎo)著農(nóng)業(yè)、工業(yè)、交通、運(yùn)輸、通訊等領(lǐng)域的變化和發(fā)展,人類對(duì)科學(xué)、技術(shù)和機(jī)器的依賴已經(jīng)緊密到無(wú)法分隔的程度,已經(jīng)是一個(gè)被技術(shù)和機(jī)器統(tǒng)治的時(shí)代。同時(shí),自工業(yè)革命以來(lái),亞當(dāng)·斯密著述《國(guó)富論》打開(kāi)了人類認(rèn)識(shí)和理解自然、財(cái)富以及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新思路,諸如經(jīng)濟(jì)學(xué)、經(jīng)濟(jì)體、生產(chǎn)、分配、消費(fèi)、利潤(rùn)等等成為顯詞、顯學(xué)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根本力量。有別于農(nóng)耕時(shí)代,人們理解的世界圖景是以經(jīng)濟(jì)為核心、以主要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為標(biāo)志的,可以稱之為“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盡管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帶給人類無(wú)法估量的利益,人們的生活質(zhì)量與生存條件都獲得了極大地改善,然而,其所倡導(dǎo)的價(jià)值觀和追求利益的道路破壞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帶來(lái)了環(huán)境危機(jī)、政治危機(jī)、文化危機(jī)等等,通常被倫理學(xué)家稱為“時(shí)代危機(jī)”或“歷史轉(zhuǎn)折點(diǎn)”,就是指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給人類帶來(lái)的問(wèn)題和困惑,就是倫理憂患。倫理憂患的文化形態(tài)形成于歷史進(jìn)程中,同時(shí)表現(xiàn)出中西兩種不同的表達(dá)形式。
二、倫理憂患的文化表達(dá)
此種危機(jī)以及對(duì)危機(jī)的憂患始終伴隨著人類發(fā)展進(jìn)程,作為一種終極憂患情懷的存在成為人類文化現(xiàn)象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也是人作為文化存在實(shí)體的一種內(nèi)在規(guī)定。此種終極憂患表現(xiàn)在中西兩個(gè)文明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西方文明中以尼采為代表發(fā)出的絕嘆:“上帝死了”;二是以倫理道德為主調(diào)和基色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所感喟的“人心不古”。
在西方傳統(tǒng)中,從柏拉圖開(kāi)始,哲學(xué)家就把世界分為兩個(gè)世界,塵世的世界和理念的世界,并認(rèn)為理念的世界、非塵世的世界更為根本,塵世的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擬,真理、本源這些第一性的、純理性的東西都在理念世界里。這一傳統(tǒng)一直持續(xù)到近代,康德的先驗(yàn)理性、黑格爾的絕對(duì)精神都是理念世界的表達(dá)。人們雖然生活在塵世世界里,但理念世界才是人的追求和目的。到了19世紀(jì),這一傳統(tǒng)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尼采高呼,“上帝死了”,那個(gè)神的世界、絕對(duì)的世界沒(méi)有了。尼采是最重要的道德哲學(xué)家,他對(duì)于西方哲學(xué)劃時(shí)代的意義在于他直指18世紀(jì)理性主義所主張的自律的道德主體,認(rèn)為這個(gè)道德主體是一種虛構(gòu)、幻覺(jué),尼采瓦解了它,讓意志取代理性,教導(dǎo)每一個(gè)人以某種巨人、英雄般的意志行為使自身成為自律的道德主體。從尼采開(kāi)始,古希臘傳統(tǒng)的思辨的智慧哲學(xué)已經(jīng)成為狹義的哲學(xué),讓位于思考現(xiàn)實(shí)生活和生命的現(xiàn)代哲學(xué),即哲學(xué)發(fā)生了轉(zhuǎn)向、轉(zhuǎn)向了人間,更加強(qiáng)調(diào)和關(guān)注我們生活的世界。存在主義強(qiáng)調(diào):存在先于本質(zhì),就是這個(gè)世界的人的此刻實(shí)存,是先于本質(zhì)的東西。到了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則是徹底解構(gòu),所有的世界都沒(méi)有確定的東西,一切都是現(xiàn)象、碎片,都是非連續(xù)的,一切都是細(xì)節(jié)、多元、相對(duì)、模糊、雜亂的,無(wú)規(guī)律可尋、也無(wú)需去尋,從而走向徹底的虛無(wú)。后現(xiàn)代解構(gòu)的是人類的信心與信仰,其揭示了一些本質(zhì)問(wèn)題,但也造成了人類的精神危機(jī)和信仰危機(jī),是終極憂患的極端形式。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學(xué)派也意識(shí)到的這些問(wèn)題,以美國(guó)學(xué)者小約翰·B·科布和大衛(wèi)·格里芬為代表的建設(shè)性后現(xiàn)代學(xué)派,已經(jīng)著眼于從建設(shè)性的角度解讀后現(xiàn)代和人類文明現(xiàn)象。
以儒家思想為主調(diào)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國(guó)人只有一個(gè)現(xiàn)實(shí)的生活世界,孔子所追求的對(duì)形而上的反思與超越,不是對(duì)感性世界和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的超越,而恰恰就是在生活的世界和感性時(shí)空中。按照李澤厚的分析,先秦儒家持守的正是一種執(zhí)著于現(xiàn)實(shí)人生的實(shí)用理性,“它拒絕做抽象思辨,也沒(méi)有狂熱的信仰,它以直接服務(wù)于當(dāng)時(shí)的政教倫常、調(diào)協(xié)人際關(guān)系和建構(gòu)社會(huì)秩序?yàn)槟繕?biāo)。”[1]李澤厚:《哲學(xué)綱要》,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頁(yè)。孔子說(shuō),未知生,焉知死。在儒家看來(lái),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生的意義就在于生活的過(guò)程,是歷史性生成的過(guò)程。超越與不朽不在天堂,不在來(lái)世,就在人倫日常,就在個(gè)人修行。于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guó)思想的著眼點(diǎn)就在當(dāng)下,這樣的文化傳統(tǒng)不會(huì)有“上帝死了”的大喊,針對(duì)現(xiàn)世的各種不適與危機(jī),則會(huì)有“人心不古”的哀嘆。同時(shí),對(duì)于個(gè)體的生命秩序與道德準(zhǔn)則,孟子所言:“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wú)教,則近于禽獸。”[2]《孟子·滕文公上》。其規(guī)定了人性的依據(jù),人異于禽獸之處在于“人之有道”,就是“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guī)范體系,以“仁”為本體,“居仁由義”,通過(guò)“義”的分辨和“體”的陶冶,最后構(gòu)建起“信”的道德信念,由此建立起人的主體性以脫離動(dòng)物性,這就是儒家倫理對(duì)人的規(guī)定。而且對(duì)待道德原則,孔子持絕對(duì)的態(tài)度,規(guī)定了內(nèi)圣外王的人格境界,從儒家的角度,對(duì)于中國(guó)人而言,得仁行仁、成仁成圣是最高的追求,“人人皆可為堯舜”。由此建立起人的精神生命的同一性。這個(gè)同一性既是變化的也是感受的,文化設(shè)計(jì)模式以及同時(shí)產(chǎn)生的憂患一直是一個(gè)“并蒂蓮”,從保守的意義上看是衛(wèi)道士,似乎是“九斤老太”,以一副不受歡迎的道德嘮叨評(píng)價(jià)滾滾而來(lái)的歷史進(jìn)程,從積極的意義上看,這種憂患又成為人類精神家園的守護(hù)神。
西方文明最大的心愿是“回到古希臘”,那是因?yàn)槲鞣轿拿鲝奈椿氐竭^(guò)古希臘,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原罪意識(shí)使得他們“回到上帝”成為根本的追求,其精神同一性在于通過(guò)上帝來(lái)溝通。中國(guó)文化在文明之初就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有別于禽獸的“人”的概念,即“人之有道也”,用“道”將“人”這一有限存在的實(shí)體與理想狀態(tài)的“人格”,即“道”之載體聯(lián)系起來(lái),將特殊的個(gè)體與普遍聯(lián)系起來(lái),使“我”意識(shí)到“我們”從而獲得精神的家園。這一文化設(shè)計(jì)運(yùn)行到近代,在民族存亡的歷史關(guān)頭,這種文化同一性遭到質(zhì)疑,讀書人檢討民族文化,喊出“打倒孔家店”,一直在傳統(tǒng)中延續(xù)、未曾邁出過(guò)精神同一性的中國(guó)文明遭遇危機(jī),開(kāi)始了持續(xù)一個(gè)多世紀(jì)的文化檢討與文化運(yùn)動(dòng)。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之“天下”指的是中國(guó)文化,表達(dá)的是一種積極的憂患,是對(duì)中國(guó)文化所依靠的精神同一性的“興亡”之憂患及擔(dān)起責(zé)任的擔(dān)當(dāng)意識(shí)。
三、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道德之咒”
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是最為典型的倫理型文化,有別于西方宗教文化的文明設(shè)計(jì),中國(guó)文化在其文明的誕生、演化過(guò)程中有兩個(gè)核心要素使之成為倫理型文化,一是對(duì)人性善的假設(shè)前提和終極信仰;二是以建立在現(xiàn)世生活中倫理道德的統(tǒng)一性。以“倫”為核心的倫理型文化中的“道”,是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的最根本的依據(jù)與支撐,是人的存在最后的、終極性的東西。“大道”情結(jié)是倫理型文化的固有物與標(biāo)識(shí)器,老子說(shuō),大道廢,有仁義。此種大道的完美體現(xiàn),在先秦時(shí)期的思想家們看來(lái)就是周朝的社會(huì)體制,最早的道德咒語(yǔ)也由此發(fā)出,形成了倫理型文化的思維模式,即道德的“后顧模式”。
從中國(guó)文化體系看,最早的思想動(dòng)蕩可追溯到殷周之際的社會(huì)變革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思想評(píng)論。國(guó)學(xué)大師王國(guó)維說(shuō)過(guò):“中國(guó)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jiǎng)∮谝笾苤H。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guò)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zhuǎn)移;自其表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1]王國(guó)維:《觀塘集林·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頁(yè)。中國(guó)作為文明古國(guó)最早遭遇社會(huì)轉(zhuǎn)型與變遷是在先秦氏族社會(huì)崩毀時(shí)期,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情況是,“長(zhǎng)治久安”的氏族社會(huì)的遠(yuǎn)古傳統(tǒng)正在迅速崩毀,許多邦國(guó)在劇烈爭(zhēng)奪,戰(zhàn)爭(zhēng)頻發(fā),社會(huì)轉(zhuǎn)型在即,國(guó)事變化多端。其時(shí),物質(zhì)文明在迅速發(fā)展,生產(chǎn)、消費(fèi)大規(guī)模擴(kuò)大,財(cái)富、欲望不斷積累和增加,貪婪、狡黠、自私、陰險(xiǎn)等等人性的弱點(diǎn)暴露無(wú)疑,文明進(jìn)步所帶來(lái)的罪惡與苦難未曾有過(guò)、令人震驚,家族、邦國(guó)、個(gè)體的生存信念及方式亟需理論資源加以支持。當(dāng)時(shí)的諸子百家中的儒道如孔子、老子、莊子均道堯舜,希望以回到周朝、回到美好的古代作為救世良方,都以各自的表達(dá)體現(xiàn)出向古情懷和道德終極理想主義的特點(diǎn),也為道德中國(guó)奠定了道德優(yōu)先原則甚至道德第一原則的文化基因,成為“世風(fēng)日下、人心不古”的最初表達(dá)。那么,什么“風(fēng)”、何以“古”呢?所謂“風(fēng)”就是風(fēng)氣、習(xí)慣,是社會(huì)倫理的統(tǒng)一性,是當(dāng)下的合法性問(wèn)題;所謂“古”,就是傳統(tǒng)的統(tǒng)一性,文化統(tǒng)一性的最后規(guī)定,是人的精神家園的基石,在此基礎(chǔ)上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表達(dá)的是道德歷史的同一性,所謂“下”就是對(duì)照此“古”,這種統(tǒng)一性的差異或反對(duì),這樣的道德咒語(yǔ)正是道德社會(huì)的同一性與道德的歷史同一性之間沖突、博弈、解構(gòu)、重構(gòu)、調(diào)和、適應(yīng)之過(guò)程的循環(huán)往復(fù),是文明體系自身調(diào)整的一個(gè)信號(hào)。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shí)代是所謂“禮壞樂(lè)崩”的時(shí)代,傳統(tǒng)氏族社會(huì)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正在瓦解,“民散久矣”,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政治、軍事發(fā)展變化起伏更迭、變遷劇烈,西周以“禮制”為特征的統(tǒng)治秩序面臨崩潰,在這樣的動(dòng)蕩時(shí)代,特別是面對(duì)社會(huì)道德衰落,孔子說(shuō):“郁郁乎文哉,吾從周。”[1][7]楊伯峻:《論語(yǔ)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8頁(yè),第28頁(yè)。他東奔西走、周游列國(guó)就是想要恢復(fù)周禮,維護(hù)“禮”的統(tǒng)治秩序,主張維持原有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以免破壞原有的氏族制度和統(tǒng)治體系,從而維護(hù)原有的道德秩序和倫常規(guī)則。而老子的“大道”情結(jié)則在于追求遠(yuǎn)古“小國(guó)寡民”的原始時(shí)期:“有舟車,無(wú)所乘之;有甲兵,無(wú)所陳之;使民復(fù)結(jié)繩而用之”[2][3][6]王弼注:《老子道德經(jīng)注校釋》,樓宇烈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90頁(yè),第45頁(yè),第43頁(yè)。,“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fù)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wú)有。”[3]在這種社會(huì)中,人無(wú)知無(wú)欲,沒(méi)有追求和向往,一切人為的進(jìn)步,從文字技藝到各種文明都應(yīng)廢棄,一切都相對(duì)平靜、安寧、緩慢、柔弱,鄰國(guó)相望而不相侵,老死不相往來(lái)。大家都不過(guò)分發(fā)展,相安無(wú)事,沒(méi)有爭(zhēng)奪和毀滅。老子的“無(wú)為之治”實(shí)則是積極問(wèn)世的政治哲學(xué),理想的社會(huì)模式是小國(guó)寡民,社會(huì)風(fēng)尚是不要發(fā)展、回歸自然的原始狀態(tài)所帶來(lái)的自然道德。莊子與老子有接續(xù)關(guān)系,但不同的是,莊子關(guān)心的不是倫理、政治問(wèn)題,而是從關(guān)心個(gè)體生存狀況出發(fā),抗議“人為物役”、反對(duì)異化,他要求“不物于物”,要求恢復(fù)和回到人的“本性”,反對(duì)“仁義”,也反對(duì)技術(shù)的進(jìn)步,要求否定和舍棄一切文明和文化,回到原始狀態(tài),無(wú)知無(wú)識(shí),“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4]王先謙撰:《莊子集解》,沈嘨寰點(diǎn)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4頁(yè)。,“生而不知其所以生”[5]許維遹撰:《呂氏春秋集釋》,梁運(yùn)華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2頁(yè)。,像動(dòng)物一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抱甕入井”的寓言故事就是其反對(duì)技術(shù)進(jìn)步的代表性主張,莊子的主張是人類文明發(fā)軔之初就出現(xiàn)的反異化的呼聲,是人類思想史上最早的反異化的呼聲,也是物質(zhì)文明進(jìn)步與精神生活沖突后“道德咒語(yǔ)”的最初形成。
西周覆滅以后,作為倫理實(shí)體的社會(huì)分崩離析,個(gè)體逐步獨(dú)立出來(lái),中國(guó)社會(huì)第一次被啟蒙,傳統(tǒng)的統(tǒng)一性、社會(huì)倫理道德的統(tǒng)一性都面臨著合法性的危機(jī),因此,老子說(shuō):“大道廢,有仁義”[6],孔子凄凄惶惶地“郁郁乎文夫,吾從周”[7]。這種對(duì)文明認(rèn)同危機(jī)的擔(dān)憂最初就是由各個(gè)民族的文化英雄、文化天才覺(jué)悟到的,或者說(shuō)就是其先知先覺(jué)的,這樣的倫理憂患常常是以“道德咒語(yǔ)”的方式出現(xiàn)以達(dá)到警醒的作用,先知們把主要是情緒性的道德咒語(yǔ)不斷提升和體系化,就成為一種對(duì)啟蒙、對(duì)歷史前進(jìn)的一種反思,最終成為整個(gè)社會(huì)的文化自覺(jué)從而努力保持社會(huì)歷史前進(jìn)的合理性。
歷史浪潮總是滾滾向前、世間萬(wàn)物總是生生不息,歷史處于日日更新的進(jìn)程中,變化無(wú)常是永恒的,向前看是日新的歷史以及由此帶來(lái)的各種變化,以最終的“大道”來(lái)衡量、來(lái)評(píng)判則常常是迷茫與不解,甚至痛心與不安,于是感慨“世風(fēng)日下,人心不古”。作為倫理型文化的中華文明最為典型地表達(dá)了倫理憂患的形成和作用,表征著文化自覺(jué)、倫理自省的天然性。
四、“后”倫理憂患
倫理憂患的另一個(gè)表達(dá)形式就是道德的“后顧模式”,或者說(shuō)是一種倫理上的“后意識(shí)”。曾幾何時(shí),“80”后、“90”后、甚至“00后”成為了時(shí)髦用語(yǔ),代表了一個(gè)群體,表征的是不同于傳統(tǒng)甚至有些標(biāo)新立異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其實(shí),這種“后”用語(yǔ)是一種“后”意識(shí)的表達(dá)。在歷史前進(jìn)、代際更迭過(guò)程中,是所謂“過(guò)來(lái)人”對(duì)后一代的信心與信任問(wèn)題,是對(duì)當(dāng)下構(gòu)建倫理統(tǒng)一性的價(jià)值基礎(chǔ)的信心問(wèn)題,這種疑憂交錯(cuò)的“后”意識(shí)本質(zhì)上是人類對(duì)自身延續(xù)的精神鏈條和文化鏈條的倫理憂患,表達(dá)出來(lái)就是前一代已經(jīng)成為“后”的一代對(duì)即將成為“后”的一代的憂患,是倫理憂患的當(dāng)下表現(xiàn)形式。
歷史總是一代推動(dòng)一代、代際更迭、永不停息,傳統(tǒng)社會(huì)中對(duì)于年輕人的成長(zhǎng)只是將其當(dāng)作社會(huì)整體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接受教育和評(píng)價(jià)、服從長(zhǎng)輩的一代,而且總是傾向于認(rèn)為有一種影響青少年的黑暗力量在起作用。23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下了一個(gè)結(jié)論:年輕人因天性而瘋狂的程度,一如酒之于醉漢。莎士比亞的劇作《冬天的故事》里,有一個(gè)牧羊人希望“10歲到23歲這段年齡給它一筆勾銷,不然就讓青春一覺(jué)睡過(guò)去”。社會(huì)和成年人群體都將年輕人看作是唐突的甚至是危險(xiǎn)的,不僅要教育他們,甚至要管束他們。年輕人生活在長(zhǎng)輩制定的一套價(jià)值體系和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中。社會(huì)學(xué)理論將傳統(tǒng)社會(huì)稱之為“前喻社會(huì)”就是指的這種狀況。相對(duì)應(yīng)的就是“后喻社會(huì)”,年輕人逐步成為掌控社會(huì)的主體。在迅速變遷和技術(shù)橫行的社會(huì),年輕人顯示出了他們的優(yōu)勢(shì),他們反應(yīng)迅捷、接受能力強(qiáng),沒(méi)有條條框框的限制,他們比指導(dǎo)他們成長(zhǎng)的長(zhǎng)輩更快、更緊地?fù)肀Я诉@個(gè)多變的世界,特別是在技術(shù)日益統(tǒng)治世界的狀況下,在某些時(shí)候,年輕人甚至成了“老師”和指導(dǎo)者,于是“后群體”從整體中獨(dú)立出來(lái)了,不必在價(jià)值體系中只有服從的義務(wù),是聽(tīng)話的對(duì)象、灌輸?shù)娜后w,甚至是擔(dān)憂和指責(zé)的對(duì)象,所謂“不聽(tīng)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現(xiàn)在年輕的一代因掌握新技術(shù)、新理念而成為一個(gè)有優(yōu)勢(shì)的群體,他們與父輩們平起平坐地一同面對(duì)這個(gè)世界了,甚至由技術(shù)權(quán)威再變?yōu)槲幕瘷?quán)威來(lái)指導(dǎo)長(zhǎng)輩,傳統(tǒng)又一次遇到挑戰(zhàn),這是人際人倫層面的挑戰(zhàn),是晚輩和長(zhǎng)輩社會(huì)定位的一種社會(huì)角色和文化作用的一種根本性調(diào)整,是既有文明和文化體系遇到的重大問(wèn)題之一。應(yīng)對(duì)這個(gè)“后群體”和“后現(xiàn)象”,作為倫理憂患面對(duì)當(dāng)下代際更迭的一種特定表達(dá)的“后”倫理意識(shí),平衡著社會(huì)發(fā)展和人際關(guān)系。這種“后”倫理憂患意識(shí)是人作為道德存在物的一種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的特有表現(xiàn),是人類文明終極憂患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
人類文明固有的疑憂交錯(cuò)的“后意識(shí)”與不斷成長(zhǎng)的蓬勃的“后一代”在后喻社會(huì)、在不斷發(fā)展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以及后現(xiàn)代社會(huì)博弈并演繹成“永遠(yuǎn)的‘后’”與“永遠(yuǎn)的道德”的文化形式,形成所謂“后”倫理憂患。
歷史長(zhǎng)河總是義無(wú)反顧地滾滾向前,所謂“不息江河萬(wàn)古流”,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也不因任何憂患而停滯。同時(shí),不絕于耳的憂患之音讓我們的心靈與理智從世俗的喧囂中掙脫出來(lái),反思人的行為與后果,對(duì)以物質(zhì)力量為主導(dǎo)的發(fā)展方式進(jìn)行倫理診斷、道德批評(píng)和文明預(yù)警。因此,歷史總是在瀟灑前進(jìn)的,而人的精神、文明總是后顧的,歷史的瀟灑是建立在文明后顧之上的,歷史的悠久取決于文明后顧的厚度。“后顧”方式的倫理憂患是文化保存與發(fā)展的保證,如果沒(méi)有憂患,文化就會(huì)喪失;但如果過(guò)度憂患,就會(huì)走向保守,表現(xiàn)出對(duì)未來(lái)、對(duì)青年一代的懷疑與缺乏信心。歷史總是在理性為主的歷史主義與情感為主的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中前行,演繹著瀟灑的歷史與“后顧”的文明之變奏曲。
[1]樊浩:《文化與安身立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2]李澤厚:《哲學(xué)綱要》,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
[3]〔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版。
[4]何懷宏:《倫理學(xué)是什么》,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
[5]《孟子·滕文公上》。
[6]王國(guó)維:《觀塘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7]楊伯峻:《論語(yǔ)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8]王弼注、樓宇烈校注:《老子道德經(jīng)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
[9]王先謙撰、沈嘨寰點(diǎn)校:《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10]許維遹撰、梁運(yùn)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
〔責(zé)任編輯:天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