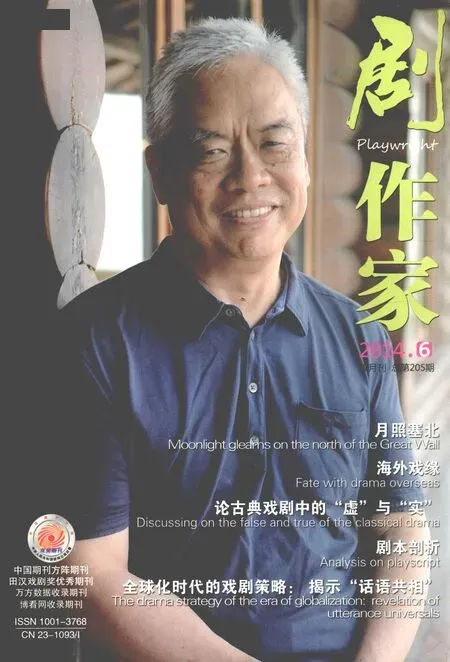《陽光下的葡萄干》之戲劇沖突與意象
楊 晉
《陽光下的葡萄干》之戲劇沖突與意象
楊 晉
《陽光下的葡萄干》作為第一部由美國黑人女劇作家榮膺“紐約劇評家獎”的戲劇作品[1],甫一問世便獲得好評如潮,連演四分之一個世紀,已然躋身美國戲劇經典之列。曾有評論指出,“可以公道地說,嚴肅成熟的美國黑人戲劇應始于1959年洛蘭?漢斯博雷的《陽光下的葡萄干》”(Littlejohn1966:79)。該劇的成功絕非偶然,其格局之高挑大氣,結構之精巧細致,戲劇語言之傳神生動,主題思考之寬廣深邃,使它跳出了“黑人”戲劇的種族框架,具有了普世意義上的人文關懷。夢想是貫穿全劇的主旋律,劇名正是來自蘭斯頓?休斯的那首詩,“夢想受挫將會怎樣?/它會干枯得/像一顆陽光下的葡萄干嗎?”正是劇中人物對夢想的追求觸到了我們內心深處,而與夢想交集的種種戲劇沖突,更是撥動了我們的靈魂之弦,引人深思,催人追問。如果夢想是劇中的織梭,沃爾特一家便是織架,它交織的便是三根張力十足的沖突主線:家園、家庭和種族,而為承載及凸顯這些戲劇沖突,劇作家洛蘭?漢斯博雷巧妙設計了眾多戲劇意象,這些戲劇意象乍一看或許不那么引人注意,但是卻能產生奇妙的場效應,更是在這幅精巧的織錦上繡上了華麗的圖案。漢斯博雷曾這樣描述細節和普世意義的關系:“我相信戲劇寫作最可靠的想法之一就是,如果你想創造具有普世性的東西,你必須極其注重細節。普世性,我認為,來自于如實的描述”(1969:128),劇中的種種戲劇意象,正是漢斯博雷如實描述、細節至上的匠心獨運。
一、戲劇沖突與意象之家園篇
《陽光下的葡萄干》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劇作,反映的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黑人工人階層生活中的挫折,喜樂和哀愁(Wilkerson2001:140),詹姆斯?鮑德溫指出,在之前的美國戲劇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多的關于黑人生活的真實描述(轉引自Cheney1984:55)。但它不是單單反映種族沖突、宣揚政治信條的社會抗議劇,它首先是一部家園生活劇,盡管以美國黑人生活為背景,反映出來的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矛盾以及對家園的愿景、對成長的期盼卻是無膚色、無國籍,足以在每個家庭里激起共鳴。
沒有家園,何以家為,任何家庭都渴望擁有屬于自己的家園,而在20世紀五十年代,美國黑人正處于生存空間惡劣、社會地位邊緣化的特殊時期,大量的黑人家庭蝸居于城市貧民窟中,而沃爾特一家的生活環境正是典型代表,他們和鄰居一起擠在狹窄逼仄卻又租金昂貴的公寓房里,光線欠佳,衛生間都要幾家公用,生活有諸多不便,于是家園的憧憬與現實的憋屈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沖突,并被劇作家巧妙地展現在一系列自然元素的戲劇意象之中。比如陽光,一開幕時劇作家就告訴我們沃爾特家里的格調分外灰暗而倦怠,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屋里唯一的自然光來自于廚房的小窗戶,陽光是生命熱力之源,而在擁擠而且設計不合理的黑人貧民窟里,人們卻被剝奪了這份明亮和熱力。到后來得知媽媽莉娜?沃爾特買了房子后,露絲關心地問道“會不會—會不會有很多陽光?”[2]莉娜則非常理解地回答“是的,孩子,陽光充足的很”(80)。對久居昏暗的人們而言,充足的光照已然是奢侈了,或者說對莉娜和露絲來說,只要能讓陽光照射進來的房子就是好房子。比如動物意象,露絲曾苦澀地把她們住著的地方比作是個老鼠陷阱,吞噬了家里大量的金錢(32)。當莉娜終于給全家人帶來家園夢想的曙光時,露絲激動不已:“再見了,這些該死的開裂的墻壁!再見了,這些四處奔跑的蟑螂!”(79)再比如植物意象,莉娜在廚房的窗沿上—那是家里唯一有自然光的地方—放了一盆小植物,“瘦小脆弱,卻頑強地生長著”(27)。這盆植物恰恰代表了莉娜心里的家園夢想,渺小卻堅韌,到了快搬家的時候,莉娜仍然細心照料它,女兒比莉莎不解地問她為啥要帶這“破爛舊玩意兒”,莉娜的回答是,“它就是我的表達”(101)。終于要和陰暗的舊宅告別時,莉娜仍不忘回來把它帶走,或許在她心里,這小小的盆栽雖然缺少陽光照耀,卻不乏精神(40),它孕育著希望。她甚至認為它最能貼近她對花園的渴望之心(41)。關于花園的戲劇意象在劇中也反復出現,莉娜在白人社區買的房子就有一個花園,她可以壟一塊地,種種花草(78),沉浸在喜悅中的家人甚至送了她一套嶄新的花園工具以及花園帽(103)。能夠擁抱陽光,貼近自然,這就是貧民窟里的平凡夢想。由此可見,諸多自然意象在本劇中的使用樸實無華,潤物無聲卻凸顯了貧民窟里居住環境的惡劣,更烘托了劇作家園夢想的主題,我們不禁回想起劇本開篇的詩句,那里正有一個點題的自然意象:“夢想受挫將會怎樣?/它會干枯得/像一顆陽光下的葡萄干嗎?”夢想會不會受挫,就好像一顆葡萄在陽光的曝曬下枯萎縮水,不復之前的水靈鮮活?或許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像一顆葡萄干的味道一樣耐人尋味。
二、戲劇沖突與意象之家庭篇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一家人難免因為性格或者追求方面的原因產生種種矛盾沖突。《陽光下的葡萄干》的一大吸引力就在于劇作家精心刻畫了家庭沖突中沃爾特一家極具魅力的人物形象,生動鮮明,個性迥異,具有臉譜式的戲劇意象特征,讓人難忘。莉娜是個意蘊豐富的母親意象。喜歡花花草草的她首先是“大地母親”的形象,是“所有人的母親,堅強,慈愛,堅定,讓家人團結在一起的凝結劑”(Wilkerson1986:444),她含辛茹苦養兒育女,操持家務任勞任怨,并盡最大可能地去為家人實現家園夢想,在家庭受到挫折時她是力量的源泉、不倒的支柱(109);她同時又是一個“黑人母系氏族家長”的形象,是家中的堅強壁壘(Hansberry1963),也是家里無人敢挑戰的權威(Cheney1984:66)。做出買房的決定時她利落果斷,在女兒比莉莎對上帝不敬時(34,39),在兒子沃爾特對他妻子露絲脾氣暴躁時(58),莉娜更是及時展現了她的威嚴,管教子女,讓家庭重歸有序;她還是個“傳承者”,把家庭的尊嚴(123),把愛和信心(125)傳遞給她的子女,更重要的是,在家庭面臨危機時,她能保持鎮靜,安撫家人,而且把“家長”的位置傳給了沃爾特,并教會了他如何成為真正的一家之主。沃爾特接過家庭的重任,也正標志著他由“成人”走向“成熟”。我們不禁想起在戲劇的前半部分,做為兄長的他無視家人的辛勞和肩上的責任,好高騖遠卻又眼高手低,一心想著用父親的保險賠償金去盲目投資,甚至攤上了妹妹的學費。后來他投資被騙,家里蒙受重大損失,這時他才痛定思痛,意識到他對家庭的責任,意識到家庭和種族尊嚴比物質主義或金錢追求更為重要。當家園夢想受到外部勢力挑戰時,他挺身而出,維護了家庭的核心利益。沃爾特這個如涅槃重生的“成長者”形象,讓人動容,又讓人回味。妹妹比莉莎首先是個“實驗者”,喜歡“實驗不同形式的表達”(35),她以三分鐘的熱度投入到諸如馬術、劇社、攝影以及吉他等各種活動中,無論別人如何看待,她依然固執地追求著自我的身份(49)。比莉莎同時又是對傳統和偏見的“挑戰者”,她積極接受高等教育,喜歡獨立思考,不愿當一個順從的女兒或者某人“不需要思想”(83)的女朋友,她敢于在強勢的莉娜面前說出對上帝的懷疑—雖說隨后被莉娜給鎮壓,也能夠在富裕卻俗氣的喬治面前說不。或許她張揚的個性部分地導致了她和莉娜之間的代溝或者隔閡,但這也恰恰是一個家庭朝氣和希望的象征。露絲則是“賢妻良母”的形象,克勤克儉,謙恭忍讓,為了給家里減少負擔,甚至動了瞞著丈夫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的心思,生活上她照顧一家老小,尤其是丈夫沃爾特,但卻未能真正被他理解,就好比她未能真正理解丈夫的想法一樣,每次沃爾特談起自己的理想和煩惱時,她卻只能回以生活上的關愛,而且對沃爾特來說是一種機械的、例行公事般的關愛:“把雞蛋吃了吧”(22),“想喝點熱牛奶嗎”(73),“要不來點咖啡吧”(74)。面對沮喪的沃爾特,她只能回答“除了吃的,我還能給你什么呢”?(74)面對家庭里的種種問題,沃爾特夫婦之間缺乏理解和溝通,這難道不正喻指現代家庭夫妻相處的窘境?所幸的是在戲劇的后半部分,雖然家庭財政問題仍未解決,但是對家庭夢想的共同追求讓沃爾特和露絲開始真正為對方著想,終于冰釋前嫌,迎來了婚姻的重生(Cheney1984:70)。由此,劇作家通過塑造沃爾特一家諸多張力十足的戲劇人物意象,用他們的喜怒哀樂,折射出千萬個家庭普通而又真切的愿景和煩憂。該劇上演后,劇評人HenryHewes曾評論說,“劇中人物是有色人種,有著他們種族特有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也有著所有人都有的、相同的問題”(1959:28)。劇本給我們展現了沃爾特一家的家庭問題,又賦予其普世意義,讓所有讀者觀眾都能感同身受,捫心反省,沉思自問。
三、戲劇沖突與意象之種族篇
《陽光下的葡萄干》是一個以美國黑人社會為背景的家庭劇,時間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正是美國黑人掀起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的時代,當時美國社會因此而處于激蕩的社會和法制變革的邊緣(Wilkerson1986:442)。這部劇作之所以引起巨大反響,是因為它直面當時美國社會白人與黑人的沖突,尤其是主流白人社會對黑人的歧視,并且坦然表達黑人群體對歧視的控訴和對幸福的向往,在劇中這份控訴和向往,都是由貧民窟這個戲劇意象承載的。如前文所提到的,沃爾特一家在擁擠、昏暗、雜亂的貧民窟公寓里生活,租金卻依然不菲,露絲說過,他們一家在這套公寓房里支付的租金足夠他們買下四棟房子(32),以管窺豹,當時美國社會存在著對黑人極不公平的“住房隔離”現象,也就是說,白人可以有選擇住房的自由,而大多數弱勢黑人群體卻因其經濟拮據,被迫在市區破敗的貧民窟里生活,而且要支付高昂的租金和房屋稅,如要去市郊購房自住,則要能忍受白人甚囂塵上的歧視和打壓。漢斯博雷也坦言,劇中自始至終都貫穿著種族壓迫這根線,無法逃避,這些人住在美國的貧民窟里,恰恰因為他們是黑人,而貧民窟的生活會給他們方方面面的感受產生影響(轉引自Bigsby2006:279)。沃爾特一家的住房情況正是這種住房歧視的縮影,能在陽光下擁有自己的家園,和白人平等地生活,這就是沃爾特一家心之所向。即便他們能夠承擔得起,卻也只是無奈地發現,黑人區建造的房子不僅偏僻,而且“價格是其他地方房子價格的兩倍”(79)。權衡再三后,莉娜在白人區克萊伯恩公園那里買下了一棟房子。買白人區里黑人的房子,這是十分具有象征意義的戲劇意象,Bigsby甚至稱其為“堂吉訶德式的舉動”(1985:384)。雖然白人社區的代表林德納第一時間就造訪沃爾特一家,試圖勸阻他們不要搬過去,使用的論據從同一社區的幸福感,到威脅論等等不一而足,他甚至提出,作為補償,他所代表的白人社區可以高價回購這棟房子。面對未知的—也可能是麻煩重重的將來,沃爾特一家最終還是毅然決定搬到他們買下的房子里去,這個決定象征著黑人民眾對家園夢想不屈不撓的爭取,也體現了如Bigsby所指出的,劇作家對“個人尊嚴”和“個人從自己的選擇中建造身份的必要性”的關照(1985:383)。
關于種族問題,《陽光下的葡萄干》不僅涉及到了普通意義上的歧視或敵視,更涉及到了更深層面的身份認同問題。作為非洲裔美國人,美國黑人們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美國性和非洲性的沖突,特別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風起云涌之時,是在美國扎根,還是去非洲尋根,已然成為黑人面臨的一種文化抉擇。[3]在本劇中,這也正是比莉莎要面臨的抉擇。她在美國長大,耳濡目染的是美國文化,而非洲人的基因卻不斷提醒她要忠于自己的民族根源。劇作家把這種美國性和非洲性賦予在種種戲劇意象上。比莉莎兩位追求者就分別具有美國性和非洲性的代表意義。喬治是美國黑人,黑人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Cheney1984:56),家境富裕,在美國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中熏陶成長,對黑人的非洲遺產嗤之以鼻,認為非洲式的衣著裝飾“非常古怪”,而且所謂的“偉大的西非傳承”不過是“一堆穿著破爛衣裳的精神論者和一些茅草屋”而已(67-68);阿薩蓋則是在北美游歷的尼日利亞人,盡管國家清貧,卻依然深以自己的非洲血脈自豪,面對比莉莎“被殘害了”的頭發和所謂的美國黑人族群中發生的“同化主義”他可謂大搖其頭(49)。在劇中兩人的出場也是劇作家精心設計,喬治衣冠楚楚,斜紋軟呢上衣,開司米羊毛衫,襯衫領帶寬松褲,白色小鹿皮皮鞋,正是這雙白色的鞋子被沃爾特拿來說事:“你們這些上過大學的是不是都穿這種高檔的白鞋啊?”(69)后來又見沃爾特酸溜溜地說:“這個世界上沒有誰比得上你們這些戴著兄弟會徽章、穿著白鞋子的黑人大學生忙了”,“大學里你們學的只是談吐、讀書、穿白鞋子…”(71)白鞋子這個戲劇意象是對美國性的隱喻,即美國主流白人社會的生活方式、成功觀和價值觀,這正是喬治踐行的—也是沃爾特所推崇的,后者因其主流美國價值觀的堅持追求,曾一度接受了只有擁有金錢和權力才能真正成熟的美國式理念(Washington1988:123)。阿薩蓋鄙視這種物質同化主義,他給比莉莎帶來的禮物—來自非洲的頭飾和長袍—也頗具象征意義,它們代表著非洲性,即黑人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根源。第二幕第一場里,比莉莎穿戴上了頭飾和長袍,伴隨著尼日利亞的民間音樂翩翩起舞,嘴里還唱著非洲的歌曲,后來醉醺醺的沃爾特加入后把舞蹈升級為激情四射的非洲部落戰士之舞,這個場景盡管有點鬧劇色彩,卻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美國黑人與生俱來的對非洲文化的親近,在屬于非洲的音符響起時,他們感受到的是來自久遠祖先的文化符號(秦蘇玨2008:48)。對比莉莎來說,親近非洲的根、擯棄“同化主義”是她的精神向往,所以阿薩蓋的求婚并要帶她去非洲生活對她而言有一定吸引力,她甚至也循他的建議改成了非洲式的發型,但是生在美國、長在美國的她卻也知道讀醫學院從而出人頭地、改善家人的生活這條美國特色的道路,是最為實際的選擇。面對喬治和阿薩蓋兩人的追求,比莉莎何去何從?戲劇的結尾并未指明。比莉莎的糾結困惑是千萬美國黑人文化認同危機的縮影,這或許是個無解之局,但劇作家卻意在表明,無論膚色如何,每個民族都有、都不應該避談自己的文化驕傲,無論身處何方,精神的根源都不能忘。正如Abbotson所指出的,劇作家在對待同化主義和對待非洲根源方面都是同等的謹慎,但是它對黑人生活的多樣性和創造力的極大肯定,以及對一代代的黑人在斗爭中展現出來的力量的描述,正是讓該劇成為不朽經典的原因(2007:129)。
四、結語:戲劇沖突與意象之希望篇
如上文所提,《陽光下的葡萄干》是一部關于夢想的戲劇作品,沃爾特一家的夢想雖普通卻真切,或渺小卻感人,他們的夢想到底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希望的崩塌還是啟示錄般的災難(Bigsby2006:278)。
仔細研讀劇本,我們可以發現不少代表希望的戲劇意象,如前文提到的自然意象—莉娜精心呵護的盆栽植物,貌似孱弱卻堅韌不拔,它的活力對莉娜來說就是希望。不管未來怎樣,一家人終于要搬進屬于自己的房子,這是家園的希望。比莉莎抵制住了喬治代表的物質誘惑,認識到了自己的民族根源,學會了理解和寬容,這是文化傳承的希望。露絲懷上了第二胎,盡管她曾有打掉孩子的想法,卻終于在莉娜的勸說下準備把孩子生下來,這是生命的希望。沃爾特遭遇挫折,造成家庭重大損失,卻因此脫胎換骨,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從而真正成為家里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這是家庭團結凝聚的希望。但這些希望的戲劇意象是不是意味著大團圓的結局呢?劇作家沒有落入俗套的窠臼,她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意象來引發我們的思考,實現夢想的希望或許有,但讓人不安的變數同樣不乏。沃爾特一家人實現夢想的曙光是由老沃爾特逝世后保險公司十萬美元的理賠金帶來的,這張理賠金支票在戲劇的開頭曾讓一家人朝思暮想、念念不忘,因為它能促成眾多家庭心愿的實現,可恰恰是因為這些家庭的愿望要通過身故理賠保險這種低概率事件才能實現,我們會對夢想成真的確定性產生質疑—離開了“偶然性十足”的保險理賠(Bigsby1985:381),沃爾特一家離實現家庭夢想會有多遠呢?另一大“不確定”在于,理賠的保險金一部分用來買房,其他的全部被沃爾特投資被騙去,也就是說買了房后沃爾特一家在經濟上又回到了之前的拮據狀態,他們能夠支付每月購房的分期款嗎?(張沖1995:45)決定搬入白人為主的克萊伯恩公園,從此一家人確實能擁有自己的家園,但是家園的上空將是揮之不去的危機,白人社區對他們的歧視甚至是攻訐無疑是他們頭上揮之不去的陰云,在極端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會被驅逐或迫害![4]沃爾特一家的決定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們吃螃蟹的做法在另外一層意義上說也表明黑人族群未能抱團對抗白人社會的欺壓,正如沃爾特的錢被騙這個戲劇意象也意味著黑人需要團結而不是內斗如此總總,我們可以看出劇作家并不是在為夢想的實現大唱贊歌,她冷靜從容地告訴我們,對夢想要有信念,但不可將自己鎖入天真幻想的囚籠之中。我們不禁想起劇本開頭那首意象豐富的小詩,寥寥數語,言盡夢想道路之坎坷:
夢想受挫將會怎樣?
它會干枯得
像一顆陽光下的葡萄干嗎?
抑或像一傷瘡—
潰爛難當?
它會像腐肉般惡臭
或者結滿硬皮、渾身裹糖—
甜如蜜漿?
或許它只是不堪負重
下沉晃蕩。
或許它會迸裂如炸彈?[5]
殘酷的社會現實密謀要挫敗黑人家庭的期望(Abbotson2007:117),追夢的人在踽踽前行,唯有不屈的意志能讓他們朝著夢想邁進。或許這正是劇作家的本意,她有意識地抵制絕望的戲劇,確定人性的潛力能超越人性的殘忍,而且弘揚人性頑強的意志(Wilkerson2001:144)。這部戲劇也是對上面那首小詩中設問的回答:夢想或者干枯,抑或迸裂,但是如沃爾特一家的追夢人們卻不懼在現實的壁壘上碰得頭破血流,他們的堅持和斗志讓他們光芒萬丈。從這個意義上說,《陽光下的葡萄干》就是一個源于沖突卻旨在贊頌的戲劇隱喻,贊頌生命的堅韌,贊頌存在的頑強,也贊頌未來的希望。
參考文獻:
Abbotson,SusanC.W.Masterpiecesof20th-CenturyAmericanDrama[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Bigsby,C.W.E.ACriticalIntroductiontoTwenti eth-CenturyAmericanDrama.Vol.3:BeyondBroadway[M].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
Bigsby,C.W.E.ModernAmericanDrama:1945—2000[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Cheney,Anne.LorraineHansberry[M]. Boston:TwaynePublishers,1984.
Hansberry,Lorraine.TheOriginofCharacters:A ddresstotheAmericanAcademyofPsychotherapists[Z]. NewYork,5October1963.
Hansberry,Lorraine.ARaisinintheSun[M]. NewYork:NALbooks,1966.
Hansberry,Lorraine.TobeYoung,GiftedandBlack [M].NewYork:NAL,1969.
Hewes,Henry.APlantGrowsinChicago[J]. SaturdayReview42(April4,1959).
Littlejohn,David.BlackonWhite:ACriticalSurve yofWritingsbyAmericanNegros[M].NewYork:Gross manPublishers,1966.
Washington,J.Charles.ARaisinintheSunRevisited [J].BlackAmericanLiteratureForum,Vol.22,No.1,Blac kWomenWritersIssue(Spring,1988).pp.109-124.
Wilkerson,MargaretB.ARaisinintheSun:Anniv ersaryofanAmericanClassic[J].TheatreJournal.Vol.38. No.4,TheatreofColor(Dec.,1986).pp.441-452.
W i l k e r s o n,M a r g a r e t B.A f r i c a n Americanplaywrightsatmid-century[A].TheCam bridgeCompaniontoAmericanWomenPlaywrigh ts.Ed.BrendaMurphy.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pp134-152.
秦蘇玨.走向夢想:從《陽光下的葡萄干》中男子氣概的重生看美國黑人的雙重意識[J].四川戲劇.2008年第2期.pp46-48
張沖.面對黑色美國夢的思考與抉擇:評彼得遜的《跨出一大步》和漢絲貝里的《陽光下的干葡萄》[J].國外文學.1995年第1期.pp41-45
注釋:
[1]1959年漢斯博雷是作為第一個黑人劇作家,也是最年輕的劇作家,同時也是第五位女劇作家獲得該榮譽的,《陽光下的葡萄干》還是第一部由黑人女劇作家創作并在百老匯公演的劇作,也是百老匯由黑人作家創作并在四分之一個世紀里公演時間最長的劇作。漢斯博雷獲獎時擊敗的正是奧尼爾和威廉斯這兩位美國戲劇巨擘。
[2]本文中戲劇人物對白皆出自劇本ARaisin intheSun,NewYork:NALbooks,1966年出版,為筆者自譯,下同。
[3]W.E.DuBois把這種情況稱為“雙重意識”,即受到兩種不同文化的影響,他們發現要忽略任何一方都必須犧牲自己一部分的身份,如要達到非洲傳統和美國經驗的平衡,黑人的價值體系就會出現問題(轉引自Abbotson2007:126)。
[4]劇中搬入白人社區這個情節設定來自于劇作家自己的親身經歷,在她八歲時,一家人搬到了排斥有色人種的白人社區居住,結果遭到了無窮無盡的騷擾并最終被驅逐,雖然父親后來訴諸法律而且勝訴,這對他們一家的生存環境權利卻于事無補。可見劇作家對沃爾特一家搬家的決定并不抱有幻想。
[5]此詩為《陽光下的葡萄干》開篇,由蘭斯頓·休斯所做,筆者自譯。
責任編輯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