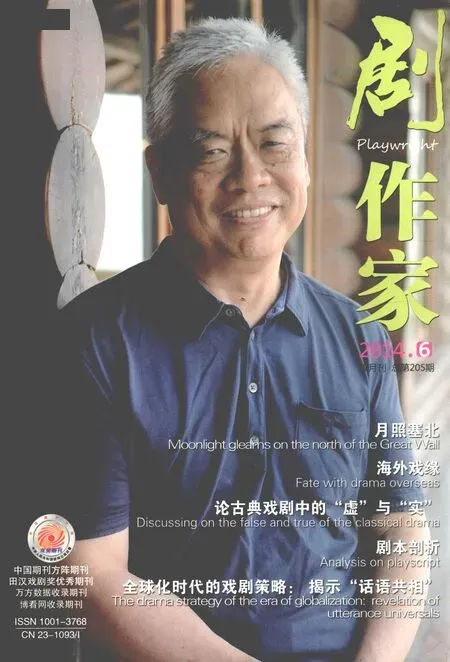也談音樂劇的創新和本土化、民族化——《悲慘世界》帶給中國音樂劇的啟示
林宏偉 駱麗曼
也談音樂劇的創新和本土化、民族化——《悲慘世界》帶給中國音樂劇的啟示
林宏偉 駱麗曼
隨著《歌劇魅影》《悲慘世界》《貓》《獅子王》等西方經典音樂劇的推出,音樂劇一次次以春天般隆重而盛大的場面,夏天般令人無法拒絕的熱度,乃至以秋天般不修邊幅的姿態,闖入國人不及準備的視野和心里。而更令人驚嘆的是,音樂劇已大大超越我們對它的最初印象,它不僅是早年百老匯式的輕歌舞喜劇了。經典的現實主義名著,超現實主義的荒誕情景、浪漫主義的童話故事,甚至更為深刻的人文思想,都可以通過舞臺、電影、動漫等音樂劇形式加以表現。音樂劇的藝術空間已進入一個全新維度,不得不讓我們以更莊重的心情、崇敬的目光迎接它和審視它。
縱觀美國音樂劇發展史,不難發現其成功的兩大法寶:創新和民族化、本土化。在表現形式上注重流行性,采用濃郁美國風情的黑人民謠、藍調和爵士樂。《出水芙蓉》甚至將芭蕾舞進行華麗包裝和富有音樂劇式的喜劇化處理;在內容上,展現地道的美國人生活。《演藝船》、《俄克拉荷馬》等劇都特別注重民族化和本土化;即便引進劇目也極力迎合美國觀眾的觀賞習慣和口味,再火爆的音樂劇搬到美國也要重新制作包裝,打上美國烙印。
就拿《悲慘世界》這部著名的音樂劇來說,該劇最初的法語首版并不成功。1985年10月,英國戲劇家麥金塔與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為英國觀眾改編的英語版《悲慘世界》首映。盡管當時對該劇的評論多為負面,很多學者譴責它把文學經典改編成音樂劇。但出乎預料,演出獲得英國觀眾的極大熱捧,不僅創造了當時的票房紀錄,而且轟動了整個世界。連美國百老匯都為之傾情,忍不住改編這部音樂劇。面對一部如此成功的劇目,百老匯依然本著其“創新和民族化、本土化”法則,執著地進行了很多新的嘗試和改編,使之完全變成百老匯版本。從1987年首演至2003年就演出6680場,并贏得包括最佳音樂劇等8項托尼獎。這僅是開始,隨之而來的無數巡回版、國際版和地區版被搬上舞臺,使之紅遍了全世界。
然而,反觀我國的音樂劇,從1982年上演的國產首部音樂劇《現在的年輕人》開始,到今天三十多年間,我們音樂劇人不可謂不努力不進取,創作和演出劇目不可謂不多,題材和風格不可謂不豐富,更不乏大投入和大制作。并且咱也一直強調創新和本土化、民族化。可這么多年,國家傾力,省市傾力,竟沒有一部常演不衰的音樂劇在劇場里保留下來。這不能不讓人唏噓和反思,咱的音樂劇到底差到哪兒?
路子不對,指導思想不對?“創新”、“本土化”、“民族化”沒錯啊!沒錯嗎?咱不妨剖析下這三個詞匯。創新之前,先問問自己:憑什么創新,有沒有資格創新?然后再談創什么新。創新應先有舊的方可創出新的。咱有舊的嗎?在別人舊的基礎上創出新的也是別人的。核芯、主板、系統是別人的,外殼創的再新,充其量一外包代工。藝術這東西不倫不類,就算便宜白送也沒人買賬。到頭來付出再多還是沒有自己的東西。什么是自己的東西?顯然,本土的民族的才是自己的。
就音樂劇來說,什么是自己的本土的民族的呢?要我說就是中國戲曲。先別噴,戲曲和音樂劇兩個概念?你說的!中國漢字“曲”和音樂、“戲”和劇同義,倆字合起來就是音樂劇。說白了,戲曲是中國音樂劇。當然,說戲曲是中國傳統音樂劇更恰當些。如果想不通,假設一下,假設沒有白話文運動,今天我們一定把西方音樂劇叫做西洋戲曲。
如果承認這種說法,咱就找到自己的本土的和民族的東西了,咱便有資格和資本創新了。中國“本土的和民族的”音樂劇就是戲曲,戲曲就是中國音樂劇創新的出發點。如果中國音樂劇人在這點上有所共識,那咱的音樂劇起點就很高了。咱們有豐富多彩的各民族戲曲;有風格迥異的眾多地方戲曲;許多戲曲都曾有過很長時間的繁榮和輝煌;更有許多耳熟能詳至今仍在上演、可以媲美西方任何一部音樂劇的優秀劇目。
在此基礎上,探討如何創新咱自己的現代音樂劇——核芯、主板、系統是自己的,進而運用和借鑒中外現代技術、理念和風格去創新,是不是更有底氣,也更有方向!
責任編輯 劉 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