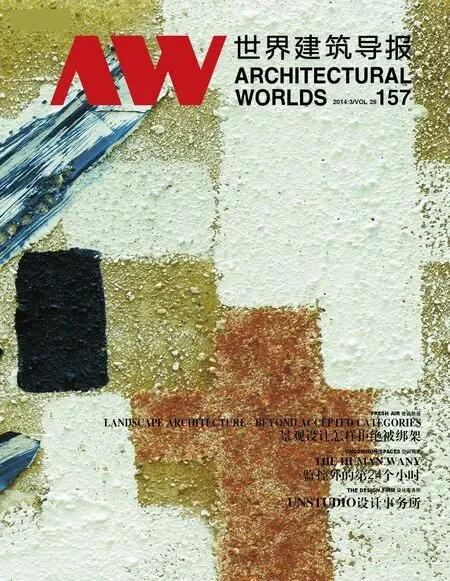監控外的第24個小時
(文)吳彥 (圖)Ahmet Ogut

In her case file on Ahmet Ogut, Wu Yan turns the artist’s methodology against him,“stalking” his ongoing urban interventions. Wu Yan notes that she hasn’t actually seen one of his works. Instead, she has experienced them after-the-fact, in retrospective lectures and documentation. But this after-the-fact appreciation of an artist such as Ogut is perhaps the point. His work continuously points to invisible cities, which run parallel to the so-called real world and thereby highlight the tensions and ideosycracies at play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Ogut was born in 1981. He currently lives between Istanbul, Amsterdam, and Berlin.In 2009, Ogut represented Turkey in the 53rd Venice Biennale.
我見過Ahmet Ogut 。但很遺憾,還沒有機會親身經歷過他的作品。目前為止,所有的體驗都是通過他事后的轉述:講座中的前傳后續,回顧展里的影像文獻,還有就是網站上的圖片文字。這里面確實有機緣的關系,但也不得不歸咎于作品本身的機關重重。我很好奇置身于描述里那個世界的感覺,因為那個世界一定是發生在現實之外的。但他又讓我肯定,現實并不是存在的唯一場所,我需要找到的是一種進入的方式,轉述提供的僅僅是過去的線索,行動的目的在于下一秒的改變。耐心點。
其實,每個藝術家都應該有屬于自己的創作媒介,盡管Ahmet Ogut的作品呈現方式廣泛,包括繪畫、攝影、錄像、裝置、行為、藝術家書等,但我會堅持把他的實踐歸納為策略藝術。策略藝術不同于觀念藝術,觀念藝術側重思維模式,策略藝術付諸行動,還得是漢娜·阿倫特定義里的那種公共行動。1981年,Ahmet Ogut出生在土耳其迪亞巴克爾一個典型的庫爾德族家庭。目前在伊斯坦布爾、阿姆斯特丹、和柏林之間游移、生活、工作。2009年Ahmet Ogut代表土耳其參加了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
線索一
2009年的某一天,圣路易斯的多處公共場所莫名間冒出了一批以假亂真的安全標識牌,牌上寫著“警告:此區域23小時視頻與音頻監控。”或許我要找的進口位置就發生在那被解放的第24個小時里。游戲開始了,我得找到他。

線索二
回到2005年的伊斯坦布爾。我,身份不明的車主辦事歸來,暫時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這應該并不重要。假想兩組場景:面前的私家車被紙板裹成了不容錯過的黃色出租車,或者,被貼上了藍白紙條外加紅色頂燈,改頭換面成了執法用的警車。的確都是他干的,在光天化日里。
線索三
應該也是在2005年,只有那一天的機會,吊車把我升到了巴塞爾美術館二樓的高度,我記不清他那會兒的位置了。就這樣,我透過玻璃往里看作品,隔著墻,逛了一圈樓上的美術館。還是沒什么人。天藍的連一絲云都沒有,所以稍稍有些反光。看見我了嗎?
線索四
他告訴我:“伊斯坦布爾那天天氣不錯,我就在小巷里瞎逛。轉眼間停電了。我摸著黑繼續往前走。面前突然橫著輛小摩托,頭燈開著,燈光直射進路邊的地下室。我趕緊湊近了,透過玻璃往里看。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特別喜歡故事里最后的那句話,纏著他又給我說了好幾遍,說著說著,我們從伊斯坦布爾走到了柏林。
線索五
“記得2011年新西蘭的旋轉車站嗎?”他問我。
“當然。我在維多利亞廣場你告訴我的那個位置等了很久。先是因為地震沒出現,后來好心的路人告訴我它已經被搬走了,結果我只能站著等。對了,那里面一共有幾個車站?”我想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盡量積極一點,其實那段回憶有些乏味。
“兩個。來回轉。”他漫不經心地回答道。
線索六
他一般話不多,偶爾會有眉飛色舞的時候,比如現在。
“2008年的夏天,Jacob Fabricius邀請我參加一個由他策劃的叫‘搭便車’的項目。項目要求美術館所有的工作人員在整個6月里以搭便車的方式走遍瑞典南部,并同時根據參展藝術家的指示或做行為表演、或推廣介紹作品,或散布文字介紹。包括Jacob在內的每個工作人員必須代表一個參展藝術家,搭便車兩天。一聽到這個項目,我就特別激動,立馬告訴Jacob我在土耳其念本科時幾乎每天搭便車的故事。最后我交的方案叫‘將軍搭便車’。‘將軍搭便車’是由Olof Olsson表演的。兩天時間里Olof穿著將軍制服,提著兩面小國旗,等著搭便車。每次有人答應載他一程,他得讓司機同意把那兩面小國旗插在汽車前蓋上,直到將軍下車,這樣便車看起來就像官方車輛了。這就是權力結構里荒謬的地方。套上制服的搭車人便不再是簡單地要求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而成了路人無法忽略的戰略符號。整個過程里讓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匆匆擦肩而過,沒有停留的車輛。他們或許看到了‘將軍’,但根本沒有機會求證究竟這是真的,還是假的。這個流動的瞬間就是藝術行動。因為無法停車與現實求證,這一刻會永遠困擾在司機的腦海里。”
線索七
在柏林聞到‘地面控制’里的瀝青味時,我一陣恍惚。第一次被那股味沖到,是在伊斯坦布爾,鋪滿瀝青的地板,空間的大門敞開著,直對大街,路邊踢球的小孩盤著球,順勢就溜進了美術館,一氣呵成,也沒什么規矩。柏林的場地首先在建筑特點上就要深邃很多,據說實現的過程里還不乏波折,美術館對瀝青可能造成的健康影響頗為擔憂。作品換了個地方,就換了個味兒,現代化之路還很長。
線索八
一時興起,我決定加個小機關。我把第八條線索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