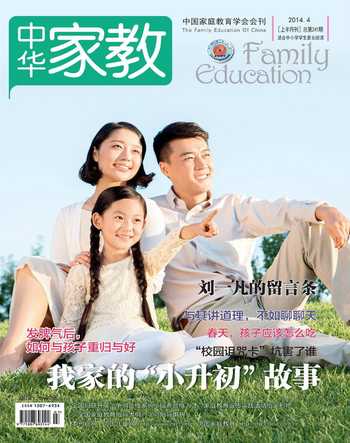再談家教三大誤區
在中國傳統教育上,“聽話”成了“一條鞭法”。在封建時代,普通百姓求得生活安穩,自給自足,不惹是生非,做一個老實人就可以了。在那種社會環境下確實不需要自我意識,不需要創新意識,不需要民主意識,只需要絕對服從。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孩子的自我受到壓抑,長此以往孩子就在無所適從的扭曲、矛盾中長大,然而這一切都隱藏得很深,直到孩子平庸、無能、出問題時,父母們才奇怪并無比痛惜地說“這孩子很聽話很聰明的”。
在一項全國性的獨生子女人格發展調查中發現,在被看作“聽話”的孩子中,自述膽小的占34.3%,不愛提問的為38.8%,對創造發明不感興趣的為27.5%。淘氣是孩子的天性,能夠堅持自己的看法,不人云亦云,是人格意識的基本表現。“聽話”不是沒有問題,也不僅僅是怕懲罰不敢提出反抗,而是因為孩子依戀著父母,不愿挑戰父母的權威,他們不想因為自己做了父母不喜歡的事而傷害父母。父母應該主動提供寬松自由的環境,不讓孩子壓抑自己,“乖乖生”出問題或自殺的比例遠高于淘氣的學生,父母們應該反省了。
從心理成長上看,“不聽話”是孩子獨立性的需要,是自主意識發展的表現。三四歲時是第一反抗期,在具體動作活動上表現為“我自己來”;青春期是第二反抗期,要求全面的人格獨立,“我的事情我做主”。
從心理健康上看,孩子在不愿意時,能把想法用情緒、行動表達出來,這是維持自身心理平衡的需要。如果他完全聽話時并不表明他愿意,只是表明他開始進入壓抑。
能“犟嘴”的孩子其實會更健康,這表明他在作更高層次的探索,即自己個人的心理強度到底有多大?外界的權威到底又是個什么東西?“爭辯”是應付沖突的訓練,“抗旨”是有目的地尋找自己能力的極限,許多人一輩子都接觸不到自己的底,摸不到自己的邊,他們是懸空的,他們一輩子與焦慮與恐懼打交道。
打罵是“聽話教育”的變種──當孩子不聽話時,父母、老師為維持權威,便自然而然地實施了這一招。
經常受打罵、受喝斥的孩子,永遠享受不到寧靜的心境,他的神經系統永遠是緊張的,他的激素系統總是在失衡狀態,表現在外部就是孩子食欲不強,多夢易驚,不能集中注意力,易怒易躁,喜歡打罵人,可以說睡眠、進食、智力、情緒都處于極大的破壞、摧殘狀態,本該燦爛的內心體驗變得黑暗一片。
在心理門診經常遇到這樣的孩子,一位父親講述了自家孩子的問題。三歲的孩子在幼兒園尿了褲子后失蹤了,老師給父母打電話,父母急匆匆趕到幼兒園時,孩子已經找到,原來他自己躲在廚房后面哭,后來發展到不愿去幼兒園了。問孩子為什么要尿尿卻不跟老師說,孩子說怕老師罵。老師不一定罵過他,但可能罵過別的孩子,也可能父母本身喜歡罵,害得孩子更怕老師。
還有幾年前發生的一起幼兒被悶死在校車內的案件,語言暴力也是導致悲劇發生的間接原因。該校車司機呵斥孩子“不許下車”,結果孩子在司機的威懾下,到達目的地后也始終不敢下車。司機下車揚長而去,孩子被長時間關在車內,窒息而死。
溺愛是“聽話教育”的另一類變種──即父母放棄權威聽命于孩子,反正都要聽話。在生活中不難看到這樣的現象,父母寵愛
幾個子女中的某一個,結果那一個卻是最不孝的,對父母態度之惡劣令人發指。我們該同情誰呢?我說父母是在自食其果,因為父母早年包辦了孩子的一切,剝奪了孩子心理健全成長的權利,沒有盡到父母的責任,孩子在驕縱下越發唯我獨尊、自私自利,對父母指手畫腳或不屑一顧,甚至肆意踐踏、傷害父母。
溺愛對孩子傷害于無形,卻是更嚴重的,它與打罵完全不同。被打罵的孩子受壓抑,其壓抑的能量在不良環境中會畸形暴發出來,但在正常環境則可能只是影響人格。而一味地溺愛孩子,當孩子的愿望實現得太容易時,他們就會認為是應該的,而且當他們長大后反而認為社會倒欠他們一筆債。當家長向孩子的無理取鬧投降時,父母實質上是在教孩子反過來控制那些傾心關愛照顧他們的人。驕寵過度的孩子目空一切,為所欲為,不知道德為何物,如果將來社會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將無所顧忌地肆意妄為。
十五年前我還在上海的兒科醫院實習時,親眼所見一個患腎炎的九歲女孩,要求父母哭夫妻倆就哭,命令父母下跪他們就下跪。她跑到醫生辦公桌上亂扔東西,醫生說了一句,她打開墨水瓶潑得醫生滿臉滿衣。臉可以洗凈,那件白大衣卻不能再洗白,它警醒著父母們溺愛其實是傷害,傷害了孩子,也傷害了父母自己。
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培養孩子形成自主性人格,只有人格獨立才能真正健康地適應社會。聽話是不允許孩子自主,打罵也是不允許孩子自主,而溺愛則是超越社會道德的自主。父母們切記時常提醒自己,避免身陷上述三大家教誤區。
(黃懷寧 原心理科副主任醫師,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