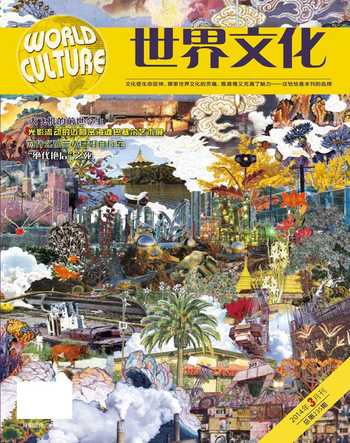源頭活水一枝梅
張晶鑫

一枝梅是古代朝鮮歷史故事及民間傳說中與洪吉童和林巨正齊名的三大俠盜之一,深受朝鮮半島人民的喜愛。1975年高羽榮創作的長篇歷史漫畫《一枝梅》更是將這位出身于社會底層的俠盜形象升格為韓國文學史上家喻戶曉的傳奇英雄,不僅該漫畫被評為“代表韓國的一百種書”,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枝梅也憑借極高的人氣入選 “代表韓國的漫畫人物”系列郵票。
若談及一枝梅這一形象的最初來源,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的史書、類書、雜書、民間傳說以及話本和小說創作中同一枝梅相關的人物與故事屢有出現。這些珍貴的文字記載雖散見于一些古代文學典籍中,但足以能窺得韓國的《一枝梅》與中國文學的緊密關聯。從流傳學角度對這些事實聯系進行一番粗疏的整理和分析后,筆者驚喜地看到俠盜一枝梅這一形象不斷發展、演變的歷程,猶如其“前世”與“今生”的輪回一般。
在《辭海》中,“俠”舊稱“扶弱抑強,見義勇為的人”,而“偷”則被解釋為“竊取,背著人做事”。從字面上看,“俠”與“偷”一褒一貶,其意義可謂大相徑庭。而在中國,自春秋戰國時起,就有人將二者合而論之,并逐漸衍生出“俠盜”這一名詞。早在戰國中期,莊子就曾提出“盜亦有道”的觀點,在《莊子·外篇·胠篋》中,跖之徒問于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該文中,偷盜者被賦予了“圣”“勇”“義”“智”“仁”這五種美好品質,作者通過“道”給“盜”以合理性、合法性,從而將“俠”與“盜”成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俠盜”的最初思想淵源。隨后,司馬遷又于《史記·游俠列傳》中概括了“俠”的本質,稱:“今游俠,其行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矣。”莊子和司馬遷的闡釋成功地將“俠”與“盜”進行了靠攏,提升了其精神特質,并賦予它一定的理論價值,為后世文學作品中俠盜形象的脫穎而出奠定了基礎。
在宋代,話本、擬話本興盛一時,許多妙趣橫生又寓意深刻的小故事于此時期誕生,其中不乏講述俠盜的篇章,如《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宋四公義救被張員外欺負的乞丐,并偷盜張員外財物的故事雖然與之后描寫一枝梅的短篇小說情節出入甚大,但很明顯二者之間有一種繼承和影響關系,以鄭振鐸先生為代表的不少學者還認為《二刻拍案驚奇》中神偷懶龍(一枝梅)的故事就脫胎于該話本。
元明時期,大量的筆記小說、話本小說不斷涌現,它們中既有作家對前代史料、傳說和小故事的收集整理,也有作家于先人基礎上的改編創作,而俠盜的故事在這些作品中占據了不小的比重,為之后一枝梅的定型做了很好的鋪墊。明代黃日韋的《蓬窗類紀》卷五《黠盜紀》等作品中記載的黃鐵腳用豬脬妙偷酒壺的故事,不僅生動地刻畫了其機智和老練,也成為日后“一枝梅”系列故事中的重要元素。
如果說黃鐵腳為一枝梅的出現奠定了豐富的情節基礎的話,那么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余卷二十五和陶宗儀的《說郛》卷二十三諧史中的“我來也”則對一枝梅的最終定型有著極大的助力。“我來也”是宋代臨安的一個大盜,不知姓字名誰,入室偷盜于無形,因每次作案后都在墻壁上寫下“我來也”三個字而得名。有一次他失手被擒,憑借機智博得獄卒信任,得以化險為夷,事后贈獄卒重金以作報答。作者雖未道明“我來也”是否是個俠盜,但他的機智和義氣盡表于故事當中,堪稱俠盜一枝梅的雛形。
可以說,到此為止,一枝梅的形象雖然并未定型,但其性格和事跡已有了基本輪廓。明末凌濛初的短篇小說集《二刻拍案驚奇》的出現,終于賦予了該形象完整的“生命歷程”。在這部小說集的第三十九卷《神偷寄興一枝梅俠盜慣行三昧戲》中(與之類似的情節還出現于同時期西湖漁隱的文言小說集《歡喜冤家》的第二十四回《一枝梅空設鴛鴦計》),作者通過十幾個系列小故事生動講述了活躍于明代嘉靖年間的神偷懶龍劫富濟貧的事跡。小說中的懶龍身材小巧,膽大心細,身懷絕技,是當地有名的神偷,因他每次行竊后都在墻上畫一枝梅花而得名“一枝梅”。
該小說共有16個子故事,“入話”講述了孟嘗君門下一個善于雞鳴狗盜的門客和宋代臨安的大盜“我來也”,而“正話”,即后14個故事則集中描寫了懶龍的事跡,具體來說,可分為六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1個故事,可算個引子,寫懶龍盜墓時于機緣巧合下得了一枚銅鏡,此鏡可在黑夜中為之照亮,成了懶龍的法寶,而通過其厚葬尸首這一細節表現了他“盜亦有道”的品格。
第二部分由第2、3兩個故事組成,寫懶龍偷富濟貧,驗證了他“損有余而補不足”的人生哲學。一個故事記敘他本欲去富商周甲家偷盜,不想卻誤進了一對貧賤夫妻的房舍,隨后趁夜取了周家二百兩銀子,贈與這對夫妻;另一個則講述了他偷取銀子接濟一位自小與他相識的貧兒。
第三部分由第4、5、6三個故事組成,記敘懶龍在偷盜過程中遭遇窘境時,如何憑借機智轉危為安。行竊中,他曾被反鎖于衣櫥中,被女主人捉住過腳踝,也曾用寶鏡照亮時為人察覺、追趕,但最終都化險為夷。
第四部分由第7、8、9、10、11五個故事組成,主要寫懶龍以“偷”來游戲人生,在這些小故事里,他有時娛人娛己,和友人打賭,有時則因某種原因戲耍一下他人,偷的東西大多原樣奉還,張巡鋪的鸚鵡、店家的酒壺、福建公子的錦被、米店的糧食和道士的板巾,懶龍皆偷去過,可最終又都物歸原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小人不曾有一毫贓私犯在公庭,亦不曾見有竊盜賊伙扳及小人。小人只為有些小智巧,與親戚朋友作耍之事,間或有之。”
第五部分由第12、13兩個故事組成,寫懶龍和貪官污吏的斗智斗勇。面對貪婪的無錫知縣,懶龍先偷去了他兩百金子,見其不改,又剪了他家小孩兒的發髻以示警告,而面對逼迫他偷盜巡按御史印信的吳江知縣,他勸其還印,可這貪官不聽,最后落了個罷官入獄的下場。
第六部分即第14個故事,講述了懶龍被人冤枉后如何自白。適時,蘇州府丟失銀元寶十來錠,矛頭直指懶龍,實則是庫房官吏監守自盜,張小舍為他澄清,他贈銀送刀,既感謝又警告,而后金盆洗手,得以善終。

從情節上看,這些故事是對前代史料、話本和筆記小說等的整理和創新,在描寫懶龍的14個故事中,大多皆是作者原創,但也有幾個故事是對前代資料的重復或改編,如第8個故事的后半部分,懶龍偷酒壺可見于明代黃日韋的《蓬窗類紀》卷五《黠盜紀》、馮夢龍的《古今譚概》卷二十一《譎知部·黃鐵腳》《智囊·雜智部·狡黠》卷二十七《黃鐵腳》,只是主人公由黃鐵腳變成了懶龍;第13個故事巡按御史失印后設計得印這一情節則可見于明代宋懋澄的《九龠集》卷十《海忠肅公》、馮夢龍的《古今譚概》卷二十一《譎知部·海剛峰》等作品,而第4個故事懶龍被困于衣櫥中,學老鼠叫而脫險則與《水滸傳》中時遷到徐寧府上盜鉤鐮槍類似。
從立意上看,這部短篇小說著重描寫的是懶龍的機智和手段,雖不乏對其俠義之舉的描寫,但所占比重仍比較小,故事輕松幽默,有著豐富的想象力,符合市民趣味。
大約在李氏王朝后期,該故事傳入朝鮮半島,深受當地民眾喜愛,于是漸漸有了俠盜一枝梅的傳說。然而,在古代朝鮮歷史上,關于一枝梅的記錄只有“義賊一枝梅偷出貪官污吏們的財物來拯救良民,之后留下梅花”這短短一句話,1975年韓國著名漫畫家高羽榮的長篇歷史漫畫《一枝梅》使這一形象得到了飛躍性發展,主要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出生于古代朝鮮貴族之家的一枝梅因其母白梅的婢女身份,剛剛落地就遭到貪戀功名的生父拋棄,幸為乞丐杰赤和僧人涅空所救,后又得后金貴族夫婦撫養,學得一身武藝,12歲時被間諜王橫步騙回朝鮮。在朝鮮,一枝梅在遭到生父二次拋棄以及痛失初戀和恩師等一連串打擊后,流落東瀛,機緣下精熟了中、日、朝三家武學。21歲時重返朝鮮,以黃金梅花為信物,成為一名匡時濟世的俠盜。他懲治貪官惡霸,救濟貧苦百姓,暗中協助清正廉潔的捕盜官具滋明屢破奇案,掃平鳳仙派和海東青派兩大盜賊團體,并和以金自點為首的陰謀集團展開了殊死的斗爭。在懲惡濟貧,艱難尋母的同時,他還和沒落貴族小姐月姬演繹了一段哀婉感人的愛情故事。然而,最終后金的興起、明朝的衰落和朝鮮的動蕩迫使其忍痛告別月姬,返回遼東和當地智勇雙全的武官亮布一同救助難民……
于中國長大,熟諳中國文化的高羽榮在中國古代小說和史料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經歷,創作了這部集歷史性和自傳性于一體的長篇佳作。它以一枝梅的成長歷程和行俠事跡為主線,摻雜行俠、求學、愛情、親情、友誼、陰謀、時局、尋母、著書等多條子線索,描寫了古代朝鮮王朝上至世道貴族,下至貧苦百姓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涉及廣闊的歷史生活圖景,主題深刻、風格清新,同時還不乏各種幽默元素,塑造了總是橫著走路的墻頭草王橫步和理論強、實踐差的貴族學士裴善達等喜劇形象。而在逆境中百折不饒,始終以九死未悔、堅忍果敢的決心尋找著夢想與希望,追逐著信仰和仁愛的主人公一枝梅更是寫盡了亂世英雄的情與淚。恰如韓國影視明星姜富子所說:“《一枝梅》讓我們哭,讓我們笑,展示了世界黑暗的一面,卻讓我們對光明充滿希望。”
2009年初,由該漫畫改編的24集名品史劇《一枝梅歸來》(每集70分鐘)于韓國MBC臺上映,使這一故事的含金量再一次提升。此影視劇在尊重漫畫主要情節、風格特色和感情基調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番改編和再創造,扼要地說,二者的不同之處有以下幾點:
風格特色上,漫畫輕快舒緩,常以幽默的對白和辛辣的諷刺來賦予故事深刻的內涵,而影視劇嚴肅深沉,風格沉郁,頗具史詩氣勢,配以優美的畫面和純音樂呈現出一種更為深刻、唯美和壯闊的視聽效果。
人物形象上,漫畫中的主人公色調較為陰冷,在與古朝鮮貪官污吏斗智斗勇的過程中手段不乏狠辣,而影視劇卻著重彰顯了其仁愛精神和道德意識,通過一枝梅對周遭親友的關護和對敵人的寬恕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的寬容和友愛,以“潤物細無聲”的手法滲透出較強的教化色彩。
情節立意上,漫畫通過精彩的故事和幽默的對白,旨在表現艱難時局中人們的掙扎與拼搏,而影視劇使用鎖閉式結構和大量的畫外音揭示了古朝鮮豐富的生活圖景和人物復雜多變的心理活動,并一改漫畫中的開放式結尾,以10年后再返朝鮮的一枝梅與月姬母子一家團聚收尾,并在故事的最后通過一枝梅的夢境和他對時代和英雄等問題的反思,指出需要召喚英雄的時代并非是一個好時代,彰顯了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從而加深了作品的主題和立意。
在漫漫的文學史長河中,一枝梅這一形象從中國的史書、類書、民間傳說以及話本和小說創作中萌芽、產生、發展,進而向東亞地區流傳,形成了豐滿的人物形象和完整的故事。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通過各國愈加頻繁的文學交流,這一故事系列必將被注入新的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