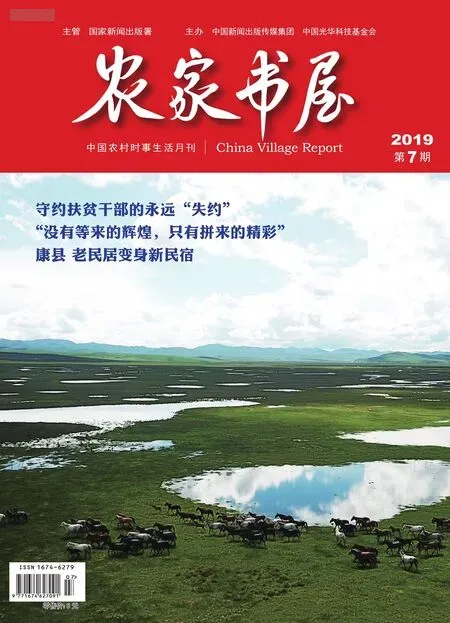下鄉養兒:讓鄉村與童年更近
盛湘潁
“窗戶的燈光照著院子,雞鴨狗兔羊都安安靜靜,天天坐在我腿上,我抱著她。村子里有說話的聲音、狗叫聲、電視響聲、蟋蟀叫聲,還有燒火的煙味、做飯的香味,泥土的濕味。過兩天我們就可以去西瓜地買西瓜,種白菜和蘿卜……中秋節我們可以看到清清楚楚的月亮……冬天燒土暖氣的時候,我們可以在爐子里烤我們自己種的紅薯。”
在新近出版的《下鄉養兒》一書中,馮麗麗以日記形式記錄了她和丈夫帶著女兒天天搬到京郊農村,用親近自然療法治愈家庭的失敗與傷痛的故事:因孩子恐懼上學,連睡覺都怕,跟校方溝通、接受心理輔導都無果,這對夫婦辭工下鄉帶孩子,在農村呆了4年,最終讓孩子找回快樂,返城讀書。
其實,即使沒有這本書,“下鄉養兒”的話題,也讓不少為人父母者有著參與討論的熱情。課業負擔的沉重、日漸污濁的空氣、不再安全的食物,讓人想念鄉村的遲緩與清潔。可以說,“下鄉養兒”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育兒可能,卻也是一場奢侈大膽的行為。無論是幾年前北大MBA夫婦帶女兒隱居終南山,還是最近武漢7對父母帶孩子回農村自教的現實案例,下鄉養兒既是一個熱鬧的話題,同時也是一個尷尬的存在。
武漢山村:7對父母的選擇
“下鄉養兒”對成日困于城市車馬喧嘩之中的家庭,很有吸引力。下鄉識野趣,親近大自然,關心糧食和蔬菜,不僅符合孩子的天性,對成年人也是一種愉悅的生活體驗。正因返璞歸真,回歸了鄉土的樸素人情,馮麗麗夫婦才找到了更符合孩子天性的成長環境,孤僻、膽小、沉默的孩子,重新回歸自然、健康的成長狀態。
馮麗麗一家在京郊山村居住了四年;無獨有偶,一年多前,武漢也有7對父母將孩子從武漢市區帶到黃陂區木蘭鄉,他們在一個小山村找到一所廢棄小學,改建成集住宿、學習一體的場所后,家長充當起老師,閑時就與孩子一起開荒種地。
這7家家長是好友,平時總帶著10個孩子在一起玩兒、讀書。孩子長大后,大家覺得在城市奔波相聚浪費時間,顧及空氣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便萌生了搬到農村去住的想法。
他們選擇的這個山村并不封閉,村里建筑整齊漂亮,村邊小河潺潺,周遭小山環繞。合伙租下村中一所偏安一隅的廢棄小學,簡易裝修后,大家便從城區搬來安營扎寨;除了偶爾利用周末回城度假,多數時間都住在村里。
宿舍樓后院,是家長帶著孩子開墾的菜地,白菜豌豆長得郁郁蔥蔥;廚房里堆放著有機稻米和周邊村民送來的南瓜。“過簡單的生活,只吃素食,穿最普通的衣服,一個月有300元錢就夠了。大家彼此關系單純,每晚8點就上床睡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一位媽媽說。
在山村,孩子們的教育全由家長授課。早晨7點半起床,吃過早飯,孩子們坐在蒲團上,誦讀四書五經;之后,大些的孩子學數學、書法課程,數學課主要由游戲和故事等手法構成,講求實用性。3歲以下的孩子主要就是玩。每周五,孩子都要去周邊小山“探險”,摘野花找石頭。周六有一節英語課,跟老師朗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遠離城市的污染和喧囂,保護孩子的天性,盡可能給他們自由,一片沒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環境,陪伴他們一起學習和成長,這就是我們想給孩子們提供的生活。”一位媽媽這樣解讀她心中的“世外桃源”。
在山村,孩子們有專門的圖書室,擺著教育、科學、繪本類書籍。孩子們沒有考試,但也有任務,是跟家長一起刷墻布置教室、填埋垃圾、種菜澆水等,大點的孩子自己手洗簡單衣物。“很多人以為教育就是上學考試。而我們認為,讓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勞動、讀書,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們可以在自然中學習,從模仿父母中學習。”家長之一萬老師說。
下鄉養兒利弊何在
據了解,武漢7對父母中實際常在鄉村陪伴孩子的多為母親,父親在城市賺錢養家。這些家庭有的是私營業主,有的是教師出身,也有個別家長是“海歸”。他們主張“在家上學”,還在網上成立了“在家上學聯盟”,已有南京、上海、北京、廣東、成都等20多個分站點。
針對上述7家家長的做法,武漢市教育局有關人士指出,按照《義務教育法》規定,凡年滿6周歲的兒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應當送其入學接受并完成義務教育。雖然孩子也在接受教育,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送其入學”接受教育。只是,《義務教育法》并未明確規定,若不按條款行事家長會受怎樣的處罰。該人士稱,家長的教育資質未經認定,孩子們又沒有學籍,教學質量也無從評判。
對此,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馮桂林則認為,這是一種值得倡導和肯定的現象。這些家長是在對人的全面發展進行一種探索。現行的“應試教育”模式,弊端就是忽略了健全人格的培育,造成了對孩子的童心和人格的壓抑。不過,馮桂林也認為,這種嘗試具有風險性,將來會在升學、社會評價和認可等方面存在系列問題。所以,如果其他家長沒有足夠的心理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知識,就不能盲目效仿。
當然,理想與現實之間難免存在鴻溝。陶行知曾說,兒童生活即兒童教育。在兒童教育作家三川玲看來,實際上“我們提供給兒童的,都是虛假的購買來的生活”——比如農作,是去大棚里面摘下成熟得剛剛好的草莓,然后用比市場更貴的價格去購買;不去真正的沙灘或泥地里玩耍,而是到商場圍起來的15平方里面花30元玩一小時干凈的沙子;不在田間地頭、小區樓下跟小伙伴游戲打鬧,卻在優雅漂亮的早教機構,跟一群突然認識的孩子“社交”。
幾年前,北大MBA的孟堯夫婦就因眷戀傳統文化,帶女兒西西隱居終南山多年,用誦讀經典的方式教育女兒。孟堯認為,居住在山林中更適于對西西的“格物”教育。西西每天早晨6點起床,6點半誦讀《論語》等經典,9點讀英語,午飯后背《詩經》,午休后抄寫英文和古漢語,晚上畫畫用毛筆白描勾勒花卉、古裝人物或等,聽媽媽講《說文解字》。
在孟堯的理解里,終南山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格物”條件。山谷里前后數里地不見人煙,屋子附近的榛子林下常傳來野豬刨土的聲音。離家不遠的山頭長滿了松樹,被西西爸爸修整成一個茶寮。每有訪客,西西樂于給他們當向導,奔跑在最前面,她還認識周圍所有野花以及各種不知名的昆蟲,記得每一個節氣。
《下鄉養兒》出人意料地熱銷,說明不少家長有讓孩子脫離現行教育框架的強烈欲望。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深泉學院,今年5月,重慶南開中學彭書涵被美國深泉學院錄取,引發了一陣“深泉熱”。加州沙漠地帶的深泉學院,是一所只有25個學生的“初等學院”,突然在一個十幾億人的國家走紅,耐人尋味。
深泉學院更像一個教育烏托邦。學生在這里學習、勞動和自治,學校牧場上有三百多頭牛,一群小伙子在這里除草,擠奶,修水管。其實中國有類似的學校,如安徽休寧的“德勝-魯班木工學校”。深泉那種山谷、土地,中國到處都有。現在也有家長,在做這方面嘗試。
如今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在周末或假期,攜一家老小上山下鄉、親近自然。但如果要讓一戶城市家庭長年攜家帶口居于鄉下,過那種與世隔絕的瓦爾登湖式生活,恐怕也沒有幾個家庭有這樣的勇氣。學者熊培云說:“我回想起自己曾經向天地開放的年輕生命,也為今日不曾帶自己的孩子久居鄉村而耿耿于懷。”
“下鄉養兒”仍顯另類
目前,置于當下常見的教育路數中,“下鄉養兒”仍顯另類。有人認為,在“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現行教育體系下,恐怕沒有多少家庭擁有這種“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資本與勇氣。在城市囊括了絕大部分優質教育資源的情境下,下鄉是否會讓孩子失去教育先機,是家長的普遍憂慮;其次,父母有較高的收入,足以負擔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開支也成為“下鄉養兒”必備的物質基礎。
教育資源的城鄉不均,成為多數家長對下鄉養兒的最大擔憂。“農村的教育方式比城里更加‘應試化,這對小孩的成長不利。”有家長擔心,鄉村教育資源不足,讓孩子在將來的社會競爭中,“在需要拼攢努力的時候,實力不足”。
其次,孩子在鄉村的人身安全,也讓家長無法放心。沒有護欄的水塘,散養的貓狗,監管不嚴格的商品,衛生習慣與孩子欠缺的自理能力,也是家長不能放手的原因。如此,孩子的鄉村體驗,就被加上諸多限制,如時間不能太長,必須有父母陪伴。
對比下鄉養兒和城市養兒,馮麗麗也認為各有利弊,“鄉下有大自然,有動物,有鄰居,但生活比較單調,有好多我們不太接受的思想。城里有書,有博物館,有比薩餅,但是孩子可能對四季,對自然缺乏感受。”因此,她建議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如果條件具備,盡量利用兩個地方的優點。”
馮麗麗的女兒天天,如今帶著這種美好的感受回到了城市。但這并不是故事的結局,“只要他們還活著,生活就還在繼續,各種問題層出不窮,一個又一個的麻煩等待他們去解決,他們在面對,在改變。”曾連載《下鄉養兒》的《讀庫》主編張立憲說。
下鄉生活會給孩子們留下難忘的記憶,而家長也意識到這種體驗的重要,然而,幾乎沒有幾個人愿意將孩子放在鄉下養。父母當然無法放棄現有可以支撐生活的一切,包括工作、社會關系。而鄉村,也不再是想象中的模樣,雖然天空清朗、樹木挺拔,但城市化所不可避免的問題已經在侵蝕著鄉村原有的樣貌——它們頭也不回地走在了消失的路上。重要的是,城市的教育資源依舊為鄉村不可匹敵。
盡管鄉村意味著新鮮的空氣、自由的空間、緩慢的節奏、放松的心情,孩子體驗鄉下生活,可以增長見識,懂得勞動的艱辛和勞動成果來之不易,但在面對是否愿意把孩子放在鄉下這個問題,多數家長認為,生活、工作、家庭都在城市,都市人距離鄉村已經越來越遙遠,下鄉養兒是一個不現實的話題。
有為數不少的家長表示,可以嘗試尋求兩種教育模式的融合,吸收這些父母對教育的某些理念和做法,在生活中實施。也有人認為,越來越多人放棄學校教育,這也提醒教育部門應當思考如何在當前國情下,構建更多元化、更符合孩子發展的教育模式。
或許,“下鄉養兒”頂多只是一種個性化嘗試,它值得被包容和理解,卻很難具備推廣價值。從另一層面來說,“下鄉育兒”給我們的啟示,也絕非是把教育探路導向“下鄉”這一條道那么簡單。學會因材施教,學會順應教育規律與尊重孩子天性,恐怕才是“下鄉養兒”真正給出的教育密碼。
或可預見,未來的孩子,也許將會與鄉村越走越遠了。從鄉土社會中走來當代中國,其實在靠血緣維系著農村和城市的人際關系。多數孩子的下鄉體驗,是源于父母探望長輩時順便為之,當父輩徹底消弭了這種關系,試想,孩子的鄉土生活還有多遠?
正如一個孩子所說:“因為家鄉不在鄉村,我沒有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