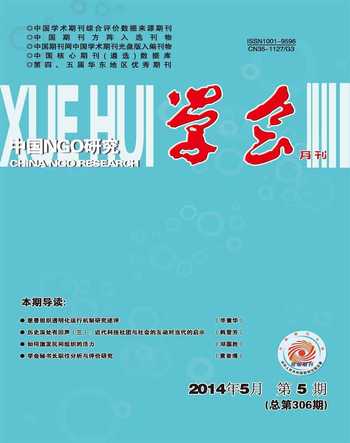政府進一步向社會放權核心在于培育社會組織
湯蘊懿
十八大后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路徑將從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向理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轉變,這一轉變的核心在于加快培育社會組織。社會管理不能都由政府承擔,完善社會管理,就需要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加大第三部門工作力度。然而,對于大量承擔具體公共事務的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受傳統的經濟型城市運行的長期影響,在地方公共事務中普遍形成了包攬一切的慣性思維和制度沿革。官辦的基層自治組織大多承擔著政府指派的行政管理任務,在民眾眼中他們代表政府,在政府眼中他們代表民眾,結果既喪失了政府的合法性和資源,也喪失了社會的合法性和資源。要實現社會部門自我服務和自我協調,特別需要強調有限政府的概念,厘清政府與社會以及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激活社會的自治功能,形成一個共建共享能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性的大社會。
一、培育社會組織是政府進一步向社會放權的基本方向
政府要向社會放權,就應當把社會自我管理、自我修復、自我建設的權利和能力交給社會,使社會組織成為社會有序管理、及時修復和自我完善的“先鋒”和“前衛”。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管理創新的總體特征是從傳統公共行政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轉變。面對著社會利益主體與利益訴求多元化的總體趨勢,尤其是進入微博時代,以管控為主的傳統行政模式存在實施主體單一、行政手段僵化的弊端凸顯,越來越無法適應當前社會結構原子化、個性化和流動化的特點,不僅難以實現社會穩定和諧,還容易導致更多的社會矛盾。通過市場化運作,引入各種非政府的組織,建立各種契約關系和合作伙伴機制,有效地拓展政府管理的形式與能力,明顯地提高公共服務的效能與效益,是當前創新政府管理的歷史方向和各國政府改革的基本趨勢,也是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城市管理的基本方向。
二、培育社會組織需要頂層設計
和西方先有社會、后有政府的發展時序不同,中國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城市化進程,使得中國社會組織在社會結構、發育程度、功能作用和運作模式等方面都明顯依附于政府。社會組織對于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空間需要政府更加主動地做出讓渡和制度設計。
(一)觀念更新
社會在快速發展,但我們當前的思維方式還相當落后。學者指出,當前社會管理創新不愿發展社會組織,這主要“是一些領導對于社會組織的認識存在誤區,不少人內心深處還是擔心社會組織做大、做強后會成為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對社會組織發展設置障礙。”其實,真正的穩定是用利益博弈消解社會矛盾,是多方博弈力量的平衡狀態,這才是最可靠的社會穩定。
(二)責權分明
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形成政社分開、權責分明、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理清政府和社會的權力邊界是政府放權的前提。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掌舵者”。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行政主體,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責無旁貸,對于公共服務的規劃、公共服務的資源保障、公共服務的統籌協調、公共服務的質量監督都負有直接責任;社會組織是公共服務的“劃槳者”,以其專業性、開放性和自治性提供各具特色的公共產品,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
(三)重點突出
在職責明確的基礎上,社會組織“前臺”功能要得到強化,重點發展領域應在“互益性”、“專業性”等一般公共服務領域;政府則可以退至“后臺”,加強對“純公共性”和“時效性”等特殊公共服務的提供,做好“守夜人”角色。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強調政府向社會放權,但政府必須對社會職能的擴張作出及時地回應。當前,上海地方政府急需加強對虛擬社會的服務與管理,加強對新興經濟組織的服務與管理,加強對社會風險和公共安全的管理,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
(四)分類推進
在對社會組織的改革培育進行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時,要充分考慮不同城市的原有的社會基礎、當前社會的結構和社會發展的需求。綜合考慮,上海應首先發展“互益”類社會組織;其次發展“公益性”社會組織,以滿足異質性移民城市的社會管理服務需求。領域選擇上,建議依次發展商會協會類、志愿服務類、文體娛樂類、公益慈善類和環境保護類等社會組織,把服務經濟、服務社區作為社會領域改革的重點。
三、培育社會組織需“摸著石頭過河”
在行政控制型的社會管理方式下,社會組織發育普遍面臨著登記門檻過高、運行過于行政化和扶植效果不強等突出矛盾,在社會穩定和諧中的作用遠未發揮出來。近期廣東、深圳、北京、云南等地的積極探索,為完善社會組織頂層設計提供了基層實踐經驗。
(一)立法先行
目前,針對社會建設領域中國家尚無法律、法規專門的規定,給各地培育管理社會組織帶來了制度性障礙。深圳市從立法入手,從2007年起,以5年為一個周期對社會組織發展進行了系統性立法。“十一五”期間先后推出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民政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推進民政事業綜合配套改革合作協議》和《關于進一步發展和規范我市社會組織的意見》〔2008〕;“十二五”期間,又推出了《深圳市社會組織發展規范實施方案》(2010~2012年)、《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創新促進條例(草案)》(2011)、《深圳市社區社會組織登記與備案管理暫行辦法》〔2010〕和《深圳市社會組織評估管理辦法(試行)》(2011)。當前,深圳社會組織的立法體系涵蓋了從“規劃——基本法——登記注冊——管理評估”各個環節,對深圳社會組織的培育發展建立了規范。
(二)組織完備
北京市的創新是在社會建設的總體布局下由黨委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和強力推進,形成了鮮明的特色: 一是組建黨政聯動、合署辦公的社會工作委員會(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作為專門的改革推進機構。與以民政部門牽頭協調的改革相比,這一機構設置更為有力,加強了改革措施的落實力度;二是建構“樞紐型”社會組織工作體系,以工青婦等人民團體和其他樞紐型社會組織為抓手,全方位地促進社會組織登記管理、能力建設和資源分配。該體系下,樞紐型社會組織替代行政部門承擔業務主管單位的職能,并作為公共服務購買平臺引導政府資源向社會組織流動,可視為結合人民團體功能轉變而進行的“以社管社”新路徑探索。
(三)核心突破
當前,困擾各地社會組織發展的首要困境是社會組織的雙重登記管理制度和限制性競爭原則。廣東省自2005 年底出臺的《廣東省行業協會條例》,率先取消了對行業協會的雙重審批制度限制和非競爭性設置制度限制,將行業協會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取消了業務指導單位對行業協會成立前置審批的條款設置,行業協會可直接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籌備成立。2009 年底,這一創新被推進到異地商會、公益性社會組織和經濟類社會組織。新疆、安徽等地把異地商會登記權限下放到地市級和縣級,降低異地商會的登記門檻。北京取消了工商經濟、公益慈善、社會福利、社會服務四類社會組織業務主管單位,嘗試社會組織統一直接登記。二是率先突破行業協會、商會“一業一會”限制。
深圳市實行由寬到嚴的資格審查和登記注冊制度,設定備案、法人登記、公益認定的三級準入機制。同時根據實際情況,重點扶持發展社區社會組織,對社區社會組織實行登記和備案雙軌制,授權街道辦事處對社區社會組織備案管理,并給予資金扶持。在放松前置審批后進一步加強后置監管力度,通過建立社會組織披露平臺,對社會組織內部和社會的信息披露作了詳細規定,對社會組織的退出機制作了重點安排。
(四)配套保障
第一,完善政府購買服務機制,通過公共資金的引導促進社會組織體系的優化和能力的提升;第二,認真落實稅收優惠政策、設立社會組織發展基金、加強社會組織人才建設等扶持舉措,如深圳市推動“孔雀計劃”和“人才安居工程”等重大人才政策和重點人才工程惠及社會組織人才;第三,政府不與民間組織爭利。深圳市規定,凡是能由市場和社會組織提供的,政府不再設立新的事業單位,而交由市場和社會組織承擔,逐步向有承接能力、公信力高的社會組織轉移職能。第四,實行跨界合作。如杭州市提出“社會復合主體”概念,探索跨域合作的實現機制,培育黨政、學界、行業、媒體四位聯動的新型社會創業組織。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