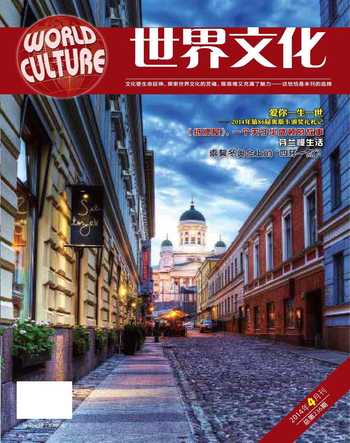今天的俄羅斯文學
張楠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月7日在俄羅斯索契冬奧會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說:“我年輕時多次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小說,奧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索契完成了這部著作。”他還一口氣說了11個俄羅斯作家的名字:“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肖洛霍夫,他們書中許多精彩章節和情節我都記得很清楚。”……
這些作家或許有人不熟悉,但他們的作品在中國影響巨大。魯迅曾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稱“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他還把俄國文學的譯介工作比喻為“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俄羅斯文學在“五四”之后進入中國,它以其直面現實的勇氣、對社會的深沉擔當及強大的人文情懷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中國讀者。但俄羅斯文學真正成為中國人和中國文學的“導師和朋友”,恐怕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很少有人沒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等“蘇維埃經典”。視文學為“生活教科書”、視作家為“靈魂工程師”的蘇聯文學,與當時弘揚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社會大背景相呼應,極大地影響了中國青年的個性塑造和精神成長,那一代人身上后來所謂的“蘇聯情結”,在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俄蘇文學的長期熏陶。
后來,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俄羅斯文學作品的出版量也在減少,有專家總結這其中的原因大約有這樣幾點:首先,在人們普遍贊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當下,反而出現了英語和美英文化的話語霸權,相比之下,俄羅斯文學和其它非英語文學一樣,都變成了“小語種文學”,被程度不等地邊緣化了。其次,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的國力有所下降,國際影響力與蘇聯時期不可同日而語,雖然一個國家的文學水平與國力之間并無什么直接的聯系,但其國際聲望的大小無疑還是會影響到其文學和文化的輻射力。最后,被許多評論家稱之為“后蘇聯文學”(蘇聯解體之后)的俄羅斯文學,自身也出現了空前多元的局面,令人有眼花繚亂之感,這使得我國在對其的整體把握和系統譯介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難。
那么,俄羅斯文學的現狀是怎樣的呢?本期特別刊載“格拉斯新俄羅斯文學”(Glas New Russian Writing)叢書主編娜塔莎·佩洛娃(Natasha Perova)關于“俄國文學現狀”的文章,為讀者提供一扇了解當下俄羅斯文學現狀的窗口。在本文中,娜塔莎·佩洛娃表明了對于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的恐懼,解釋了當人們欲了解當今俄羅斯文壇現狀時,類型文學(genre literature)是跨不過去的門檻。
俄羅斯人民有著極為崇拜本國作家的傳統。這不僅僅是指我們這些受“偉大的俄國文學”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中年人,許多年輕人也有相同的感受。現在的文學和嚴肅藝術日益西化,作家寫作也是娛樂大眾而非進行教育。像其它地方一樣,今天大多數俄羅斯人都喜歡熱鬧的表演、刺激的游戲以及消遣性的小說,嚴肅藝術不得不裹上艷俗包裝。互聯網上各式各樣(包括閱讀在內)的娛樂活動也使人們沉溺其中,比如網絡雜志只錄用短小、娛樂感強的小說,而將那些帶有悲情和沉重色彩的故事拒之門外,人們的閱讀耐心下降、關注范圍萎縮。出版商也竭力讓作家適應大眾的口味進行創作,畢竟讀者是他們的錢包……以上種種自然挫傷了作家們的自尊心及對自我價值的認同感。
格拉斯出版公司在過去幾年主要出版三十歲以下、曾獲得過“新人獎”(Debut Prize)作家的作品,因此對這代作家有所了解。他們對成為斯大林所說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感興趣,更不愿像19世紀的知識分子那樣身系國家命運。年輕的作家們頭腦清醒且相當實際,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動蕩、經濟混亂充斥在他們成長的歲月,因此他們視亂世如平常。當我們這些中年人對現實表現出震驚、沮喪的時候,他們卻顯得冷靜與超然,從不指望這個世界能夠圓滿。但是這批作家對細節相當敏感,具有生動地描繪真實俄羅斯的能力,他們眼神犀利,筆觸精致,感情漠然。
過去,蘇聯作家的日子不好過。審查制度以及不同政見經常會這樣那樣地影響他們的創作——不是親蘇就是反蘇,如果 “為了藝術而藝術”,毫無疑問必然是反蘇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審查制度取消以后,之前被禁的書籍潮水般涌入書店,此時新創作出的作品被冠以“后蘇聯”(post-Soviet)”的,而后就是“后后蘇聯”(post-post-Soviet)的,但它們仍舊不能從蘇聯的歷史里擺脫出來。只有今天這些二三十歲的作者拿起筆講述現在的生活,“蘇聯主題”才變成了遙遠的過去,對他們來說,“蘇聯”純粹是一段歷史,就像彼得大帝或伊凡雷帝。
當局最終也意識到知識分子其實沒什么危害,于是便采取放任的態度。今天的作家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發泄就怎么發泄,而政府也不介意作品中出現的不同觀點,因為這些作品印數有限。作家渴望自由,而當其真正擁有自由的時候,他們卻發現沒人在乎他們那些大膽的想法。政府偶爾仍會找作家們的麻煩,但聰明的作家干脆把這些麻煩當作宣傳、炒作自己的機會。
20世紀90年代,我們目睹了俄羅斯文學與傳統道德的背離,魔幻、科幻、怪誕以及虛無主義等題材作品變成了主流。當然還有一批嚴肅作家并不追逐時尚,魔幻、怪誕、偵探小說在他們眼里只是文學形式,他們只想利用這些形式來表達其偉大的思想,描繪其想象中宏偉的畫面。這足以讓人想到,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其實就是魔幻類作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其實也是一部偵探小說。
當代文壇的現狀極為多樣。俄羅斯國外的讀者經常說,俄羅斯過去二十年間大事不斷,但卻沒有任何一部能夠表現這一時期重大事件的“有分量的小說”問世。其實讀者應該明白,文學與新聞不同,它做不到及時記事,作家需要對一段歷史進行消化,同時分析社會的種種變化。這就是為什么在社會動蕩最激烈的時候,作家們仍然試圖要理解他們所經歷的過去。當代小說由于種種原因很少被翻譯出去,但它們確實存在。有許多重要作品面世,其中有涉及改革的、幫派爭斗的、狂熱追逐資本主義的、小人物討生活的……比如奧爾嘉·斯拉夫尼科娃的小說《2017》,它就是過去二十年里俄羅斯生活的縮影。她的最新小說《腦殘》(Light Head)似乎更具時代氣息(內容涉及情報機關的恢復、恐怖主義、大批做小生意的經理人以及一直以來對小人物冷漠無情的國家機器對人際關系的破壞等)。
市場經濟時代,低俗小說已經戰勝了純文學,輕輕松松地將純文學推到了邊緣地帶。如果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當代,要把他們的小說推薦給商業出版社出版的話,多半會很困難,他們可能會以各種理由被拒,例如作品太長、太密、太繁冗、情節發展緩慢、過于嚴肅等等。許多純文學作家正在朝中端市場靠攏,并有大量作品問世。而在20世紀90年代的早期,他們會因此感到無地自容而使用假名。但現在,知識分子精英擁抱流行文化成為時尚。維克托·佩列溫(Victor Pelevin)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最早開始利用不同體裁形式進行創作的作家之一,且獲得了廣泛關注。然而他又是為數不多從不犧牲任何文學價值的作家之一,因而他的作品受到了不同層次讀者的青睞,每一個人都能根據自己的水平來感受文本。新生代作家中很少有能模仿他的例子來達到一種平衡——寫作質量與大眾市場之間的平衡。鮑里斯·阿庫寧是另外一位特點明顯的作家。作為知識分子,他文化修養高且做出了一個明智的決定——為大眾市場而寫作(盡管使用筆名),因此大獲成功。他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也是一名優秀的心理學家,他知道如何打動那些簡單的頭腦。他的經驗被許多聰明的年輕作家所效仿,并且有不同的成功案例。
由于純文學不得不與大眾文化共存,因此年輕的作家不斷地試圖跨越這其間的障礙,不斷地運用各種流行文學形式,憑借著各種自我推銷的手段“出彩”,其中“爆丑聞”成了抓住公眾眼球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俄羅斯的薩德侯爵弗拉基米爾·索羅金被控傳播色情,他的書甚至被扔到莫斯科劇院外的硬紙馬桶里,而這一丑聞恰恰提升了索羅金的人氣,以至于他的出版商們竭盡全力地來散播消息。而純文學創作的組織過程也像娛樂業一樣,有炫彩的表演、有比賽、有收視率以及測驗等等,嚴肅作家也上電視節目,甚或為商品進行廣告代言。
當下,西方社會對俄羅斯年輕作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主要涉及創作形式與方法,而非更深層次的東西。由于作家們關注的是俄羅斯,作品選材也本土化,因此他們的作品在精神與風格上都保留著獨特的俄羅斯味道。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俄羅斯19世紀古典文學就是以法國古典小說為模板的,但卻絲毫無損其本身的原創性與重要性。
蘇聯時期,女性作家的名字以及性別問題等幾乎沒有出現在俄羅斯文學當中,但作為更具實踐型的生物,女性則在以大眾市場為導向的出版過程中表現得特別積極。現今,無論是在低俗小說還是純文學小說領域都涌現出了大量的成功女性,這也是當代文壇的一大特點。
國家對文化的扶持連同意識形態審查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結束,這給了作家自由表達的權利,但公眾的興趣已經不由分說地轉向了大眾文化,嚴肅文學失去了往日的威望。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產生出了大量、多樣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這種后審查時期與20世紀20年代有著頗多相似之處——國家又一次身處激烈變革的陣痛之中,之前的偶像遭到顛覆,既有的價值觀受到質疑,全新的觀念此起彼伏,各種創作理念及怪誕的理論、運動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后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各路分支(魔幻現實主義、齷齪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并駕齊驅。作家為了接近讀者,在公眾缺乏興趣的新文學中勉強謀生,為此紛紛成立自己的出版社、書店以及文學俱樂部。純文學小說以微型版本出版并且印數稀少,大眾正忙于惡補之前的那些禁書……當下,雖然文壇與藝壇的活躍度是前所未有的,似乎一片盛況,但暗波涌動的卻是集體失去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