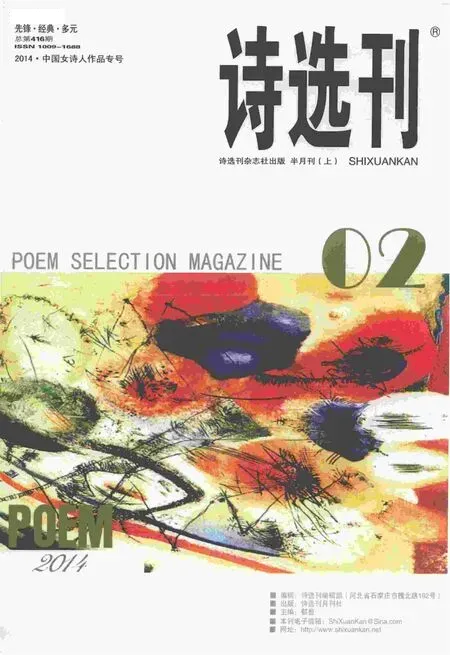阿略的詩
阿略,畢業于中南政法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喜歡閱讀,偶爾在報刊發表很快被遺忘的文字。
透過冰冷的玻璃
透過
冰冷的玻璃
你發的灰白、眼角的皺紋
在我右手指尖
流動。
我說,這風陰冷。
你笑了。
笑得溫暖。
我不再用把睡衣裹緊
比如,愛或者恨
他說,你要盡量暴露。
我投過去的眼神讓他動了隱惻之心
繼而說出一個好聽的名字寬慰我——
你這是艷陽癥。
跨出門檻的一瞬,我小小地樂了一下
就算指頭有點化膿,能攤上這樣好聽的名字
也不算太冤。
我開始原諒和淡忘刺破指頭的魚翅
為什么我能明白無誤地
領會醫生交待的注意事項
卻偏偏挑出這幾個字,改了姓名?
后來弄清楚艷陽癥其實是厭氧癥。
我們時常為獲得某種寬慰或別的什么
癔造花環與枷鎖。
比如,愛或者恨。
遠離
遠離聒噪。遠離浮華。
遠離悲戚。遠離愉悅。
遠離憂愁。遠離歡樂。
遠離衰敗。遠離蓬勃。
遠離冷漠。遠離纏綿。
遠離中傷。遠離頌揚。
要近,就進到一個心房。
靈魂
她們已失散多年。
這是一次有預謀的背離。
曠野。荒漠。叢林。潮水。
噴列。放浪。恣意。低吟。
遠離塵囂。與猛獸同流。
是什么一次一次試圖將她掠走。
憐
所以,可憐的人兒
你有權保留你的嚷嚷
保留一切你可以猜想得到的猜想
而我將繼續以我的沉默
以輕蔑的若無其事
地球再大,我站立的地方
你終究沒法立足
——除非把我干掉
即使站在了和我同樣的位置
你也未必能想到我所想到的
渴望被吞噬的歡暢
誰又不是呢
游走的孤魂。
夜深人靜,與自己對話
幽暗的天空近在咫尺并步步逼緊。
我已無法愛上,無法再愛上某個具體,
魂魄游離于荒郊野嶺。
一想到它將被野獸啃噬,
就會讓我有著某種難以形容的快暢。
胡扯歌
呼嘯的風,像萬馬奔騰。
八面撕扯樹干。搖撼。
樹葉兒一卷再卷,曲成
夢回子宮的模樣。
太陽醉得有點癲狂,
像一個獄門前的男人吻著
他的女人。
我端坐家中,
聽樹搖,看風聲,和萬物親吻。
“他們都藏在了情人的懷抱”
月亮的聲音掩飾不住挑逗,
“為什么會萬籟俱寂”?
他們死了。他們愛得死去。
她,蹺起二郎腿活脫脫個潑婦樣。
仰著脖子,乜斜的眼
看夜幕下漸漸安睡的屋子。
我恨一頭飄逸的黑發
我愛一碗米飯。
也愛著碗里僅剩的殘羹。
我愛春天枝頭吐露的新芽,
也愛秋天凋零的落葉。
我愛小鳥的歡歌,也愛著它的哀鳴。
我愛清澈,也愛著渾濁。
我愛一切詭異雜亂,以及所有的隱隱灼灼。
就像罪孽愛著邪惡。
可我恨,一頭飄逸的黑發。
失眠的泰迪
夜里三點四十,聽見淡淡在屋里走動。
它走一走停一停,走一走又停一停
偶爾還會曲起一只前腿,左耳微微一動
好像聽見了什么。窗外一直很靜。
自打兩點半鐘,一陣細微的風經過
再沒有任何聲音。淡淡又在走動
它走一走又停一停。
窗外一直很靜。
這只來自法國的泰迪犬
正在遭遇失眠。
無所謂
無所謂信不信
那之后
原本冰冷的石頭
變得柔美溫馨
晨曦抑或晚霞
以及霜雪般的月光
也總能幻化出些影子
同一片天空下
蔚藍傍著雨密布
一半淹沒
一半干涸
來生來世
之后,還是有過念想。
一點點憧憬,一點點希望。
已經晚了。
那塊空地,安靜地荒蕪。
稻草人賣力地伸展,
鳥兒,不曾來過。
滔滔
紅酒。微醺。
這時的心境最適合把話兒
從心窩掏出。
假如對面恰好有個人坐下
是不是該
顯擺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