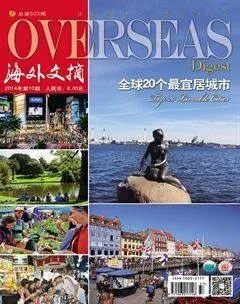德國“包容學校”
在“包容學校”中,殘疾學生和正常學生坐在同一間教室里共同學習——這是德國自引入義務教育制度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徹底改變了所有學生、家長和教師的生活。
2006年,聯合國簽署了殘疾人權益公約,第24條確立了建立起一個“包容并蓄“的教育體系的義務,即殘疾孩子應該去普通學校上學。時任德國聯邦殘疾人利益專員、殘疾孩子的母親艾佛斯-邁耶爾飛至紐約,為德國簽署了這一公約。“那時還沒有人意識到,”艾佛斯-邁耶爾說,“我帶回家的是怎樣一枚重型炸彈。”2008年12月,德國議會通過了該公約,從而帶來了德國教育制度的一次偉大變革。
何為“包容”?
很多政治家、教師和家長認為,“包容”主要是指輪椅坡道、殘疾人廁所。這種想法是多么片面啊!“包容”意味著教師成為一門全新的職業,德國66萬名教師都應該學習殘疾兒童教育的基礎知識。專業教師和殘疾兒童教師必須一起備課,一起上課。殘疾孩子不能只是在普通學校瞎坐著陪讀,而是真的能發展其個人能力。
此外,“包容”更是一種態度。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同的,多樣性是生活常態。到目前為止,德國教育體制要求學生必須適應學校,而在一個包容性的體系中,學校必須適應學生。這就是根本上的變革。
殘疾并非身體缺陷,而是社會標簽
幾十年來,殘疾人學校幾乎一直被公眾所忽視。2008年,德國教育界泰斗克拉斯·克萊姆第一次對此進行研究,2014年5月他得出結論:所有殘疾人學校學生中有四分之三沒有小學畢業,求職更是毫無機會。殘疾學生融入普通學校不只是因為聯合國公約的法律強制性,殘疾人學校的失敗本身就為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此外,德國殘疾人學校常常是私立的,很多學校同時還經營成年殘疾人的設施,從沒有畢業的殘疾學生那里盈利。從殘疾人學校進入殘疾人車間,從生活護理需求到護養院需求——作為殘疾人,你一生都是目標消費者。而這種消費可能還會延續到身后——教堂機構常常還設有專門的殘疾人墓地。
如果說起殘疾兒童,你腦海中浮現的只有坐在輪椅中的“令人擔憂的孩子”,那你就錯了。在德國,只有約12%的殘疾孩子是身體上的殘疾,以前的人們稱為“智障”的孩子也只占到16%,人數最多的是“有學習領域的特殊教育支持需求”的孩子,占到了40%。將“學習障礙”作為官方的殘疾分類評級是德國專屬,全世界獨一無二。也就是說,大部分被認定為“殘疾兒童”的孩子在其他國家并不會上殘疾人學校,因為他們并不被認為是“殘疾人”。
而這種最常見的殘疾——學習障礙、情緒或語言發展障礙,大部分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原因造成的,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合理的教育。來自移民家庭的孩子常常成為“殘疾孩子”,因此,“殘疾”在德國常常根本就不是醫學診斷,而是一種社會標簽。
“包容”帶來的新可能
“包容”學校引發的最大討論是:讓有天賦的孩子和有學習障礙的孩子在一個班里學習,究竟應該如何教學?
“早上好,舒爾特老師、海特曼老師和漢斯麥爾老師。”在古特斯洛的雅努什·科扎克學校,6A班的學生們向3位老師問好。舒爾特是經濟學教師,海特曼是殘疾兒童教師,包容助手漢斯麥爾幫助一位坐在輪椅中的女孩。6A班有3個有學習障礙的女孩、一個有智力缺陷的男孩,以及其他正常孩子。
瑪麗在哭。學校把她歸為“有學習障礙”一類。瑪麗早上很難開始學習,坐在她旁邊的同學索倫知道這一點。他輕輕地撫摸她的背,給了海特曼一個手勢。而后者在瑪麗身邊蹲下來,把她抱入懷中。瑪麗很快就恢復了平靜,課堂繼續進行。五年級時,6A班的孩子開始和完全不同的同學一起學習,有些孩子最初提出抗議,因為任務簡單得多的同學受到了老師同樣的表揚。“但很快所有孩子都覺得很自然很正常了。”海特曼說。
這堂課的主題是:該如何設計一家超市?學生們講述他們的想法,然后每個學生分得一個任務。舒爾特和海特曼共同備課,為不同學習水平的學生設計了4種方案。成績好的學生得到的任務是最難的。10分鐘后,舒爾特和海特曼拍了拍巴掌,這是討論結束的信號,所有人都完成了任務。速度快的學生完成了復雜的任務,可以用盡全力,不需要無聊地等待。速度較慢的學生也可以努力解決他們力所能及的難題。
麗莎笑得很開心。如同瑪麗一樣,她也被蓋上了“學習能力障礙”的印章。但她好勝心很強,好成績讓她開心,因此在分發任務時她總是要求做學校認為對她太難的任務。自從轉出殘疾人學校之后,麗莎取得了巨大進步。海特曼相信,麗莎能夠小學畢業,而在殘疾人學校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今年1月,漢堡的埃里希·凱斯特納學校獲得了包容學校評比中的雅各布·穆特獎。這里總是由一位老師和一位殘疾兒童教師共同授課,有時還會配備一個社會教育專家。學校不是為一個年級制定一個教學計劃,而是為每個孩子制定一個。教師要下午6點之后才能回家,并且都要不斷接受繼續教育。
結果是可喜的:比起漢堡殘疾人學校,獲得了小學畢業證的殘疾孩子數量翻了4倍。同時,參加高中畢業考試的學生數量和畢業考試成績都高于平均水平。在凱斯特納學校,智障兒童普遍都學習讀寫。盡管主流觀點認為這絕不可能成功,但今年夏天,又有一個被認為有學習障礙的孩子通過了高中畢業考試,取得了畢業證。
關門的殘疾人學校
到2016年,奧拉夫·阿奇爾斯領導了多年的這家高斯殘疾人學校就要關門了。3年來,這所學校不再招收新生,學生們現在都去普通學校上學了。“最初我也對包容學校抱有遲疑,”阿奇爾斯說,“但現在我承認,對殘疾孩子來說,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課確實是個優勢。”
高斯學校是一所傳統的學校,很多學生一家三代都曾在這里上學。他們的祖父母上學時,這所學校還被稱為“輔助學校”,父母上學時變為“特殊學校”,孩子們上學時就變成“殘疾人學校”了。“學習障礙”沒有醫學上的原因,但它仍是可遺傳的,正如貧窮一樣。這所學校的孩子來自底層,殘疾人學校雖然不以教育受歧視的孩子為己任,卻履行了這樣的功能:它們保護底層孩子不受上流社會孩子的欺負。
今年暑假,高斯學校的副校長佩特拉·克洛普實開始在700米開外的一所普通學校上班。“我一直都為我們的殘疾人學校感到自豪,但是在普通學校,我們教育的孩子能夠達到全新的水平。”
尤其有用的是一條古老的教育理念,即孩子從其他孩子處學習。以前在殘疾人學校,紀律是中心主題,老師得時刻注意保持課堂安靜,一個小時可能就只有幾分鐘能夠集中精力學習,而在包容課堂,在其他孩子的影響下,殘疾孩子真正用來學習的時間大大增多。
位于德國最北部的石荷州是最早關閉殘疾人學校的聯邦州之一。“我們是沒有學生的殘疾人學校。”石勒蘇益格-克洛普殘疾人中心校長拉爾斯·克拉克爾特說。去年夏天,最后一批學生離開了學校,而該中心的一共44位教師繼續照顧石勒蘇益格區的約300名殘疾孩子,不過地點不是在殘疾人學校,而是分散在26所不同的普通學校。
包容課堂的問題
盡管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包容學校仍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里的同事工作負擔很重。”漢堡納爾遜·曼德拉學校校長波多·基瑟說。這也造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一些老師無法適應這種轉變,感覺自己受騙了。他們做出職業選擇時,并不知道自己還必須教殘疾孩子。資深教師突然要聽新教師的意見,殘疾兒童教師工資水平更高,這也使得他們在辦公室中并不很受待見。目前仍需采取有效措施,讓所有老師都轉變觀念,融入這種新體系。
曼德拉學校的學生90%都有移民背景。“問題并不在于孩子們在家里講的是土耳其語,而是家人之間根本沒有交流。”校長基瑟說。這些孩子五年級(中學一年級)進入曼德拉學校時,大部分已經留過兩次級了,他們并不是身體殘疾的孩子。
自從包容學校在漢堡興起以來,更多有著特殊教育支持需求的學生加入其中,每個班都有三四個。但是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課上有殘疾兒童教師輔助,大部分時候教師都是獨自應付殘疾孩子的問題。“一些政治家認為,一堂課雇傭兩個老師,總有一個是在尸位素餐。”基瑟說。
殘疾兒童教師缺席的包容課堂會是怎樣的?“親身體驗一次課你就知道了。”基瑟說。一旦老師為不同的孩子分配不同的任務,小小的教室中很快就會爆發混亂,然后孤軍作戰的老師就會讓最聽話的學生去走廊上靠窗的長凳處學習,至于差生就沒人管了。
凱斯特納學校校長皮特·卡策爾是包容先鋒。他喜歡說起學校創立初期的困難,那時一部分同事和家長反對共同學習。“除了態度和教育理念,包容學校首先是資源問題。”校長說。幾十年來,德國教育支出低于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水平,如今資金不足的教育體系還要解決代際難題“包容”。此外,還需要成千上萬殘疾兒童教師,可惜就算有錢也雇傭不到他們,因為大學教育出的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很少。學校圖書館幾乎沒有任何關于包容教學的資料。德國推行包容學校時遵循的原則是:先引進,再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這就像一位市長為了環保先封鎖市中心,不讓汽車駛入,再問城市需要多少公交車。
“這樣的話,包容會成為災難。”德國中小學校長聯合會主席古德倫·沃爾特斯-福格勒警告。校長們感覺他們被政治家拋棄了。盡管有不少試點,但是聯邦各部并沒有為復雜的轉型制定出最終的解決方案,為學校領導班子提供指導方向,這樣所有的學校都必須重復同樣的錯誤。
由此可見,為殘疾孩子提供一個公平的受教育環境勢在必行,但由于經驗不足,德國包容學校的發展仍然任重道遠,需要社會各界持續努力。
[譯自德國《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