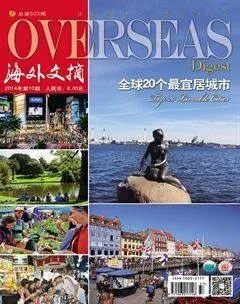陰影中的孩子

醫生、親戚、父母,所有人的關心都屬于家中患病的孩子,而他們健康的兄弟姐妹則一天天隱瞞住自己的需求和煩惱,比同齡人更加成熟,甚至為自己沒有生病感到罪過。這些孩子被稱為“陰影孩子”。
陰影孩子比同齡人更加懂事、成熟。他們會隱瞞自己的需求,敏感地了解到父母的期待,并努力迎合。由于缺乏安全感,他們常常會出現睡眠或進食障礙。很多孩子都會嫉妒家里的小病人,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有時他們會對患病的兄弟姐妹甚至父母感到憤怒。
2010年夏,天氣悶熱。馬克斯站在客廳窗戶前,雙手和鼻子抵著玻璃,手掌和鼻尖留下印子。他多想出去和小伙伴們一起玩耍。他的肋骨處掛著一個引流管,褲腰處是一個導尿管。當時6歲的馬克斯已經患癌癥5年了。他做了干細胞移植手術,剛從醫院回家,免疫力極低,不能出門。
回到家中,虛弱的他一進家門就倒在地毯上,甚至無力和他的姐姐、弟弟問好。姐姐克里斯提娜站在門廳不知所措,弟弟尤斯圖斯小心翼翼地上前試圖撫摸他。母親大聲喝止:不行,松手!她的聲音近乎歇斯底里,畢竟任何一個疏忽都可能導致馬克斯不得不重回醫院。
4年過去了,如今已經10歲的馬克斯在家待的時間很短,但是他的姐姐和弟弟早已對如何照顧他了然于心。為了避免致命的感染,房間要盡可能保持無菌狀態。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手帕,不時用消毒液擦拭門把手,盆栽被放進車庫中無人問津直至枯萎。如果馬克斯的朋友來看他,克里斯提娜會在門口熟練地將一個防毒面具塞到來訪的小朋友手里,以保護馬克斯不受外界細菌的侵害。
陰影孩子
這就是生活在柏林市郊的克里斯提娜和尤斯圖斯的日常生活,也是在全德國有重病孩子的2.2萬個家庭中上演的一幕幕場景。醫生、親戚、父母,所有人的關心都屬于患病的孩子,有誰想過那些健康的兄弟姐妹們的需求?他們一天天隱瞞住自己的需求和煩惱,比同齡人更加成熟,甚至為自己沒有生病感到罪過。這些孩子被稱為“陰影孩子”。
大部分“陰影孩子”的父母都不想談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很高興已經戰勝了這個問題,或是可能還沒有勇氣去思考疾病對他們健康的孩子意味著什么。
貝爾格夫婦不想自己的真名和住址出現在故事中,但是他們愿意說說他們的陰影孩子。瑪麗安娜·貝爾格坐在客廳沙發上,她的旁邊坐著女兒克里斯提娜,后者體態柔弱,臉色蒼白,比實際年齡顯得更小。克里斯提娜一直在試圖使用成人世界的詞語:“就是這樣,你必須把自己的想法隱藏起來,失去自我感。”
母親瑪麗安娜說,最開始克里斯提娜才是那個讓人擔心的孩子。她3歲時脊椎出現了一個腫瘤,但是和同時被確診為癌癥的1歲的馬克斯完全不同,手術后克里斯提娜很快就恢復了健康。醫生確診馬克斯為“神經母細胞瘤”,這是一種惡性生長的腫瘤,是兒童當中最頻發的癌癥種類之一。
自那以后,馬克斯就開始了一段與病魔作斗爭的長長征途,總是在生死之間徘徊,從一家病院進入另外一家,從格賴夫斯瓦爾德到圖賓根,從圖林根到柏林夏里特醫院。可治療均宣告無效,腫瘤擴散到腎臟、肝臟和腸道中,轉移到骨頭里。
最初瑪麗安娜還每周工作兩天,其余時間就在醫院守著。晚上由丈夫代替她,這樣她可以回家給剛出世不久的小尤斯圖斯喂奶。“除了馬克斯,我腦袋中已經沒有留給其他孩子的地方,”她說,“完全沒有。”
很快繼續工作就已變得不可能。瑪麗安娜有時一天要做六七次飯。馬克斯想吃烤豬肉,瑪麗安娜趕緊為他做。然而在開吃之前,他突然更想吃鴨肉丸子,或是通心粉、荷包蛋、紅燒肉。她又重新為他做。“他想吃東西,這已經讓我們喜極而泣了。”瑪麗安娜說。
我也可憐!
2009年,克里斯提娜已經變得沉默寡言了,她小時候非常愛說話。不知何時,小尤斯圖斯也意識到了,他不能給父母帶來任何麻煩。“他很長時間都不發一言,”瑪麗安娜說,“是個非常好帶的乖孩子。”
克里斯提娜很快就開始討厭餐桌上總是出現的馬克斯喜歡的肉食。她不得不放棄騎馬,因為根本沒人帶她去。出于同樣的原因,她也放棄了跳芭蕾。她只能和弟弟尤斯圖斯一起玩耍。“我很悲傷,”她說,“但是只能接受這個現實。”在朋友們一起吃冰淇淋或游泳去時,克里斯提娜坐在馬克斯的病床旁。慢慢的,女孩們就不再問克里斯蒂娜要不要一起去了,因為她們知道,她永遠都沒有時間。
“當我因為要去看馬克斯而不能去上學時,”她說,“常常有人會嘲笑或是嫉妒我。”當老師讓克里斯提娜回答一道計算題,而她不知道答案,因為她根本就心不在焉時,其他孩子也會哄堂大笑。老師把克里斯提娜的父親叫到學校,因為她在課上的表現很糟糕。而父親讓她站在全班面前講明實情,這讓克里斯提娜覺得很丟臉。但是回到家中,她什么也沒有說,因為她知道,家里的問題已經夠多了。
一天,課堂上討論的主題是那些沒有父母的可憐孩子。克里斯提娜回家后說:”媽媽,我也是個可憐的孩子,我也只有半邊家庭。“這句話深深震驚了她的父母。他們把克里斯提娜從學校接回家,找了所新學校,現在她上學的路程根據乘車路線的不同需要一到兩個小時。他們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心理醫生佩特爾森女士每周為克里斯提娜治療一次,和她一起玩耍,去動物園,烘烤小餅干。2011年,醫院的一位社工向他們介紹了一個專門為“陰影孩子”成立的組織——兄弟姐妹小組。
小組見面會
一個霧蒙蒙的春日,8個孩子在深紅色的地毯上圍坐成一圈。尼爾斯一手拿著絨毛狼玩具,另一手拿著一張紙。這是他給姐姐寫的一封信,她5個月前因癌癥離開了人世。他說:“我想讓你們聽聽,我給她寫了什么。”其他孩子都安靜地傾聽著。“我希望,你在天上能夠清楚地看到我在做什么……我想對你說的太多了……沒有你的日子很無趣!”然后他們一起唱歌,想象尼爾斯的姐姐也能看到,也許在天上,在金色云間另一個有著秋千和噴泉的城市。
50歲的治療師戈爾布格·貝爾胡思也坐在圓圈中。她說:“孩子們討論死亡時候的勇敢和坦誠令人驚訝,他們比我們做得更好。”貝爾胡思目光和善,她自己也是個陰影孩子,和一個身心殘疾的哥哥一起長大。她幫助建起了這個柏林慈善組織——兄弟姐妹小組。在這里,重病孩子的健康兄弟姐妹們聚在一起。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們正在研究,陰影孩子的家庭狀況會對他們的身心健康帶來怎樣的影響。他們發現的,也正是貝爾胡思所經歷到的:有些人會變得固執、愛哭,卻比他們的同齡孩子更加懂事、成熟。他們會隱瞞自己的需求,敏感地了解到父母的期待,并努力迎合。他們常常不會表露自己的情感,內心沖突卻非常強烈,這表現在他們的笑和哭之間轉換得很快。由于缺乏安全感,他們常常會出現睡眠或進食障礙。很多人都會嫉妒家里的小病人,感覺自己沒有價值。有時他們會對患病的兄弟姐妹甚至父母感到憤怒。貝爾胡思說:“我的哥哥病得很嚴重時,我在心里許愿:‘可以結束了,他可以死了!’我那時14歲,已經知道不該這么想了,心里非常矛盾不安。”
目前世界上像這樣的互助小組還很少,但是隨著對陰影孩子關注度的提升,這樣的組織會慢慢增多。在這里,陰影孩子們終于松了一口氣:沒有人問愚蠢的問題了!可能傳染嗎?你也會得病嗎?他死了怎么辦?“其他孩子能夠理解我的一切,我太高興了。”克里斯提娜說。她非常喜歡小組活動,甚至曾推掉同學的生日邀請來參加見面會。
知道生命意味著什么
現在,克里斯提娜可以更多地和朋友們一起,也可以去騎馬或是學芭蕾了。因為一年多以來,她弟弟的病癥已經消失了。
一方面,弟弟的癌癥讓她變得憂心忡忡,她總是害怕他的病會復發,總是在問他是不是真的好了。克里斯提娜說,癌癥也教會了她很多,比如如何成為一個大人。“因為他,我知道了生命和健康意味著什么,有多么重要。很多人還從來沒有進過醫院!”
她說,如果馬克斯沒有生病,她對色彩也不會有這樣的感覺。馬克斯長年累月不在家,她就為他畫畫,也為自己。客廳的墻上掛著一幅兩米寬的草地,上面開著紅色的罌粟花——這是克里斯提娜的作品。“畫畫可以消除沮喪,將壓抑的情緒發泄在圖畫中。”她說。
門鈴響起,兩個少年放學回家了。馬克斯第一個沖到了克里斯提娜的房間,尤斯圖斯緊隨其后。由于化療,馬克斯很矮小,和比他小3歲的弟弟差不多高。
克里斯提娜微笑地坐在床角,觀察著他們。她感覺自己和兄弟們的距離變遠了,畢竟她是年齡最大的,而且是個女孩。就在不久前,她還不被允許開窗戶,不能出門。“那時我很渴望正常的生活。”而現在她想念原來的馬克斯。他變了,已經能夠和別人深入探討無人機的未來或是搭建樂高戰船。馬克斯說,他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畢竟他都已經戰勝了癌癥。
尤斯圖斯最近變得非常孩子氣。以前他總是體貼、小心,說話輕言細語,現在他聲音變大了,變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男孩。“尤斯圖斯總在大喊大叫,馬克斯總在評論。”克里斯提娜說,“我很高興看到他們兄弟倆吵架,而不是尤斯圖斯永遠讓著哥哥。我們首先得學會,怎樣成為一個正常的家庭。”
今年4月的一個周五下午,克里斯提娜坐在柏林購物中心的一家咖啡廳中,吸著奶昔。她想買一個新包,順便散散心。馬克斯的血檢結果有點不正常,他們是否又要重新開始他們以前的生活?克里斯提娜平靜地說:“沒關系,不會有更糟糕的情況了。”
4月底,警報終于解除:馬克斯的癌癥沒有復發。馬克斯說:“我最大的冒險開始于一歲,結束于今年4月30日。”現在他可以過一個正常10歲男孩的生活了,而他的父母要努力避免克里斯提娜和尤斯圖斯再次消失在陰影中。
[譯自德國《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