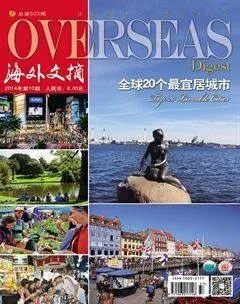時光機器
這輛老舊的綠色汽車漂洋過海,如同一臺時光機器,向新主人述說它見證的幾十年人生故事。
在一片遙遠、寒冷的海洋中,浮游著一個綠色的點。這是一輛20世紀70年代的老汽車,牢牢固定在一艘貨船甲板上的貨運箱里,在深夜筆直向前行進。這輛有輕微刮痕的經典保時捷911跑車在洛杉磯被開進集裝箱,船從港口開出,向南行駛,穿過巴拿馬運河,橫跨大西洋。幾個星期后,2013年10月,這輛綠色汽車停在我的車庫中。
然而,在它還在海洋上前進之時,我并不知道它朝我奔來的方式。我也沒有覺察到,這輛在荷蘭鹿特丹上岸的老汽車,它褪色的車漆和龜裂的人造革中藏有這么多年的美國歷史,帶來了加州的溫暖音樂,對越南戰爭的記憶,以及白宮中的過往歲月。
就在這輛車停在我家樓下的車庫中時,我在樓上客廳的筆記本電腦上看YouTube上的一個視頻:一個快70歲的男人,撥動吉他,唱著他的最后一首歌。一個人在生命結束之際唱的歌曲,還有比鮑勃·迪倫的《一切都結束了,憂郁寶貝》(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更合適的嗎?他是那樣柔弱,但充滿音樂和旋律感,他的哀愁風情無限。他是來自加州伯克利的一位吉他手。當我在YouTube上看到他最后的影像時,他已經去世幾周了,但那時我也并不知道這一點。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活和他的綠色汽車就像一部時光機器一樣,已經來到我跟前,將向我講述幾十年的美國故事。
吉他手
這個男人名叫戴爾·米勒,我在車的舊文件中找到了這一信息。2013年夏,他得了淋巴癌,因此我不可能再結識他了。在加州伯克利的一棟漂亮老房子中,住著他的妻子,律師特里·赫爾布希。那里還有戴爾的吉他,地下室中仍存有幾罐為這輛老汽車準備的機油。
戴爾在90年代買了這輛二手車。它是那么綠——橄欖綠色,斯圖加特的工廠如此稱呼這種顏色,而戴爾稱之為“鱷梨綠”。他的父親老戴爾來自一個橄欖綠色的制服世界,他是美國前總統林登·約翰遜的顧問。約翰遜繼承了肯尼迪在60年代初期遺留的越南問題,絕望地在白宮領導越南戰爭多年。
但是,當我在巴伐利亞鄉間的舊貨交易商馬提亞斯·平斯克那里第一次看到這輛綠色跑車的時候,我怎么會知道這些?謹慎、友好的平斯克從美國接管這輛保時捷車,就連他也不知道這輛綠色的老車究竟經歷了些什么。但是他感覺得到,它的故事絕不尋常。平斯克肯定不是那種相信東西有靈魂的人,但是他知道,老汽車會粘附一些東西。因此他兜售這輛車時的廣告詞是:“常青,卻有911次變化。”
我用一輛二手大眾高爾夫的價格把它買了下來,我喜歡買舊車,可能是因為它們有時讓我覺得還生活在過去。有些東西,哪怕它只是一輛車,也會將幾十年的短暫瞬間永遠背負在自己身上。
那個晚上,當我在YouTube網站上看到戴爾唱著他最后的歌謠,手指輕輕地在吉他弦上撥動時,我突然明白了,為何這輛車里裝有這么好的音樂設備,那是藍寶公司的揚聲器。我買了一個吉他手的汽車,一個自70年代就制作黑膠唱片和CD光盤的音樂人的汽車。有時候他從工作室開車回伯克利,會在車里聽自己剛剛試奏的曲子。那個傍晚,我買了戴爾·米勒的兩張CD,它們有漂亮而憂郁的名字:《指彈碎片其他樂事》(Fingerpicking Rags Other Delights)和《時光流逝》(Time Goes By)。
在秋日巴伐利亞州的鄉村道路上,我靜靜聽著戴爾的歌。那個晚上,我閱讀了在搜索引擎上找到的一切關于他的信息,直到天色破曉。我發現了戴爾的博客。他對自己得病、和癌癥作斗爭的那幾個月進行了詳細的記錄。他用幽默而充滿詩意的筆觸記錄下自己的死亡,也許是因為他仍然認為醫生可以救他。他也寫到他的保時捷汽車,他想賣掉它,因為他太虛弱了,無法在海灣大橋的黃昏堵車大流中掌握好離合器。
戴爾的病情迅速惡化。2013年3月他收到診斷書,8月博客就停止更新,他的生命結束了。網上只能找到一則報紙悼詞,出自一位名叫特加·格爾肯的音樂人之手,他是戴爾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他評價戴爾“聰明、熱心”,在最后幾句話中他也提到了這輛綠色的保時捷車。他知道,戴爾會喜歡。
來到美國
那之后,我從慕尼黑給伯克利的特里·赫爾布希寫了一封信。特里打開它后,很快哭了。盡管如此,她仍然回復我,我該去一趟伯克利,她想講講戴爾的故事,以及她的故事。
就這樣,2014年春,在戴爾去世9個月后,在這段二手綠汽車帶來的緣份牽引下,我乘坐漢莎航空的飛機來到舊金山。我在機場租了輛車,順利來到特里的家,站在門口的她非常友好,絲毫沒有對一個陌生人的戒備心。
她告訴我,他們怎樣坐著這輛車去往墨西哥的沙漠,來到峽谷和荒涼的沙地,最后墨西哥人怎樣圍繞著車站立,大叫“Alemania(德國), Alemania”。日落時,戴爾為她彈奏吉他,而她在一個小山丘上最后的陽光中隨著音樂起舞。
“他生命的最后幾周都是開著這輛車去醫院的。”特里說。戴爾非常重視汽車保養,注重尾氣凈化器的性能,從來不在瀝青馬路上留下油滴。他希望他的保時捷是自然環保的。這輛車的顏色總是讓特里想到20世紀70年代的廚房,她喜歡這顏色。他們在屋后種了一棵小小的檸檬樹,房中總是傳來尼爾·楊的永不過時的搖滾樂,“在自由世界里搖滾!”戴爾的老iPod機里有很多迪倫、The Band樂隊和恐怖海峽樂隊的歌曲。有時戴爾也會載著徒步旅行者駛過伯克利的山丘,在迪倫的音樂聲中,讓他們看最美的小徑和森林。
“他討厭華盛頓。”特里說。戴爾的父母是出身良好的德克薩斯人,年輕時候就來到了首都,為民主黨人林登·約翰遜工作。還是小男孩的戴爾和約翰遜出現在一張照片上,這位政治家看上去很慈祥,戴爾戴著一頂牛仔帽,手上拿著一把手槍。父母讓戴爾上軍校,好在一場變故解救了他。戴爾和幾個朋友在軍校兵營中叫了個披薩,這是被禁止的,他們被降級了,不再允許為他們的祖國戰斗,在越南也不行。這場事故讓他成為留著長發的“垮掉的一代”中的一員,而不是帶著噩夢歸來的越南老兵。
在特里的伯克利別墅以北15英里處,約翰·馬羅尼站在自己的修車車間中。約翰是越南戰爭的幸存者。70年代初回國之后,他決定靠修車安身立命,他修的車中就包括這輛后來屬于戴爾的1977年產的綠色保時捷。“那綠色太奪目了,我永遠不會忘掉它。”約翰說。
戴爾從來不知道越南老兵約翰曾經修過他的保時捷汽車。當時這輛車還不屬于他,它屬于加利福尼亞的一位醫生,一位注重養生、經常慢跑但仍然英年早逝的醫生。那時戴爾正在努力創作音樂,在舊金山坐出租車,直到這位家境殷實的醫生去世,家人賣掉他的老汽車之后,1998年戴爾才和這抹綠色相遇。
“那時候一切都還完全不同。”特里說。那時她還沒有花園,沒有伯克利的房子,也沒有這輛綠色的保時捷。那時她是一名律師,為來到美國避難的伊朗、阿富汗、薩爾瓦多難民申請居留許可,讓美國給他們一個逃離自己祖國的謀殺和戰爭的機會。
現在特里仍在幫助外國人獲得美國居留許可,并憑此收入頗豐。不過這些人的身份已經完全不同了,他們是在硅谷工作的申請入籍的印度程序員。她常常開著這輛綠車去硅谷,因為一家為谷歌提供產品的印度軟件公司的老總瘋狂喜歡搭她的車,甚至能對車牌倒背如流。特里讓他坐在副駕駛座位上,一起去吃午飯。
我在一家小咖啡館的后院中見到了特加·格爾肯。他為戴爾寫悼詞,組織紀念音樂會,邀請很多音樂家助陣,很快就門票售罄。
1970年出生在德國埃森的特加,可能從來沒有預料到自己會在伯克利和一位保時捷車主成為朋友。特加的父親是一位精神分析師,總想離開德國,70年代他就和兒子一起生活在美國了。后來,特加在舊金山認識了戴爾。“我當時還想,哇,大部分布魯斯吉他手都不會開保時捷,不會穿名貴的意大利鞋,也不會嗜好戴奇怪的帽子。但是戴爾就是這樣。”特加喜歡他。孩提時就和父親在墨西哥旅游過的特加,得知戴爾想開著保時捷進入沙漠時,幫助他在德國買了一個車尾行李架。然后,戴爾就載著特里和他的吉他出發了。
在伯克利的最后一天,特里問我是否可以幫她整理地下室。這可能會很有趣。那里有戴爾的歷史,很多原裝唱片層疊碼放,保時捷維修工具整齊排列,50年代的兒童T恤上寫著:如果我可以,我會選擇約翰遜。這是米勒家的孩子在華盛頓時必須穿的。
重新上路的方向盤
回到慕尼黑之后,我走進車庫,站在車前,光線慘白。現在我知道,哪些劃痕來自墨西哥之行,哪些凹印來自伯克利的垃圾桶。我看到了幾十年里的一個個瞬間。我看到螺絲釘,曾經是一個越南老兵擰緊了它們;一名硅谷程序員曾經坐過它的副駕駛座;一位美國總統顧問的兒子曾在這里聽過迪倫的歌。
當我第一次見到戴爾的老車時,我還不知道它的前車主是誰,來自哪里,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歡這車的小方向盤。它不是原裝的,戴爾自己改裝了它,他認為這樣比較好抓握。我請舊貨交易商平斯克幫我換回了原裝的方向盤。平斯克換完之后將戴爾的方向盤賣給了他的一位顧客。他不記得具體賣給誰了。
于是,美國歌手戴爾·米勒的方向盤,如今在德國的道路上,在另一輛老保時捷車中控制著前進方向。它會很好地轉彎,在蜿蜒的街道上,也在人生的道路上。這個關于一輛汽車的美好而悲傷的故事仍在繼續。我相信,戴爾會喜歡它。
[譯自德國《南德意志報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