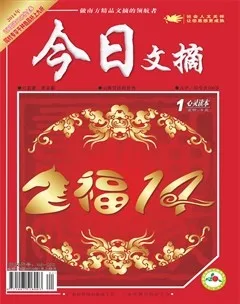NASA又喊中國人“狼來了”
2013年11月,王吉期盼已久的第2次開普勒科學會議,終于要由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召開了。
他是耶魯大學的博士后,也是國際天文學界中的一顆新星。今年初的美國天文學年會上,他參與的“行星獵人”項目組宣布,發現15顆可能宜居的“超級類地行星(與地球相似但體積巨大的行星)”,而之前人類已知的有19顆;相關論文發表時,他是第一作者。
但是,王吉等來的卻是一封拒絕信。他的導師德布拉·費希爾教授因此聯系了NASA,對方回復:“今年3月通過的聯邦法律禁止我們邀請任何中國公民。至于那些已在美國其他機構工作的(中國)員工,由于近期國會通過的法案,鑒于安全因素也將受到同樣的限制。”
中國公民不得入內?
美國總統奧巴馬于2013年3月簽署了《聯邦反間諜法》,內容包括:NASA不可在旗下設施內接待任何中國公民。另外,基于2013年7月通過的保安法案,NASA被禁止動用資金與中國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NASA拒絕王吉參加會議的理由很簡單:會議地點在其研究中心內。除了王吉,還有5名中國科學家也收到了拒絕信。這些事情,費希爾教授收到NASA的回信后才知悉。
“我不能禁止你們去。但我抵制這個會議。”她對學生們說,隨后她的研究團隊正式退出會議。憤怒的費希爾教授還對媒體講述了事情經過,令這一消息迅速為人所知。
這并不是NASA第一次拒絕中國人。2011年5月16日,美國“奮進”號航天飛機升空,該項目有不少中國科學家參與。兩名中國記者在發射半個月前得到采訪許可,但當天他們來到現場時,卻發現登記表上自己被列為“無權限進入”。換句話說,他們的采訪權被臨時取消了。
事實上,那次中國記者被NASA拒之門外前,美國兩黨也正在為聯邦政府預算爭執不休。很少有人注意到,在2011財年開支法案中,有一條不太起眼的條款:“禁止NASA及白宮科技政策處運用政府資金,與中國或與中國有關的企業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并禁止NASA接待中國官方訪問者。”
而在該年底的《鞏固和進一步持續撥款法案》中,這則條款被保留了下來。將它納入預算法案的,是共和黨人、前美國陸軍律師弗蘭克·沃爾夫,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商業、司法、科學及相關機構小組委員會主席。
7月,沃爾夫再次讓這一條款出現在新的財政預算案中。幾天后,奧巴馬簽署了包含這些條款在內的一部撥款法案。
NASA局長查爾斯·博爾登則下令:“禁止他們(中國人)與NASA設施有任何新的接觸,還禁止他們遠程使用NASA的資源。”2013年3月,博爾登在眾議院作了長篇陳述。他列出,正在使用NASA設施的有281位外國公民,其中192名是中國人。
間諜案引發最嚴苛規定
此次NASA禁令的升級,與一位中國雇員直接相關。
3月16日,華盛頓機場一架飛往中國的飛機即將起飛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人員攔下了32歲的姜波,并檢查了他的行李。
姜波是成都人,NASA蘭利研究中心前雇員。2012年底他曾攜帶工作用電腦和一個硬盤回國休假一個月,回到美國后被告知合同不再續約,原因是違反了NASA的安保規定。
他準備離境之前幾天,沃爾夫議員曾對媒體說,NASA可能出現安全疏漏。隨后,沃爾夫在眾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表示,姜波有間諜嫌疑。FBI隨即立案調查。
姜波被關押后,沃爾夫又在新聞發布會上稱:姜向FBI隱瞞了攜帶筆記本電腦、一個舊硬盤和一張移動電話卡的事實。“而且,他買的是單程票,有潛逃嫌疑。”
姜的律師辯解道,姜沒有綠卡,被解雇后無法在美國長期居留,因此打算先回國休息一段時間,再去一家歐洲公司赴任。最終,FBI在姜波的電腦里沒有找到機密資料,于是撤銷間諜指控,改控其“在工作電腦上非法下載版權電影和色情影片”,勒令其48小時內離境。
而在推動調查姜波的同時,沃爾夫還將矛頭對準了NASA。他說,讓這個中國籍雇員接觸到敏感資料,已違反了撥款法案中的相應條款。隨后,沃爾夫帶領的撥款小組開始審計NASA的資金運作情況。
顯然,NASA局長博爾登非常配合。除了在國會對沃爾夫陳述的那些措施外,他還關閉了一個重要的天文學數據庫,其中儲存著數以百萬計的期刊文章、視頻等資料。
此后,在沃爾夫的推動下,3月26日出臺的撥款法案中,包含了對NASA與中國之間關系限定最嚴苛的規定:中國公民既不能參與NASA的工作,也不能遠程使用NASA的資源。他的理由是:情報人員和留學生、科學家很難區分,而“中國的航天計劃事實上是由軍方負責,不應讓中國有機可乘,取得美國的技術優勢,特別是航天技術”。
“中國間諜論”
姜波案只是導致這些禁令出臺的最后一根稻草。
近年來,美國媒體上經常可見“中國間諜”的討論。9月底,《紐約時報》曾報道,根據一家安全咨詢公司的研究,在過去兩年,“中國為了提升本國無人機技術能力,不斷通過網絡追蹤美國軍用無人機的技術承包商獲取情報”。
此前,2007年3月,美國五角大樓分析人員伯杰森被指控曾向中國特工出售軍事機密,被判刑4年半。2009年4月,美籍華裔科學家舒全勝被判處51個月的監禁,罪名是“非法向中國提供空間技術”。
商業領域也有案例。2009年10月14日,美國福特公司項目工程師郁向東在芝加哥機場入境時,遭到美國警方以竊取福特公司的商業機密為由逮捕。之后不久,BBC還報道了有關中國商人馬立頌在美國因購買特殊碳纖維,遭國土安全部門調查的消息。
美國國防部發布的《2012年度中國軍力報告》指出,中國通過非法手段獲取軍民兩用和軍用技術為自己所用。而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還曾發布報告稱,中國在航天領域取得的進步“部分歸功于成功的間諜活動”。
“中國間諜”話題的廣泛性,導致去年3月NASA相關禁令出臺后,針對中國的禁令并未引起天文學界網站SpaceRef的關注。讓這家網站意外的是,緬甸、烏茲別克斯坦、厄立特里亞也在NASA的相關禁令中——它們可能連像樣的航天產業都沒有。
“這不是科學,而是政治”
2013年3月NASA關閉天文學數據庫時,美國科學家聯合會項目負責人斯蒂文·阿芙特構就曾評論這是“嚴重的過度反應”,并說NASA正在向控制預算的議員屈服。
而此番中國科學家因國籍被擋在NASA召開的科學會議之外,再度引發不少科學家的抗議。“這次會議討論的是科學以及星體,與國防安全無關,全都是可公開獲得的數據。”費希爾對《衛報》說,“我們的同事由于國籍而被禁止參與會議,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
天文界泰斗級人物格夫·馬爾西則說,NASA“很不道德、非常可恥”;牛津大學天文學家克里斯·林托特說,以國籍限制科學家參加會議,如同回到了冷戰年代。他建議NASA更改會議地點以避過禁令,若情況得不到改善,“科學界應全面抵制會議”。
“真不幸,這不是科學,而是政治。”會議的合作組織人艾倫·博斯近日回應,以前他一直拒絕討論這一話題。
學界的呼聲最終傳到了沃爾夫耳中。在事件越演越烈之際,他給博爾登寫了一封7頁的信,說NASA誤讀了預算法案:“這是限制NASA同中國的雙邊合作,而不是多邊合作、會議或者其他學術活動。沒有禁止中國國籍的個人參加NASA的活動,除非這個人代表了中國官方。”
似乎被“擺了一道”的博爾登則于10月10日承諾:一旦美國聯邦政府重新運作、NASA開始正常工作后,他會立即聯系原本遭拒的6位中國科學家。不過他也補充,這些人依然需要通過全面安全檢查,這一過程通常要耗時數周;聯邦政府停擺后NASA有97%的員工放了無薪假,這些人得等負責會議流程的雇員回來后才能被重新加入與會名單。
實際上,博爾登自己的學術活動也受到了限制。9月下旬,第64屆國際宇航大會在北京召開,他得提前向國會申請豁免、得到允許后才成行。
會議期間,博爾登與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就兩國在航空領域合作“坦誠交換了意見”——眾所周知,在外交辭令中,這一說法意味著雙方分歧很大——雙方都表示希望加強太空技術合作。不過,有上述保安法案在先,中國科學家對兩國合作態度悲觀,因為這涉及衛星等可用于軍事的技術,只要兩國在政治上互有戒心,合作終將流于表面。
當然,還是有好消息的:如果時間還來得及,美國政府早些重新“開門”,王吉等人或許能看到來自“開普勒”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