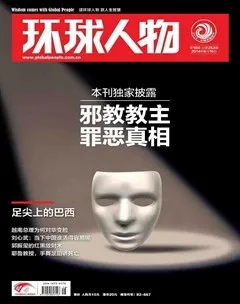足尖上的巴西




“足球王國”巴西終于又一次在本土迎來了世界杯。1950年在里約熱內盧馬拉卡納體育場輸給烏拉圭痛失冠軍,讓巴西人耿耿于懷64年。這一次,世界杯的回歸讓整個國度再次沸騰:市中心、海灘、候機樓,隨處可見迎風飄揚的巴西國旗;社區、街道和酒吧都被黃綠兩色的飾帶、油彩、氣球裝點一新;各大球場也即將迎接球迷們排山倒海般的吶喊聲……
每次比賽都是狂歡
巴西是唯一一個參加過歷次世界杯的國家,巴西足球隊也是目前世界上奪冠次數最多的一支球隊,曾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次奪冠,并在前三次奪冠后永久擁有了雷米特金杯。遺憾的是,雷米特杯于1983年被盜賊偷走后熔化。后來,巴西足協不得不制作了一個復制品。
記者在巴西生活工作期間,曾經歷了1986年、1990年、1998年和2010年四次世界杯比賽。每一次,記者都能感受到節日的狂歡氣氛。
每到世界杯開賽的日子,里約熱內盧、圣保羅、巴西利亞、阿雷格里港等大城市處處張燈結彩。巴西人具有非常豐富的想象力,喜歡用特有的方式為節日梳妝打扮。居民區里,球迷們在街道兩旁的大樹上拉起繩索,掛上一條條黃色的、綠色的彩帶,人走在路上,滿眼都是彩帶飛揚。地面、臨街的墻壁被人用成桶成桶的油漆繪出碩大無比的球星、足球,年輕人則喜歡用油彩在臉上涂抹出自己心愛球星的名字或“巴西”“冠軍”等字樣。
商店里更是獨具特色。商家們早早準備了各種紀念品,球衣、咖啡杯、皮包、酒具、帽子……上面都被繪上了與足球有關的圖案,似乎世界杯已經浸入到每種商品里。街口、路邊會有許多地攤,小販們抓住機會出售巴西隊的球衣、帶著小木桿的國旗以及看球時用的喇叭等,處處能聽到叫賣聲。
街談巷議的也都是世界杯和巴西隊的球星。你到朋友家做客,與鄰居打招呼,最容易親近的方式就是談足球。每當記者贊美巴西隊,說它一定會奪冠時,巴西朋友都會開懷大笑,甚至激動地與記者擁抱。很多次,記者在街上散步,向喝啤酒、看球賽的巴西年輕人豎起大拇指,他們都會興奮地邀記者坐下喝一杯,津津樂道地大談球賽。
隨著生活的改善、科技的發展,巴西人現在家里都有電視。每逢世界杯有巴西隊比賽時,他們便會邀親朋好友到家里一起觀看球賽。但與過去相比,氣氛已經淡了很多。當年電視還是奢侈品,巴西人是到城市廣場、街頭酒吧觀看世界杯球賽。那里球迷多,人氣高,熱鬧非凡。首都巴西利亞南湖區商業中心是酒吧和餐館比較集中的地區,自然也就成為觀看世界杯球賽最好的地方。每當有巴西隊出場時,球迷早早就從四面八方開著車趕來,或三三兩兩地坐在酒吧露臺上,或成群結隊地站在一起,觀看酒吧餐館早早為他們準備好的大屏幕彩電。每當球隊進球,男孩們會吹響震天的號角,女孩們則扭動腰肢,跳起歡樂的桑巴舞。特別是電視播音員在進球時發出的那一聲“GOLLLLLL”,特意拖長的尾音久久回蕩,能把任何一個球迷感染得手舞足蹈。
在世界杯的日子里,巴西人的情緒隨著足球轉動。球場外或欣喜若狂,或垂頭喪氣,讓人看到了一個國家的情緒。一次,巴西隊取得了一場比賽的勝利,球迷興奮地開著汽車上街游行。當記者向一輛汽車里的球迷表示祝賀時,他竟放下玻璃窗,探出半個身子,不顧危險把一面巴西國旗塞進記者手中,讓記者將這面國旗打起來和他們一同慶祝。
巴西人對足球有著獨有的熱情。記者手頭的一份資料顯示,從1971年至2009年,即便賽程密集,巴西平均每場球賽出售的門票仍有1.5萬張左右,上世紀80年代曾達到平均2萬多張。只要有自己喜歡的球隊參賽,一些并不富裕的球迷寧可節衣縮食,也要前往助陣。遇到全國甲級聯賽的決賽或類似世界杯這樣的重大比賽,許多單位提前下班,萬人空巷,甚至國家領導人也暫停國務活動,與民同樂。
球場也是最能體會到巴西人情感的地方。記者曾在里約熱內盧、阿雷格里港、薩爾瓦多等地觀看過當地舉行的球賽,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阿雷格里港觀看的一場甲級聯賽。當球賽開始后,球迷的神情隨著比賽的跌宕起伏而悲喜交加。球星一腳出色的傳球,會激起滿場的喝彩聲;激烈的對抗或盤帶過人時,球迷們的緊張又令全場窒息。一旦主隊進球,數萬人同時起立歡呼,揮動旗幟,掀起一波波的人浪,彩帶漫天飛舞。而當客隊帶球沖到主隊門前時,憤怒的叫聲和失望的噓唏聲響成一片,甚至全場球迷同唱起一首歌。記者聽不懂歌詞,就問身旁的巴西球迷,經他們解釋,才知道這是一首詛咒客隊的歌。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愛恨,還真是別有一番情趣。
今年的世界杯已經進入倒計時,不遜于以往的狂歡也進入倒計時。每到這個時刻,巴西人之間沒有年齡、職位、貧富和尊卑的界限,球賽正把他們純樸奔放的民族特性展現出來。
為什么是巴西
記者曾無數次問過巴西人:“足球,對你們來說意味著什么?”答案五花八門。有人說:“足球是我的生活。”沒有足球,生活會變得索然無趣;也有人說:“足球是信仰。”巴西人對足球的喜愛有著宗教般的執著和狂熱,只要有球賽,球迷們便像朝覲一樣涌向球場觀賽;還有人說:“足球是社會,我們因足球而和諧地生活在一起。”在巴西外交部門前就有一個這樣的石雕:五塊異形石塊分別代表著五大洲,如果將它們組合起來,就變成一個球;更有人說:“足球是巴西人的性格。”進球是巴西人心靈深處吹響的號角,帶著球一路奔跑,直到射門進球,那種快樂和喜悅是巴西人的最愛。
巴西人已經與足球融為一體,細算起來,足球在巴西有100多年的歷史。
巴西位于南美洲東南部,面積約851萬平方公里,是拉丁美洲面積最大的國家,居世界第五,人口1.91億。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卡布拉爾發現了巴西,將這片土地命名為“圣十字架”,并宣布歸葡萄牙皇室所有。因為巴西有著豐富的森林資源,歐洲人開始在這里大肆砍伐巴西紅木,漸漸地,“紅木(Brasil)”一詞代替“圣十字架”,成為巴西國名,并沿用至今。1822年,巴西宣布獨立。
根據官方的巴西足球史,最早將足球運動引入巴西的是一位叫查爾斯·米勒的青年。米勒1874年生于巴西,父親是一名鐵路工人,把他送到英格蘭接受教育。1894年米勒回到巴西時,帶回了一個足球和兩本足球規則。當父親問他在英國學了什么,他就指了指足球。正是在他的推動下,足球運動得以在巴西發展起來。
優越的氣候條件或許是足球很快在巴西扎根、生長的自然原因之一。巴西地處熱帶,陽光燦爛,雨水充沛,哪怕是在樓房林立的城市里,都會長出綠茵茵的草地。因此,一到周末,居民社區的草地上、公園的林地里,親朋好友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踢一場球,成了最普通不過的事。
炎熱的氣候鍛煉了巴西球員持久的耐力和踢球的風格。巴西球場的地面溫度有時高達50多攝氏度,據球員講,跑在球場上都能感到腳心發燙。天熱不適合大范圍跑動和長傳沖吊戰術,因此,巴西球員擅長短傳配合,以盤帶過人、地面進攻為主。
而在里約熱內盧、薩爾瓦多、福塔雷薩等沿海大城市,沙灘是人們最好的足球場。別小看這些沙灘球場,它們往往是最好的訓練場。有一次,記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跟蹤采訪來巴西訓練的中國國家足球隊。我們一起練跑步,腳踩在柔軟的沙灘上,球鞋似乎失去了彈性,一會兒腿肚子就感到累了。一旦再到公路上跑,明顯感到步伐輕快多了。
除了自然要素,更值得一提的是人。巴西人是由土著印第安人、歐洲人和非洲人混血融和的多民族國家,其中白人占54%,混血種人占39.9%,黑人占5.4%,亞裔黃種人占0.5%,印第安人占0.2%。人種上的兼容并蓄,讓巴西人常常具有印第安人的堅韌、非洲人的靈活和歐洲人的速度與體魄。這是其他種族難以獲得的優勢。
足球與巴西人稱得上是“天作之合”。在巴西,男孩幾乎個個都會踢球。只要腳邊有球,他們用木棍搭個球門,就建起了一個足球場,可以隨心所欲地踢,變著花樣地踢。2013年,英格蘭球員沃爾科特曾在短暫逗留巴西后感慨:“我們都知道足球運動在巴西很普及,但在看到一些六七歲的小孩踢球時,我震驚了。他們會合理地運用肩膀,我承認這些技巧自己都不會。”而事實上,不少聞名世界的巴西球星,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
舞動的藝術
除了自然的恩賜,巴西足球中也激蕩著濃重的文化痕跡。
現代足球傳入巴西后,起初只是白人的一項活動。那時的觀眾也多為白人,他們觀賽時著裝考究,女士著裙裝,男士則西裝革履。然而,當時的巴西已經開始經歷一次重大變革。從那時到上世紀20年代,巴西成為全球吸引外來移民最多的國家之一,成千上萬來自意大利、德國、葡萄牙、日本和非洲的移民擁入這片富饒的土地,在這里扎根生存發展,多元文化成為這個國家最突出的特征。
1888年,巴西成為南美最后一個廢除奴隸制的國家。獲得自由的黑人有了更多屬于自己的時間,足球很快成為他們喜愛的運動。他們的到來,成就了對巴西足球的最大貢獻——將舞蹈、防身術等特殊技能,通過足球發揮出來。
現在一講巴西足球,很多人不可避免地提到桑巴舞,那是非洲原始舞蹈與巴西本土以及歐洲舞蹈相結合的產物。鮮明的節奏,輕盈的步履,巴西人踢球時會借用跳桑巴的靈感。一些巴西球員在攻破對方球門后,會跳一會兒桑巴以示慶祝,不少巴西球隊甚至會在訓練時放上一段桑巴舞曲作背景音樂。
其實又何止桑巴舞。人們從今天球場上奔跑的運動員的動作中,還可以看到至今仍在巴西黑人主要聚居地薩爾瓦多流傳的“卡波埃拉”戰舞的影子。
行走在薩爾瓦多老城區的街道上,記者總會有一種不知置身何處的奇妙感覺。成片的建筑具有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卻浸染著非洲文化最鮮明的色彩。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前的廣場上鼓聲陣陣,上身赤裸的黑人青年正和著節奏向游人們展示一種好像中國武術一樣的戰舞。他們時而強勁踢腿橫掃對方,時而敏捷地空翻躲閃,一招一式都虎虎生風。這就是“卡波埃拉”戰舞。它一般由兩人組合表演,腳上高難度動作層出不窮、巧妙銜接,并與伴奏相和,絲絲入扣。“卡波埃拉”沒有“舞轉回紅袖”的婉約,也不似“起舞弄清影”的空靈,但凌厲的搏殺動作里,深藏著以柔克剛、以巧化力之道。可以說,“卡波埃拉”是生命的律動,是藝術,更是巴西珍貴的歷史和文化。
如今,不少巴西球員都會在球場上不經意做出戰舞的動作:他們腳風凌厲,身形多變。于是有人認為,正是各種舞蹈動作的糅雜,為巴西球員們的精準腳法提供了優秀的“基因”,進而賦予了巴西足球的現代風格。
巴西黑人將足球從一項體育運動提升為了一種藝術,將球場變成了娛樂的大舞臺,但直到1938年,兩位黑人球員首次代表巴西隊前往歐洲參賽,歐洲人才真正認識到黑人的力量——他們不僅會踢球,而且可以比白人踢得更好。真正改變黑人足壇地位的是1958年的世界杯。在那屆世界杯中,巴西隊第一次奪得世界杯冠軍,年僅17歲的小將埃德森·阿蘭特斯·多·納西門托更是鋒芒初露,一人打進6粒進球。賽后,人們開始稱呼他為球王貝利,他后來成為巴西首位黑人部長。
貝利讓足球運動對世界的貢獻超越了足球本身。1970年,他在尼日利亞首都拉各斯參加了一場表演賽。當時,尼日利亞深陷戰亂,交戰雙方為了不失去觀賞球王技藝的寶貴機會,宣布停火看球。那場比賽讓巴西駐聯合國大使賓海羅高度評價貝利的“和平能量”,稱貝利踢球22年,為促進世界友誼作出的貢獻要比任何國家的任何大使都多。
球隊精神,國家精神
巴西著名足球評論員托斯湯說:“足球教練應當承擔起公共責任,這就是要給觀眾踢出一場好看的足球。”
巴西人特別不喜歡那種節奏拖沓、沒有激情、過多短傳和戰術配合的球賽。記者在巴西觀看過許多場比賽,一旦遇到這種情況,場上的球迷就會大聲吶喊,甚至憤怒起來。巴西朋友告訴記者,巴西國內的足球聯賽,其實要比世界杯更精彩,因為巴西人在場上會有更多的爭球。托斯湯說:“當我看到一位明星在球場上明明可以晃過隊員直接射門,或是給隊友傳出一個決定性的球,但他出于求穩或是缺乏考慮而把球傳到一邊時,我會很不滿。偉大的球星上場比賽,必須全力以赴,這是對觀眾的負責。陣線往后縮,加強防守,伺機反攻,對于不知名的球隊來說,這也許是最好的戰術,但對于巴西這樣的大牌球隊來說,這是不光彩的,巴西隊必須想辦法戰勝對手,同時,又能踢出一場精彩好看的足球來。”
戰勝對手,靠的是不停地進攻。巴西足球教練帕雷拉說過:“最重要的是第一個進球。既然這樣,為何不爭取第一個進球呢?改變場上局面的一個辦法就是整個隊伍要在士氣上壓住對方,千方百計控球往前沖。”2006年擔任巴西足球隊隊長的鄧加也說過:“對于任何一位想要披上巴西國家隊戰袍的球員來說,比賽的激情以及對勝利的渴望是基本的條件。”于是,人們在賽場上看到的是巴西球員獨出心裁的創意、不停進攻的士氣,這使滿場比賽賞心悅目。
巴西球員對比賽的激情和進攻的渴望,往往也會使巴西人感到沮喪。因為他們把目標定得太高,每次比賽必得冠軍不可,不得冠軍似乎就意味著失敗。1998年世界杯,巴西隊在與法國隊的決賽中失利,痛失冠軍。能夠在世界杯比賽中拿到亞軍,應當說是很好的成績了。為此,時任總統卡多佐特意在總統府舉行隆重的儀式,歡迎賽后歸來的球員。那天,記者和巴西同行一大早就趕到總統府,想親眼見見這些名揚全球的球星。當球迷簇擁著車隊來到總統府時,記者發現,走下汽車的巴西隊球員個個神情沮喪,好像打了敗仗歸來一樣。卡多佐總統親手向每位球員授予一枚國家級勛章,并且說了一番贊揚的話,但當我們拿著錄音機采訪羅納爾多等人時,他們依然沉默無語或簡短應對一下就離開了。“五星冠軍”的巴西隊,就是這樣一支不甘落后、進攻求勝的球隊。
這種逢戰必勝的情緒,已經成了巴西民族性格的一個部分。有人說,沒有足球就沒有現代巴西的國家精神,足球是巴西人的國家自尊,是巴西的民族之魂,是國家精神的“凝聚劑”,也是個人情感的“揮發劑”。一位巴西球迷告訴記者,每個民族都需要有一些事情能引發集體共鳴,能盡情釋放內心的情感。但是,世界上能夠因為足球而產生集體共鳴的或許只有巴西。可以說,巴西的國家自豪感不是靠戰爭的勝利和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勝利創造的,而是靠足球的勝利帶來的。
總統不敢怠慢球星
無論是哪個黨執政都不敢怠慢球星,每次帶著勝利喜氣歸來的巴西足球隊員都會在總統府受到隆重的接待。1969年,貝利在馬拉卡納體育場踢進個人生涯的第1000個進球后,時任巴西軍政府總統梅迪西破例在總統府接待了他。巴西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科洛爾也曾在總統府舉行儀式,慶祝貝利50歲的生日。總統們還會通過表達自己對足球的熱愛和見解來親近民眾。前總統卡多佐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就提到,自己不嗜好足球,但不得不隱瞞這一點,因為足球能夠拉近他和民眾的距離,提升他的親民度。
還有一些總統,十分善于利用足球為自己造勢。前總統盧拉執政8年,曾兩次在總統府歡送國家隊征戰世界杯,只可惜球隊每一次都沒有邁過1/4決賽這道“坎”。盡管如此,4年前,他在接過世界杯承辦權時仍不忘用幽默的語言來為自己的政治拉票:“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同胞卡福今天也在現場,他曾以巴西的名義自豪地舉起過世界杯的冠軍獎杯。他不再上場踢球了,但是從今以后,他可以在我的‘球隊’里踢球。”
一個有意思的事實是,巴西推翻軍政府統治、實行民主直選以來,除了1989年外,每次總統大選都和世界杯不期相遇。因此,世界杯哨聲吹響后,球場上巴西隊每一次進球都會牽動國內大選的神經。2010年世界杯期間,首次競選巴西總統的迪爾瑪·羅塞夫和盧拉一起,身穿巴西隊球衣,坐在電視機前觀看世界杯比賽,而另一位巴西社會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塞拉卻穿著西裝到酒吧看球,一下子把自己與普通民眾的距離拉得很遠。果然,羅塞夫最終如愿以償成為巴西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2014年,巴西總統大選再次與世界杯相遇,羅塞夫將在10月競選連任。正如巴西政治學教授拉法埃爾·科德斯所說,雖然世界杯的勝負不再是今年大選的決定性因素,但“依舊是政府用來進行正面宣傳的一個機會”。于是,每一個世界杯賽場落成,羅塞夫必到場祝賀,利用這個機會展示對足球的支持和喜愛。不久前,羅塞夫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還突出強調了足球的政治意義。她說,數十年前她因參加反獨裁的游擊隊而被捕,遭到審訊者折磨。即便是身處圣保羅的監獄,她與其他反對軍事獨裁的獄友們,仍滿懷熱情地關注著1970年的世界杯大賽。羅塞夫回憶說,許多反獨裁者一開始擔心給巴西隊加油會助長軍事獨裁勢力。但是,當巴西在決賽中迎戰意大利時,他們的反對也隨之減弱。
一絲雜音
隨著中產階層的增加,巴西人對足球的感情依賴也在變化,他們很多人將足球看作是生活中的娛樂活動,足球與國家政治榮耀感的聯系正在減弱。去年以來,巴西各地反世界杯的游行接連不斷。很多走上街頭的人認為,本屆世界杯的籌辦花費太多,高達117億美元,超過了前兩屆世界杯的總和,這筆錢應當用到提高社會福利和工資收入上去。
5月末,巴西隊剛剛開始集訓,就遭遇由數百名教師和教育部官員組成的游行隊伍圍堵。他們高舉標語對球隊和記者呼喊著“教師比內馬爾(巴西國家隊頭號球星)更有價值”“衛生和教育需要錢” “不會有世界杯,這里有罷工”等口號。
在巴西利亞,印第安原住民群體也舉行了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稱政府修建世界杯場館破壞了他們的居住環境,他們甚至用長矛和弓箭襲擊警察。在圣保羅,公交車和地鐵乘務人員的大罷工一度使整個城市交通癱瘓。據巴西媒體報道,為了確保警察在世界杯期間不罷工,巴西政府已經宣布對聯邦警察加薪15%至18%。
對于一波接一波的罷工和示威活動,前總統盧拉等政治家認為背后有其政治原因。盧拉在西班牙媒體上撰文稱,某些團體認為世界杯如果失敗,今年10月選舉的投票箱就會向他們傾斜,因此他們總是傳播虛假信息,甚至有時誤導國際媒體。
當然,與由衷的熱愛和歡慶相比,這些示威與抗議只是一絲雜音。巴西總統羅塞夫6月8日在中國《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稱,舉辦世界杯是巴西人民的驕傲。無論在場內還是場外,巴西人都將團結一致,努力提供一場體育盛宴。在這個月,到巴西的游客會發現,巴西現在是一個成熟、繁榮和民主的國家。“對我們來說,足球就是生命的慶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