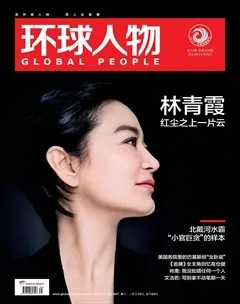87歲文潔若:寫到拿不動筆那一天



人物簡介
文潔若,翻譯家。1927年生于北京,是中國翻譯日文作品最多的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的作品,很多都是經由她之手被引薦給中國讀者。她與丈夫蕭乾晚年合譯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更是一件文壇盛事。
走進文潔若的家中,100多平方米的空間里,走道邊、沙發上、柜子里、床上,都放滿了書,幾乎沒什么下腳的地方。就連一個廢置的冰箱里,打開來也塞滿了書與資料。環球人物雜志記者想找一個地方安置攝像機,好不容易才收拾出來。這個家簡直像是文潔若的一個“車間”,老人把自己的生活空間壓縮到最低,重心依舊放在工作上。
就在不久前,由文潔若主持翻譯的三島由紀夫作品《春雪》《天人五衰》剛出了修訂本。如今,她每天都要工作8小時,過得忙碌而充實。孩子們都在國外,但這位“空巢老人”身上,看不到一絲消極和頹喪。她語言爽利,思路清晰,臉頰紅潤。她說自己常夢見父親、母親,還有丈夫蕭乾,“夢見的都是好事。”
“書呆子”的求學生涯
我父親23歲時考上了高等文官,赴日擔任外交官。父親很注重對孩子們的教育。我有4個姐姐,兩個弟弟。1934年,父親把我們接到東京,接受多語種的教育。后來,中國駐日大使被撤,父親也被免職。回到北京后,我就讀于東單頭條的一家日本小學,父親靠著變賣東西給我們交學費。
1940年3月,我去了東單三條的天主教圣心學校,攻讀英文和法文。那些金發碧眼的外國孩子,用的是母語,但學習成績卻比不上我。在圣心學校念了將近兩年書,上臺領獎的總是我。后來家中經濟條件拮據,我讀完四年級就輟學了。但我沒有氣餒,一直堅持自學。后來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
我對翻譯自小有一種情結。在日本時,有一次,書店里有一套日譯本的《尤利西斯》。原著是愛爾蘭人詹姆斯·喬伊斯1922年出版的,一度是一部禁書。喬伊斯是西方文學的叛逆者,這本書用意識流的手法寫了大量的心理活動,全書除了夾雜著法、德、意、西以及北歐的多種語言外,還時常使用希臘語和梵文。作者在寫作時處心積慮地為閱讀設置各種障礙,文字生僻、內容艱澀。父親對我說:“你看,日本人連那么難懂的書都翻出來了,要是你用功搞翻譯,將來在書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多好!”
后來回國后,他要求我把一套《世界小學讀本》日譯本轉譯成中文,我每天晚上坐在父親對面,跟他合用一盞臺燈,歷時4年,將10本書譯完,總共100萬字。這為我日后的翻譯工作打下基礎。
自1936年起,父親就失業。在圣心學校讀書時,我穿的是四姐的一雙舊冰鞋,把冰刀卸掉了。上清華時,我穿著父親的舊皮鞋。然而我的功課一直是拔尖的。我一點兒也不羨慕那些身穿皮大衣、每周進兩次城去看美國電影的富家小姐。
那時戀愛與我無緣,因為我是個下了課就進圖書館的“書呆子”。我選了好幾門高年級的課,所以時間老是不夠用。在昏暗的校園里,每次遇到樹林中喁喁細語的情侶,我就想:“我可沒有那份閑工夫。”
共歷磨難二十二載
1950年,我從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考入了三聯書店當校對,幾個月后調到剛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我不僅看譯稿,而且經常找來原文著作。在稿子周圍,密密匝匝地貼上小條,像長滿了胡須一般。我干的活遠遠超出了校對的范疇,經常因為自己“管得太寬”而加班加點。
1953年,蕭乾也調了過去。最初,我從未想過有一天能和他在一起。我們的年齡相差17歲。他之前曾有過3段婚史,二戰時當過《大公報》的駐外記者,是歐洲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1949年,蕭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報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國劍橋又以教席邀聘,劍橋的教授專程去香港接他,應允終身職位。但蕭乾回到了中國,他說:“我像只戀家的鴿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可回國后,他并未被當時的文化界接受,還不小心撰文得罪了人。所以,論名,他當時只是臭名;論利,他更是身無長物。許多人勸我不要同他結合,但最終我還是決定嫁給他。
我們的姻緣是由文字開始的。我經常捧著譯本,帶著原書去向他請教。他講話詼諧幽默,除了對譯文表達明確意見,還給我講一些道理。他反對直譯、硬譯,強調無論譯什么,首先要掌握原著的內涵。我被他的學識吸引了,沒有一個同齡人引起我那么大的興趣。我意識到在文字工作上,我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導,也有了知音。
我曾認識一對夫妻,因為一個愛跳舞,一個不愛,弄得很苦惱。我們則從未因興趣不同而產生矛盾。我們童年都生活在北平,又都上了教會學校。我們都喜歡聽亨德爾的《彌賽亞》和莫扎特的《安魂曲》,我們又都研究外國文學,喜歡狄更斯、羅曼·羅蘭、馬克·吐溫和曼斯菲爾德。
1954年初春的一天,我們從東城區民政局領了結婚證書。我們的婚禮沒有儀式,沒有交換戒指,沒有背誦誓詞,然而兩個人都像找到了生命的歸宿。
婚后,我們互相“改造”。對待翻譯,蕭乾不像對待創作那樣有熱情。但那時創作的條件實在不具備。我就對他說:“既然不讓你去搞創作,你就去翻譯幾本書好了,總比虛度光陰強。”他接受了我的意見,婚后3年,他一口氣譯了《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捷克作家雅·哈謝克的《好兵帥克》,“英國小說之父”亨利·菲爾丁的《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這三部經典之作。
但是好景不長,1957年,蕭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我也當了20多年的“臭妖婆”。那時候,每次運動一來,很多人就一擁而上,斗這個、斗那個,和自己最親的人劃清界限。但我一直相信他:“右派這頂大帽子不論你戴多少年,我都不會離開你。”
我們在惶恐中小心度日。1961年,我曾不顧家里的經濟情況,用我相當于一年半工資的巨款買了一架鋼琴。那頂隱形的帽子給蕭乾的精神壓力太大了,我以為悅耳的琴音能夠使他的心情舒暢一些。
“文革”中,他不堪凌辱,曾決意自殺。為了減少對死亡的恐懼,他就著半瓶酒吃下了大量安眠藥。之后,還沒來得及實施他的下一步自殺計劃,就醉得倒在地上,幸好被人及時發現,撿回一條性命。
之后我對他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劍橋,這17年,起碼也是個著作等身的劍橋教授了,絕不會落到這般田地。”蕭乾神色凄厲,加重語氣說:“想那些干什么!我是中國人,就應該承受中國人的命運。”后來我想,假如他去了英國,我就不會有機會遇上他。
我們共歷磨難22載,直到1979年,我們才重見天日。
翻譯“天書”最難忘
1990年到1994年,我與蕭乾一起翻譯《尤利西斯》。那是我自從與他在一起以來感覺最有意思的一段。《尤利西斯》很難翻譯,這樣一本“天書”,對我們來說卻是長久以來對自己的補償。
我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用業余時間譯了好幾百萬字的文學作品,但沒有一部名著。另外,我從事日文的翻譯比較多,十年寒窗的英文專業沒怎么得到發揮。至于蕭乾,他的遺憾就更大了。有人說他是“《大公報》記者中最幸運的”,但這只是相對而言。他曾經被奪去了手中的筆。在不正常的歲月中,他的心臟和腎臟都出現了嚴重問題,再也不能出去闖蕩世界了。后來能寫的,也就只有回憶錄和短文。
我們兩個年齡加起來150歲的老人,像年輕人一樣煥發了熱情。在寓所門鈴旁我們貼了一張紙條:“疾病纏身,仍想工作;談話請短,約稿請莫。”每天早晨5點我們就起床,在各自的書桌前開始工作。開始時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連下樓的工夫都沒有,冬天常常是和衣而臥。
蕭乾曾評價我的翻譯:“是個講究一個零件也不丟的人,連原文里的虛詞都不放過。”我們流水線作業,我擔任草譯和注釋,做到“信”,蕭乾接棒做潤色,力求“達”和“雅”。我們規定每天至少翻譯一頁原文,譯不完就不睡覺。1994年譯本出來,文化界、讀者,甚至國家領導人對它的反應之強烈,超乎了出版社和我們兩位譯者的想象。
可是之后不到3年,蕭乾就因為心肌梗塞住進了北京醫院。在病房里,我安置了一張小木桌,我們仍舊翻譯和寫作,這樣多少也分散了他的痛苦。
他常常回顧自己的一生,感慨自己年少時文思泉涌,卻不夠勤奮,尤其是小說寫得太少。而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不論文學創作還是翻譯事業,他做出的成績,都不遜于前半生。
命中注定閑不下來
1999年2月,辦完蕭乾的喪事后,兒子蕭桐勸我赴美小住。我說:“我哪里走得開?你爸爸身后的事,10年也做不完。”之后的日子,比我預料的還要忙。首先,我與吳小如先生一起整理出一部45萬字的《微笑著離去——憶蕭乾》,后來,又幫助整理出版了蕭乾的《余墨文蹤》。之后又選取了蕭乾父子之間的通信幾十封,整理出版了《父子角——蕭氏家書》等。翻譯的活我也沒少干。《圣經故事》 《冬天里的故事》以及日本詩人池田大作的詩集等陸續出版。
我這個人命中注定閑不下來,我也會像蕭乾那樣,寫到拿不動筆的那一天。我現在已經87歲了,我的身體狀況還不錯,生活還能自理,不想請保姆,做家務對我是一種調劑——不能一直工作,眼睛需要休息。我也不想去養老院,那樣的話就不能自由地工作了。
很多人都覺得翻譯工作挺辛苦的,但我就是樂此不疲。對于游山玩水、看電影、看戲,我都沒有興趣,我就是喜歡翻譯、寫作。我對生活的要求很簡單。吃得好的人不一定就長壽,很多美食家都死得早。我覺得我能活到100歲,那樣的話也就13年了,在這期間我的事情都排滿了,時間太寶貴,我還有太多的活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