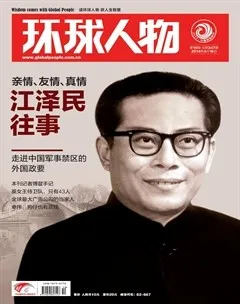校長的遺憾,更是教育的遺憾
“根叔”又上頭條了。3月31日,中組部宣布任免決定,被昵稱為“根叔”的李培根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在離任演講中,“根叔”列舉了擔任校長9年來的19個“遺憾”。令人矚目的是,只有4個是關于學科建設的,其他“遺憾”都關系到教育體制:教師與學生的距離沒有明顯縮短,大多數學生沒有脫離“教育生產線”的培養(yǎng)模式,沒能培養(yǎng)學生對過去和未來的責任,沒能維護好大學的獨立精神和自由表達,甚至向資金低頭,校園里多了官氣少了學氣……
種種“遺憾”,直切當前教育弊端,有些甚至措辭尖銳。一位官至副部級的大學校長,在國家人事任免的莊重場合,離任演講沒有官話套話,反而講了真話,只字不提成績,反而通篇說“如今徒有遺憾”。這樣的反躬自省,著實勇氣可嘉。
而且,從“仰天長嘆”“奈何不得”“卻無良策”等措辭中,可以感受到:“根叔”一定探索過、努力過,試圖改變這些狀況。這樣的勇于探索,也值得肯定。現場不少師生眼含熱淚,正是對“根叔”這兩方面勇氣的最好贊美。
但是,我們不用急著鼓掌,不妨反過來看,自從2010年在畢業(yè)典禮上侃侃而談“俯臥撐”“躲貓貓”“蟻族”而一炮走紅后,“根叔”有沒有拿出教育改革的具體舉措,有沒有落實某個改革計劃呢?很遺憾,似乎沒有。
所以,一位校長的離任“遺憾”,反映出迫切的現實困境——在任時誰都知道問題,但難以改變,離任后才敢說真話;在任時也許是明星校長,社會各界對其抱有極大期待,離任時發(fā)現其治校的變化并不大。
造成這種困境的根源何在?“根叔”也知道答案:“大學治理結構有缺陷。”說白了,就是校長的角色十分尷尬。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并未對黨委書記和校長的權責劃出清晰邊界,兩個“一把手”對峙現象時有發(fā)生。校長要在行政序列里對上負責,應對行政干預;又要在學術范疇里對師生負責,保障教授權利。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撕扯著大學校長。在行政權力和學術自由的拉鋸中,校長的作為空間能有多大呢?
要想改變高等教育的種種弊端,當務之急就要鏟除“校長官員化”的積弊,厘清大學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邊界。
不過,這也只是邁出第一步。造成這種困境的更大根源,在于整個社會對教育的功利心態(tài)。大學無法孤立于社會,高校是嵌套在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結構中的。我們呼吁大學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全社會的急功近利只能造就年紀輕輕的博士和老態(tài)龍鐘的兒童;我們呼吁大學去行政化,但在全社會都以行政級別作為評價標準時,取消行政級別,又會讓“裸奔”的大學無法和社會對接。
可以說,大學雖屬于教育領域,但只有各領域改革協調推進,處理好大學與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才能建立真正的大學。
除此之外,校長個人的擔當也是破解現實困境所必需的。近年來,人們耳熟能詳的校長大概只有兩位。“根叔”成名于敢言,創(chuàng)辦南方科技大學的朱清時校長成名于實干。當“根叔”以19個“遺憾”在這個春天給校長生涯畫上句號時,朱清時也將在今秋卸任校長,他理想中的“去行政化、校長負責、教授治校”的大學實現了嗎?“根叔”和朱清時,不約而同地留下遺憾的背影,這中間,有理想遇到冰冷現實的窘迫,有個人碰到制度高墻的無奈。
敢言者和實干者尚且如此,那些言必官話套話、行必循規(guī)蹈矩的校長,就可想而知了。當官頭頭是道,辦學不作為、亂作為,這些年來并不鮮見。校長個人的行政化和功利化,直接加劇一所大學的暮氣。相反,校長個人的智慧和勇氣,能推動一所大學的點滴進步。這種推動力,靠敢言不夠,靠實干也不夠,還得靠敢干。唯有敢干二字,才是教育家的擔當、改革者的氣魄。
放眼當今世界,1636年,美國還未建國,先有了哈佛大學;1810年,柏林大學建立,助推了德國強大。各國無不證明,“無大學則無大國”。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際,愿任內敢干的大學校長再多點,愿中國教育改革的遺憾再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