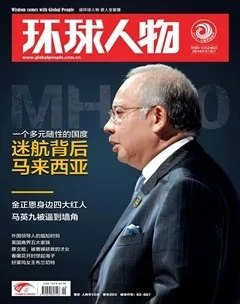北京不可能成為“小首都”

最近,保定將成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消息流傳開來,讓長期默默無聞的河北保定突然成了關注焦點。追溯歷史,“直隸”這個詞始于明朝,即直接隸屬于京師的地區,1928年才改省名為河北。曾是直隸省會的保定,始終是京津冀地區的中心城市之一,位于保定市內的直隸總督署仍在證明其昔日的輝煌。作為北京的“南大門”,保定的含義就是“永保大都安定”。到了今天,從地圖上看,河北就像一個粽子包裹著北京和天津,這兩個直轄市像兩顆耀眼的紅棗嵌在糯米里。
3月26日,河北省出臺《關于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意見》,其中對保定、廊坊、唐山等市在京津冀一體化中的功能定位、發展重點進行了初步規劃,將保定定位為“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業單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醫療養老等功能疏解的服務區”。對此,河北省發改委表示,目前河北只是根據各個城市的特點和功能定位編制方案,而政策能否落地,還要看北京、天津是否認可,更取決于國家大規劃的出臺。就京津冀一體化的走向是否明朗及未來趨勢,3月25日,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在廣東佛山舉行的“獅山論壇”上專訪了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李曉江。
“規劃不是算命”
上世紀80年代,李曉江大學畢業后參與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河北省唐山市的總體規劃。作為震后重建的城市,唐山當時被公認為規劃較好,而重工業的蓬勃發展,也令其一度成為渤海灣經濟圈的龍頭城市之一。而如今,唐山卻面臨著發展瓶頸,經濟轉型緩慢、城市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越來越嚴重。“規劃不是算命,無法預測過于長久的未來。我們只能對已有的經驗和能夠預見的發展趨勢做出判斷。”李曉江坦率地對記者說。在他看來,當時的規劃者已經盡可能做了開闊性、前瞻性的研究。“但當時我們沒有辦法判斷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后來20多年中會如此之快,也沒有辦法預見到中國會快速進入一個機動化的社會。”
李曉江回憶,當時他們設想的城市交通主要依靠自行車和公共交通,而事實上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的機動化進程一下加快了,私人小汽車迅速普及。“這個趨勢在西方國家都發生過,但當時我們認為中國不應該走這條路,應該以發展公交為主。實踐證明這種規律我們很難改變。”李曉江說。不過,他預計中國未來的城市交通還會回歸理性。“我們可以注意一下國際大都市,如紐約、倫敦、巴黎,在發展中都經歷過一個人人擁有小汽車的階段,但最后都回歸到更加合理的交通結構。我相信隨著人們消費觀念、生活方式的變化,中國目前的這種交通局面會逐漸改善的。”
另一個規劃項目則在經濟發展方面留下了更多的經驗。2003年至2005年,李曉江參與主持了建設部、廣東省政府組織的“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現在回過頭來看,李曉江認為有幾點是值得總結的:
“第一,在珠三角的產業發展模式上,我們當時就提出了產業升級和產業體系的構建,過去10年,珠三角地區從一個外延性的、以進口加工為主的結構,逐步轉向了一個自成體系、不斷完善的產業結構。第二,在產業布局上,我們當時做出了很重要的判斷,就是在珠三角的核心區不應再繼續發展污染型的企業,包括鋼鐵、石化等重型高消耗、高排放企業。第三,我們提出珠三角的城鎮化發展應該更加聚集。最后一點,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在珠三角的規劃中,提出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生態和綠色空間系統,為后來珠三角的綠道建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首都的基本功能無法疏解
環球人物雜志:最近的熱議話題是把保定打造成行政副中心。您認為北京的城市功能應該如何拆分,才能促進其良性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
李曉江:最終的政策還沒有明確,很多消息都屬于猜測。但這涉及首都職能的問題。我們在2003年開展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一直在探索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北京作為首都的基本功能是無法否定的,要把中央機關、各大高校、軍隊總部這些單位搬到河北,并不現實。
我們曾經做過研究,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是:聯邦制的國家幾乎都是“小首都”,比如美國華盛頓、加拿大渥太華、澳大利亞堪培拉,不承載經濟中心功能;但單一民族的大國首都卻都是經濟中心,比如法國巴黎、日本東京、俄羅斯莫斯科。因為單一民族的政權相對強勢,而聯邦制國家的政治是分權的,這種制度往往不允許其政治中心成為經濟中心,不允許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美國各州的州府都很小,但州內通常會有一個很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比如洛杉磯、芝加哥、紐約。所以我們最后論證的結果很清楚,要讓北京承載純粹的首都功能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集政治、文化、社會乃至經濟中心為一體的大城市。
環球人物雜志:北京的經濟功能與其他經濟中心城市有什么區別?
李曉江:當然有區別。北京作為經濟中心應該發展什么?重工業、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就不要發展了,比如鋼鐵、煤炭、汽車、啤酒這些都應該遷出去。北京應該作為經濟管理中心存在,政策制定的功能是一定要有的,這不可規避,也疏解不出去。
環球人物雜志:河北省《關于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意見》中,提出將保定打造為“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業單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醫療養老等功能疏解的服務區”,您怎么看這個定位?
李曉江: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首都的基本功能是不能疏解的。我認為,保定的規劃,應該著眼于工業和經濟配套功能。2008年,我們曾經與保定市政府和保定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出臺過一個《保定城市總體規劃》,將保定定位為:積極融入京津冀城市價值鏈體系,成為世界級城市密集地區——京津冀城鎮連綿帶的有機組成部分,建成華北內陸地區向沿海開放的橋頭堡,并繼續發揮生態屏障作用。它要成為承接京津項目擴散和科技成果轉化、以節能節水型企業為主的現代制造業基地,成為京津綠色農副產品加工供應基地,以及京南現代物流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等等。
環球人物雜志:京津冀地區的產業布局調整會有哪些好處?
李曉江:首先是改善環境。比如首鋼的搬遷,對北京環境的改善就有巨大幫助,因為周邊地區的空氣容量更大,人口相對稀少。其次,企業搬遷實際上也是重建,產業結構更合理,污染防治的水平也會提高。第三,在區域上有更加合理的布局,可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環球人物雜志:前不久還有一個熱議的話題,是讓“北京動物園批發市場”等外遷。
李曉江:北京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一方面整個城市的發展成本很高;另一方面,除了房價外,北京居民的生活成本在中國所有大城市里是最低的,因為政府補貼非常高。我算過一筆賬,在北京乘坐一次公交車,背后有政府3塊錢的補貼。這種相對低成本的運行導致了一些北京首都功能以外的衍生功能,甚至是一種寄生功能。像“官園批發市場”“動物園批發市場”這類產業,80%以上的人員和業務跟北京是沒有關系的,但它們借助了北京交通樞紐的地位和人口聚集的優勢,運行成本比較低。對于這些功能,我覺得完全可以換一個地方。
不能讓河北無路可走
環球人物雜志:普遍認為,河北省這些年一直在為京津,尤其是北京的發展做貢獻。
李曉江:這些年北京的發展確實很快,而反過來看,圍繞北京的河北省又太弱太慘,這種反差太大了。我經常說,北京天津干了河北的事,讓河北無路可走,最后不得不去發展污染最重、排放最大的產業,反過來又影響到北京天津。
環球人物雜志:京津冀地區跟長三角、珠三角相比,差距還比較大。
李曉江:確實。京津冀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高的太高,低的太低,體系完整性不如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就是兩座“炮樓”,自身發展很快,但周邊都是洼地,河北省“大樹底下不長草”“燈下黑”的效應很明顯。這需要一個過程來調整、培育。河北省為京津做貢獻沒問題,但不應該是單向的,如果河北為京津保住了一個好的生態環境,應該得到補償。
我曾經舉例,北京用了10年時間減少了1000萬噸的燃煤,幾乎用掉了全國所有的天然氣,北方地區大部分的天然氣都保證北京使用;但河北省10年之間增加了1億噸的燃煤,造成整個區域污染嚴重。過去北京煤改氣,以為改完環境就好了,最后發現沒有一個大的區域協同,還是照樣掉到霧霾陷阱里。河北的城市都圍在北京周邊,霧霾最嚴重的10個城市里河北占了7個,北京空氣怎么可能好?
河北有7000萬人口,整個京津冀地區的1億多人口必須是一個和諧、協調的發展。不能在北京感覺是個國際大都市,出去了感覺是個大農村。前些年國際上還炒作過中國“環首都貧困帶”的概念,就是因為北京與其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落差太大了。京津地區過去10年的發展證明,任何大城市,離開了區域發展都不能獨善其身。你擠占了別人的發展機會,最后你的發展也要受影響、付出代價。
環球人物雜志:對于京津冀地區的一體化,現在能否找到一個前瞻性的、可持續的發展方案?
李曉江:這只能是漸進的,因為中國發展太快、太急,任何事情都是有慣性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是有很長的距離。雖然科學發展觀已經講了10年,但很多領導甚至專業人員的思維仍然停留在10年前。中國一線城市20年前犯過的錯誤現在二、三線城市還在犯,明明看到國外的教訓,還是無法避免重復。
環球人物雜志:這種情況的根源是什么?
李曉江:根源還是我們的發展思路:把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的目標,結果一定是失衡的。土地財政也好,GDP導向也好,發展模式不從根本上去改變,思維定式和路徑依賴就一定會繼續。一個社會應該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成熟、淡定,但經過30年的發展,我們還看不到這種跡象。一直說GDP能夠保證就業,但不同產業的發展對就業的促進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事實上,這幾年投資帶動的就業比例已經很低了,而調整產業結構、發展服務業、完善社會治理都是穩定就業很重要的方面。我認為,單一的就經濟論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頭了。
環球人物雜志:國外的城市發展模式有沒有適合中國的?
李曉江:沒有。可能我們在某一個方面和某個國家有點相像,但中國就是中國。其實現在要摸索我們自己的發展模式并不難,因為各種問題已經非常明顯,該怎么做是非常清楚的。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就是怎么才能讓進步的過程更快一點,花費的時間更短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