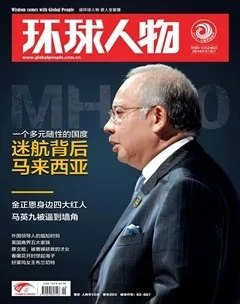春暖花開時想起海子


2014年3月26日,是天才詩人海子辭世25周年的紀念日,在這一天,各地舉行了各種形式、規模與層次的海子紀念活動。實際上,3月24日也恰逢海子誕辰50周年,數天前就有不少詩人、藝術家舉行聚會,以朗誦、表演海子詩歌的方式來表達對這位早逝詩歌天才的懷念與推崇之情。海子生前的寂寞與死后的哀榮形成了極端戲劇性的反差,足以令人玩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所有的中國當代詩人中,就知名度及受人們喜愛的程度而言,海子無疑是獨占鰲頭、笑傲群雄的。海子與喜愛他的讀者一道,構成了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的一個奇觀,值得我們分析與探究。
為喝醉后說初戀女友壞話而自責
25年前,在1989年春天的一股寒流中,時年25歲的詩人海子在河北秦皇島的山海關以極為悲壯的方式離開了人世,他把自己年輕的軀體祭獻給了朝他迎面隆隆駛來的一列火車。我們可以隱喻性地把火車理解為他所處的那個開始轉型的時代——當時代的列車無情駛過時,不合時宜的天才詩人海子清醒而自覺地選擇死亡,以此表達他對即將來臨的另一個時代(追求物質欲望的20世紀90年代)的勇敢拒絕與內在否定。
海子去世那一年,我還待在老家江西井岡山區,年少懵懂,但對詩歌卻相當著迷。記得在那一年的五六月份,我從當時影響很大的《詩歌報》上看到了青年詩人海子自殺的消息,非常震驚。在屋里有些黯淡的燈光下,我第一次讀到海子的兩首詩,記得一首詩的標題為《秋》,另一首詩的標題為《死亡之詩》(之二)。當時一個強烈的感覺是,這位名叫“海子”的詩人(我當時對海子的原名及生平并無了解),對死亡有一種奇特的向往,但他對親情又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比如在《死亡之詩》(之二)一詩中,詩人表達了對死亡的審美想象與情感,而在該詩的結尾如此寫道:“但是,不要告訴我/扶著木頭,正在干草上晾衣的/母親”。
這種親情不是詩人在作品中的虛構式表達。現實生活中,海子是個對父母、對兄弟姐妹非常關心的人。在海子生前好友、著名詩人西川的文章中,以及海子二弟查曙明不久前為紀念海子去世25周年所寫的《懷念海子》一文中,都提及過海子的一件往事,1986年春節期間,海子花幾百元錢給家里買了一臺黑白電視。當時電視在農村是稀罕物,幾百元也是一筆巨款。海子嗜書如命,稍有余錢就用來買書了,可卻把辛苦攢下的稿費全給了家里人,可見他是一個很有責任感、對父母很有孝心的人。
2013年11月,我在安徽詩人韓慶成陪同下,專門去海子故鄉——安徽安慶懷寧縣高河鎮查灣,看望他的父母及家人。在海子故居的書房里,我還親眼見到了這臺傳說中的黑白電視機。
在我的印象中,海子是個內心非常孤獨的青年詩人,他的詩歌才華在他生前完全沒有被人們所認知。在北京詩人圈子內,海子還常常遭到同行及前輩們的調侃乃至嘲諷。1988年暑假,24歲的海子專門去了一趟成都,拜訪幾位成名的青年詩人,想從他們那里得到鼓勵與肯定,結果卻失望而歸。海子還寄希望能從普通讀者中尋求知音,有一次,他興沖沖地拿出一首新作去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旁邊的一家酒館,老板也算是海子的朋友。他對老板說,愿意朗誦自己的新作,代價是一杯啤酒。結果老板立即回應:啤酒你可以喝,但詩就不要朗誦了……可見,海子完全找不到知音。他太孤獨了,那種內心的凄涼從他《在昌平的孤獨》《海子小夜曲》等作品中即可看出。他寫道:“如今只剩下我一個/只有我一個雙膝如木/只有我一個支起了耳朵……”
海子還是一個非常善良、極重情義的人。據海子在法大工作時的同事熊繼寧教授、詩人臥夫等人講述,海子在自殺前,曾見過他的初戀女友一面,她對海子極為冷漠。海子回到學校后喝醉了,第二天醒來非常后悔,認為自己可能在同事面前說了初戀女友的壞話,自責到痛心徹骨的地步。
沒想到海子的力量有這么大
“對于逝者而言,他們對于世界的記憶永遠留在了去世之前,他們的青春與理想定格在那一瞬間;而對于生者,懷念是時間給的空氣,無時無刻不在周圍徘徊、縈繞。”海子侄子查銳的話,道出了這25年來海子及其詩歌的境遇。
海子剛去世那幾年,對他的懷念基本上只局限于詩歌圈內。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隨著海子詩歌的傳播日趨廣泛,加入懷念者行列的人越來越多。每年都有大批文學愛好者慕名去安徽懷寧探訪海子故居,其中甚至有不少外國人。更難能可貴的是,一些虔誠的志愿者常年執著地守護在海子故居。
在海子的母校——北京大學,從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每年3月26日前后都會舉辦“未名詩歌節”。其中的海子紀念專場上,總是會有一個學生主動走上舞臺,帶頭領誦海子的《祖國,或以夢為馬》《黑夜的獻詩》等經典。2009年3月26日晚,海子去世20周年紀念活動在北大百年講堂多功能廳舉行,因為來參加活動的人太多,許多“粉絲”都被攔在門外,我和幾位國內的知名詩人因為遲到也不得入內,但大家待在外面不肯離去。這時,突然從里面傳出一陣齊整的、震耳欲聾的集體朗誦《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的聲音——連我們這些詩歌圈的人也沒想到,海子詩歌的能量有如此巨大。
對海子的懷念還有更高層級的形式,比如搜集、整理海子的詩歌,樹才等一大批詩人為海子創作紀念性詩篇。在我所讀到的海子題材作品中,女詩人梅爾的《十個海子》寫得非常出彩,真摯的情感與優美的想象結合得水乳交融,結尾一節是這樣的:
后來年年花開
花蕊里生長著十個海子
年年的花香
釀成了詩的酒
醉倒了一茬又一茬的青春
是的,正因為海子的詩歌能夠感染與打動“一茬又一茬的青春”,所以才有這么多人懷念他,熱愛他。這也能夠解釋為什么每年有那么多的年輕人和不那么年輕的人,不分季節,不遠萬里前往偏僻的海子故鄉參觀訪問,尋覓海子在故鄉所留下的童年足跡與青春蹤影。
死去詩人壓得活著的詩人抬不起頭?
前幾年,曾有一位批評家朋友開玩笑地對我說:海子這位死去的詩人壓得一群活著的詩人抬不起頭來。此話在較大程度上凸顯出當下詩壇大詩人困乏的尷尬事實。而從另一個角度上,也恰恰有力印證了海子是一位貨真價實的天才。因為天才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的確,相對于海子有爭議的長詩創作而言,他的抒情短詩幾乎獲得了普遍性的高度贊譽。他具有極為出色的抒情才能,其創作天賦在20世紀新詩史上可謂孤峰突起,能與其比肩者寥若星辰。這是不少人的觀點。所以,上世紀90年代末,我的碩士論文題目就是《海子論》,因為我認定海子是一位難以復制的天才。著名詩評家、海子研究專家燎原下大功夫撰寫《海子評傳》一書,也是對海子文學史地位極為重視的表現。
至于當下中國詩人的邊緣化處境,我想,并不是這個時代沒有好詩歌,只是屬于詩歌的黃金時代早已結束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多少年輕的中國詩人從詩歌的精神世界跌回現實的塵埃里。但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新詩在時間的感召下終于開始孕育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