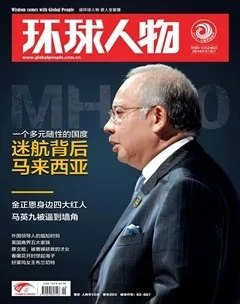蔡文姬,被曹操拯救的才女




歷史上,蔡文姬以才女著稱,“博學而有才辯,又妙于音律。”奈何天妒紅顏,一生命途多舛。所幸,她的才華為亂世梟雄曹操所賞識,讓“文姬歸漢”,為我們演繹了流傳千古的文化傳奇。
父親是一代大儒
在河南當地,至今流傳著關于蔡文姬出生的傳說。
蔡文姬的母親有一天晚上夢見一個托缽僧送她一顆蘭花籽,她因此懷孕,生下了這個像蘭花般美麗的女兒。
給新生兒過百歲那天,正趕上重陽節,蔡家十分熱鬧,按照風俗,要讓孩子“抓前程”,廳堂的桌上擺了筆硯書帖、刀弓箭囊、菱花銅鏡、白銀商幌等許多東西,家人們圍攏過來,想看看蔡文姬的緣分。只見她好奇地看著桌上的物品,之后伸出胖乎乎的小手,一把抓住了一支毛筆,這讓她的父親激動不已。
蔡文姬的父親,就是東漢末年極負盛名的學壇領袖蔡邕,他經史、天文、數學、繪畫無所不通,尤其擅長辭賦,堪稱一代宗師。可以說,這是個無可挑剔的老師,沒有人比他更全能,也沒有人比他更盡心。
蔡邕對女兒的教育十分全面,沒有因為是女孩就只讓她學女紅類的東西,而是讓她和男孩一樣,背誦古文,研讀經史。蔡文姬深深地被奧妙無窮的文化所吸引,絲毫不覺得古文經史枯燥無味,她甚至將班昭作為榜樣,希望也能編撰書籍,留名青史。
蔡邕對音樂很有研究,會作曲,古琴曲《河間雜曲》《蔡氏五弄》都是他的作品。他還善于制作樂器,著名的“柯亭笛”和“焦尾琴”都出自他的手中。其中,“焦尾”與齊桓公的“號鐘”、楚莊公的“繞梁”、司馬相如的“綠綺”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名琴。蔡文姬從小受到父親的熏陶,耳濡目染間,也培養出了非凡的音樂功力。
據劉昭《幼童傳》記載,有一天晚上,蔡邕在家中彈琴,忽然“啪”的一聲,一根琴弦斷了。正在一邊玩耍的蔡文姬說:“父親,是第二弦斷了吧。”蔡邕很驚異,心想也許是被女兒偶然猜到了。于是操起琴繼續彈奏,故意弄斷了第四根弦,問她說:“這次是第幾弦?”蔡文姬回答說:“第四弦。”蔡邕一下子服了女兒的音樂天賦,要知道,那一年,蔡文姬才6歲。從此,他用心地教女兒學琴,兩年后,便把自己所珍愛的“焦尾”傳給了她。
蔡邕的書法成就也很高,后世的梁武帝稱贊說:“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流傳下來的《熹平石經》《曹娥碑》等,皆是蔡邕的代表作。蔡文姬得到了父親書法的真傳,可惜她的書法真跡今天已無緣得見,不過北宋大書法家黃庭堅曾見過蔡文姬所寫的《胡笳十八拍》的殘片,為此還留下了一段題跋:“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余兩句,亦似斯人身世邪。”以黃庭堅的眼光,都能給出“極可觀”的評語,足以想象蔡文姬書法的精彩。
事實上,蔡文姬在我國書法藝術的傳承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她,把蔡邕書法的真諦傳授給了鐘繇,鐘繇又傳給了衛夫人,而衛夫人則是“書圣”王羲之的啟蒙老師。
蔡文姬是幸運的,因為有這樣一個超級老爸,她也被打造成遠近聞名的才女。16歲那年,她遠嫁河東(今山西夏縣)衛家。衛家是名門大族,她的丈夫衛仲道也是個才子,小夫妻恩恩愛愛。可惜好景不長,結婚不到一年,衛仲道便因咯血而死。更糟糕的是,公婆十分迷信,以為是蔡文姬克死丈夫,因而對她百般嫌棄。心高氣傲的蔡文姬哪里受得了這種白眼,不顧父親的反對,憤而回家。
這本來也沒什么,有父親的庇護,相信蔡文姬的日子也差不到哪里去。只是世事難料,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駕崩,董卓把持了朝政,下令征召蔡邕為官。他對蔡邕“甚見敬重”,3天升了3次官。或許正是這種禮遇,讓蔡邕對董卓有了知遇之恩,以致在董卓被殺后,他流露出了同情之意,司徒王允大怒,立即將他逮捕下獄。蔡邕表示“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即愿意接受刺面砍腳的懲罰,希望能完成撰修漢史的夙愿。可惜掌權者不同意,蔡邕最終還是死在獄中,享年60歲。
在匈奴的12年
短短幾年間,丈夫死了,父親也慘死獄中,蔡文姬一下子成了亂世中無依無靠的飄萍柳絮。
興平二年(195年),董卓舊部叛亂,漢獻帝請求南匈奴出兵。戰火一直蔓延到蔡文姬的家鄉,結果她遭遇了人生最為殘酷的一場劫難,和許多婦女一起被胡羌鐵騎帶到了南匈奴。
那是怎樣的一番場景呢?蔡文姬所作的《悲憤詩》中如此記載:“平上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中原弱民無力抵擋胡羌鐵騎,戰爭打到哪兒,燒殺擄掠就發生在哪兒。胡羌騎兵的戰馬旁,掛滿了中原男子的頭顱;馬后,則是被俘虜的婦女。蔡文姬一個嬌美的女子,被一群野蠻的胡人擄去蠻荒之地,一路上不知受盡多少屈辱,求死不能,只得茍延殘喘。這些被掠奪而來的人,都成為了匈奴人的奴隸,蔡文姬因為美貌,被獻給了南匈奴左賢王。
這或許是個不錯的結果,有人推測蔡文姬成了左賢王的姬妾,甚至正妃,雖然沒有王昭君出塞那樣風光,但畢竟可以生計無憂。在眾多說法中,恐怕要數郭沫若在歷史劇《蔡文姬》中想象得最為浪漫了。劇中描述蔡文姬在被擄往南匈奴的途中,遇上了年輕多情的左賢王。左賢王被蔡文姬的才情和容貌所吸引,蔡文姬則感于左賢王的多情重義,兩人遂恩愛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這不過是美好的想象罷了,事實并非如此。《后漢書》記述這段歷史時,只是說蔡文姬“為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她成了左賢王的人,在長達12年的時間里,雖然為左賢王生了兩個兒子,但并沒有姬妾身份,不過是個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奴隸。
這是怎樣的一種煎熬。作為中原文豪蔡邕的女兒,擁有令人羨慕的才華和美貌,卻要忍受背井離鄉的孤零和淪為奴隸的屈辱,即使萬般不愿,又能怎樣?大漠荒涼,黃沙滔滔,沒有人可以訴說心中的凄苦,蔡文姬只能把內心的凄涼都化于筆端,寫了下來:“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欲不同兮誰可與語!”
可即便生活再屈辱,蔡文姬都沒有想過死。她說自己并非貪生怕死,也不是不知廉恥與氣節,只是不想死在異國他鄉,就是帶著孤魂枯骨也要回家。正是這個信念,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支撐。
隨著中原政治形勢的變化,蔡文姬也等來了希望。曹操平定北方后,以丞相的身份“挾天子以令諸侯”。建安十三年(208年),他聞知蔡文姬流落南匈奴,深感憐惜。當年曹操在洛陽為官時,十分仰慕蔡邕的學識,經常登門求教,與蔡邕結為忘年之交。那時見到的蔡文姬還小,現在知道了她的下落,曹操立刻派周近(一說董祀)為使者,攜帶黃金千兩,白璧一雙,到胡地去贖蔡文姬回來。
能擺脫屈辱的生活,回到日夜思念的中原故土,蔡文姬十分高興;但要離開兩個天真無邪的兒子,她又覺得肝腸寸斷,寸步難行。在漢使的催促中,她最終還是登車而去。車聲轔轔,大漠漸行漸遠,蔡文姬百感交集,她借胡笳的音律,將那種無以復加的痛苦,寫成了一首千古絕響——《胡笳十八拍》,也為自己的異域生活畫上了一個句號。
如同瘋了般直奔相府
回到故鄉陳留圉鎮時,蔡文姬目之所及,只有斷壁殘垣和童年生活的回憶。她一個人孤苦伶仃,生活異常艱難。曹操得知她的生活狀況,又派人把她接回鄴城,并親自做主,將她嫁給了屯田都尉董祀。
董祀20多歲,長得一表人才,更難得的是,他通書史,深諳音律,有著相當高的藝術修養。這對經歷過坎坷的蔡文姬來說,簡直是打燈籠也找不著的如意郎君。不過她心里也清楚,董祀答應這門親事,多半是抹不過曹丞相的面子。
果然,新的婚姻并不如想象中和諧美好,董祀對蔡文姬平平淡淡,再加上年齡的差距,特別是蔡文姬飽經離亂憂傷,內心已十分疲倦,加之思念遠在大漠的兩個兒子,時常神思恍惚,全然沒有了憧憬愛情、體味幸福的心思。
即便如此,坎坷的命運依然與蔡文姬如影隨形。在她婚后的第二年,一個新的噩耗突然傳來,董祀犯了罪,被處以死刑,就要被執行。眼見這最后的依靠也要轟然倒塌,什么大家閨秀的風范,什么矜持的臉面,蔡文姬全顧不得了,如同瘋了般直奔相府。
相府里,曹操正在大宴賓客,請的都是公卿大臣、名流學士。聽到門吏稟報,他立刻知道了蔡文姬的來意,于是笑著對客人們說:“想必在座的不少人都和蔡邕相識,她的女兒在外流落多年,這次回來了。今天讓她來跟大家見見面,怎么樣?”
不一會兒,蔡文姬被帶了進來,披頭散發,赤著雙腳,就像一個風餐露宿的流浪者。她跪在曹操面前,無限哀婉地說:“我被胡人劫掠到草原荒漠之中12年,幸而得丞相顧念昔日與我父親的情誼,讓我回到了中原,又為我做主嫁給了現在的丈夫。現在他犯罪當死,本無可非議,然而那將讓我再次孤獨地留存世間,恐怕也不是丞相把我從大漠贖回的本意。今天我來替丈夫請罪,看在小女可憐的份上,請您饒他一命。”
她的嗓音悠揚清脆,每句話都說得十分傷心。座上的好些人原來是蔡邕的朋友,聽到他女兒悲慘的故事,看到眼前她那種憂傷的神情,都不禁為之動容,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淚。
曹操聽完她的申訴,問道:“你說的情形的確值得同情,但是判罪的文書已經發出去了,有什么辦法呢?”
蔡文姬哀求說:“您馬廄里的駿馬成千上萬,手下的武士多得像樹林,難道會吝嗇一匹駿馬,不能去救一個垂死的性命嗎?”
曹操嘆了一口氣,親自簽署了一道赦免令,派一名騎兵追回了文書,赦免了董祀的死罪。
時值隆冬時節,曹操看到蔡文姬連雙鞋子都沒穿,心中大為不忍,連忙命人取過頭巾鞋襪為她換上,并且讓她在董祀未歸來之前,留居在自己家中。
早年曹操在蔡邕家中,曾見到過不少珍貴的書籍。有一天,他問蔡文姬:“聽說夫人家原來藏書極多,現在還保存著嗎?”蔡文姬回答說:“當年我父親藏書有4000余卷,可是經過戰亂,顛沛流離,都已經散失了。”曹操十分失望,連道可惜。蔡文姬說:“不過我還能背誦400來篇。”曹操轉憂為喜,說:“我想派10個書吏到夫人家,讓他們把你背出來的文章記下如何?”蔡文姬說:“男女有別,授受不親,您只需要賜給我紙和筆,無論要真書還是篆草,我都可以寫。”果然,蔡文姬將所記憶的數百篇文章全部默寫下來,“文無遺誤”。曹操見了,非常滿意。蔡文姬此后便受曹操之命,一直整理、續寫先父書籍和遺著。
董祀被蔡文姬從死亡線上救了回來,也十分感念妻子的恩德,對她的感情有了180度的大轉彎。夫妻二人看透了世事,溯洛水而上,居住在風景秀麗、林木繁茂的秦嶺山麓。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秋,曹操征蜀路過這里時,還特地前去探望。
三篇作品奠定文學地位
蔡文姬一生命運坎坷,在歷史、音樂、書法、文學上有很大成就。然而遺憾的是,她的詩作僅流傳下來3首,即《胡笳十八拍》、五言體與楚辭體《悲憤詩》各一首。不過僅這3首詩,就足以奠定她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胡笳十八拍》原載于北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卷五十九,是一篇長達1297字的敘事詩,也是蔡文姬最為著名的作品,全詩一共有18段。在突厥語中,稱“首”為“拍”,十八拍即十八首之意。因為該詩是蔡文姬有感于胡笳的哀聲而作,所以名為《胡笳十八拍》或《胡笳鳴》。
胡笳是漢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種管樂器,其音悲涼。至于“胡笳”后來演變成“琴曲”,則得益于蔡文姬的丈夫董祀,唐代詩人劉商在《胡笳曲序》中說:“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蘆葉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為十八拍。”也就是說,《胡笳十八拍》經過董祀的改編,由胡地的笳曲,變成了中原人更為熟悉的琴曲,因而得以廣泛流傳。
《胡笳十八拍》以憂傷的曲調、反復的節拍,描述了一種撕心裂肺的絕望鄉情,感情奔放,語言熾熱,感人至深。唐代詩人李頎寫道:“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郭沫若評價說:“這是自屈原《離騷》以來最值得欣賞的長篇抒情詩”。
蔡文姬的另兩首作品《悲憤詩》,載于《后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全詩以作者親身經歷為線索,貫穿被擄入胡、別兒歸國、還鄉再嫁三個重要情節,概括了10多年痛苦離亂的生活,猶如一幅血淚繪成的歷史畫卷。這是我國第一首自傳體長篇五言敘事詩,因而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歷代詩人和評論家對《悲憤詩》的評價很高,清代沈德潛評價此詩:“激昂酸楚,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在東漢人中,力量最大。”的確,這首詩真實再現了東漢末年動亂的社會面貌和個體的悲慘遭遇,可謂字字血,聲聲淚,具有史詩般的氣勢和強烈的悲劇色彩。在藝術手法上,它繼承并發揚了漢樂府以敘事來抒情,通過描述個人經歷以反映現實的寫作方法,成為文人敘事詩的里程碑。同時,這首詩特別注重心理描寫,人物心理活動寫得既細膩又真實,具有十分動人的藝術感染力,讓人不忍卒讀。
毋庸諱言,蔡文姬能創作出《胡笳十八拍》《悲憤詩》這樣既具有高度思想性又具有高超藝術性,讀來催人淚下的上乘之作,最重要的是得力于她所經歷的人生苦難,“感傷離亂,追懷悲憤”,這種苦難凈化了生命之外的所有東西,留下的只有對命運的控訴與不屈吶喊。
蔡文姬,一代博學多才的曠世奇女,命運如此坎坷,經歷如此凄涼,她的一生仿佛都是痛苦的象征。命運對她何其不公,而不公的命運卻也為她帶來了豐富的人生體驗。倘若沒有這樣的苦難,怎么會給我們留下如此動人心魄的偉大詩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