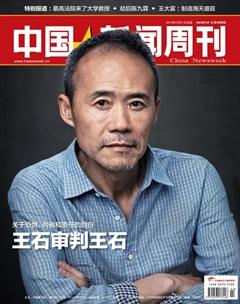歷史的回擊
什洛莫·本·阿米
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之時,勝利者們志得意滿,因為他們認定,自己必然會取得勝利。今天,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行動證明,這種觀點是多么地牽強附會。
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的著作《歷史終結點和最后一個人》反映了西方的主流觀點,書中認定,人類社會文化進步的終點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換而言之,基督教末世論變成了世俗歷史的先決條件。
然而,歷史的變化無常其實并不是什么新鮮事。黑格爾和馬克思就曾經堅信同樣的觀點。1842年,歷史學家托馬斯·阿諾德帶著典型的維多利亞式的洋洋得意,宣告維多利亞女王所統治的王國“清楚地昭示了歷史長河的完滿”。無論倡導實現某種絕對理念,還是推崇某個階級專政,事實證明,所有這些歷史先知們的預言都距離真實的歷史距離尚遠。
西方冷戰勝利之后不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和民族部落主義在“后歷史時代”的歐洲核心地區的回歸,有力地質疑了“歷史終結”的概念。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巴爾干戰爭、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血腥的阿拉伯起義,以及在全球經濟危機中暴露出來的西方資本主義的道德的和系統性的缺陷,無不進一步削弱了上述理念。
但是,或許只有俄羅斯和中國才能最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歷史并沒有改變。
俄羅斯則和車臣爆發的兩次戰爭、2008年的格魯吉亞戰爭抑或是目前出兵烏克蘭,都是不遺余力地恢復其昔日大陸帝國的威嚴。普京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針對克里米亞、甚至不僅僅是針對烏克蘭——其目標是扭轉被他稱之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悲劇”的蘇聯解體。
因此,普京正在挑戰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最偉大的成就:結束歐洲分裂和建立受西方影響的自由國度。而且,與處于敘利亞和伊朗的斗爭中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不同,普京堅守紅線,寸步不讓,那就是:西方不能爭奪前蘇聯的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而北約東擴也決不被允許。
此外,普京任由種族民族主義成為其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并以克里米亞講俄語的多數民眾為借口來讓自己的冒險行動合理化。
戰后簽訂的《凡爾賽條約》為限制德國國力而建立了許多小國,歷史學家AJP·泰勒在其1961年飽受爭議的二戰起源研究中為希特勒占領這些小國的決策辯護——泰勒稱一戰戰勝國實行的是“公開邀請德國擴張”的策略。我們也可以同樣評論今天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對俄羅斯的致命的吸引力。
當然,沒有人希望歐洲再次爆發戰爭。但是普京的行動以及奧巴馬失敗的外交政策,可能促使俄羅斯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動來削減自己過往的政治損失。畢竟,奧巴馬的全套外交政策計劃——與伊朗簽署核協議、促成以巴和平協議、與日漸疏遠的中東盟友實現和解、美國的戰略中心向亞洲轉移——現在都取決于他制服普京的能力。
而中國的角色是一個多極世界的另一個焦點。中國認為,美國的行為已經一再證明,國力才是國際事務中達成各種原則的最終的決定性因素。
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在東德的成長經歷應該讓她對普京的思想具有特別敏銳的洞察力——她把俄羅斯領導人的所作所為形容為權力政治指導下的脫離現實之舉。
然而,一直活在幻想當中的其實是歐洲:夢想著“后歷史” 時代軍事力量已經無關緊要,經濟援助可以馴服民族主義勢力,而且領導人都是彬彬有禮的守法的紳士和淑女。
歐洲人真心相信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博弈已經于1991年落下了帷幕。而普京告訴我們,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僅僅是中場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