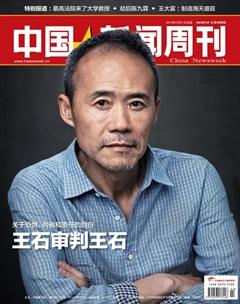“雜交”的一代
蘇潔
馮侖:“他做的比唱的好”
(萬通控股董事長,王石20年的朋友)
1993年,馮侖第一次見到王石。當時馮侖的萬通公司剛掘到了第一桶金,六個合伙人意氣風發,以馮侖為代表到深圳向領著萬科走上正軌的王石“取經”。王石辦公室里,馮侖大談熱血青年們的理想。王石潑了盆冷水,“不可能,你們將來早晚會碰到利益沖突”。這之后,二人并無太多聯系。
三年后,萬通發生了一些變化。有的合伙人離開了,公司業務遇到了危機和調整。馮侖再次找到了王石,聊起了當年的問題,聊起了現狀,找到了很多共同語言,最后成了朋友。一做十多年,兩位企業家惺惺相惜。
馮侖說,王石當年做的最正確的一個決定,就是不當老板。“為什么呢?在那一代的企業家和創業者中,很少自己創業不當老板的,創業的目的就是自己當老板,王石是唯一的例外。這個本身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萬科是他一手創建的,他追求的卻是職業經理人的定位。由于他不當老板,結果他跟我們走的路子和遇到的問題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恐怕也是萬科為什么能超級成功的秘密之一。”
馮侖贊嘆王石能夠堅持讓萬科走專業化道路,也贊賞王石的為人。2008年,王石“捐款門”事件發生后,網上一片謾罵之聲。馮侖是少數幾個站出來為王石說話的人。“王石是一個真君子,他做的永遠比唱的好。”
馮侖說自己有個“學先進的毛病”,年輕時候曾經給全國先進模范寫信學習,如今王石也成了他學習的“先進典型”。互聯網興起的時候,有點蒙的馮侖和王石等人到硅谷考察,回國后王石發狠說“弄不懂互聯網他就辭職”。結果王石到底把萬科搬到了網上,自己也成了超級網蟲。一群朋友出去滑雪,晚上累得腰酸背痛,躺倒就睡,只有王石一個人還在那上網。
“王石起初寫作是不太行的,但他勤奮,堅持天天寫,現在寫作已經成了他的一個強項;他漸漸能寫文章,現在寫書也不在話下。”馮侖贊嘆王石的堅持。王石每天大量閱讀,并且樂于跨界學習。每次到北京,都會和馮侖找不同領域的朋友聊天,了解專業知識。
馮侖說,王石的成功還沒有到頭,他還有空間。
曲向東:“在一個群體里他一定要當老大”
(中央電視臺前主持人,重走玄奘路的發起和參與者,王石的朋友)
2006年,王石和朋友重走玄奘路。開車經過烏魯木齊,剛好趕上當地穆斯林的開齋節。結束了一個月齋戒的人們祈禱、聯歡,街市恢復了平日的熱鬧。一路都是穆斯林的地域,王石突然說他不喝酒了,戒了一個月。“以前走戈壁的時候,每次休息,他都自己先喝瓶啤酒。”曲向東說,王石雖然不嗜酒,但有喝點的習慣。
一路到印度,王石真的沒喝。從印度回北京,王石說“到年底也不喝了”。后來一年沒喝,之后酒戒又延長到了三年。“他就是這么個人,不輕易承諾,承諾了就一定做到。也不是說戒酒為了健康,就為了過一種有節制的生活。”曲向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之后的一些場合中,王石也談到了那次戒酒的起緣。“穆斯林一個月齋戒節省的錢財,是給寺院救濟貧窮人的,這一點體會非常深刻。我覺得齋戒的意義,尤其是對中國富裕起來的一代人,是非常有啟發的。”
此時的王石,和十年前曲向東初次見到的那個人,已經很不一樣了。十年前,曲向東在中央電視臺做財經記者,第一次采訪王石,是關于萬科的股權紛爭。那時的王石和萬科處于各種漩渦中,“能看到他的焦慮。在萬科一線,對于萬科的前途,是一種千頭萬緒的焦慮感。”
這種感覺并未持續太久。2003年,王石登珠峰回來,兩人再次碰面。曲向東看著王石,還是那個黑瘦模樣,“在談判的時候,遇到僵局,會看著談判對手。看他的時候就在想,我已經到了珠峰頂上,看咱們誰能扛。”王石對曲向東說,他忽然感覺王石變得很強大。

珠峰過后,王石開始更多的冒險,重走玄奘路是其中之一。原本因為日程沒排開,王石對這次漫長的計劃有點猶豫。曲向東去杭州出差,偶遇王石,又聊到這個計劃。800里流沙、大漠、孤煙、無人區,兩人越聊越起勁。
“還是玄奘當年西行的地貌,到時候把大家的手機都沒收了,體驗玄奘當年的感覺。”曲向東半開玩笑。“你真敢收手機?你敢收我就走!”王石回應。
結果就真走了,走了40天。雖開車隨行,王石卻天天負重背著個包,像個苦行僧。同伴學樣,也紛紛背上。誰知第二天,王石開始背兩個包。“他的性格有點硬,像石頭一樣。在一個群體里一定要當老大。”
石頭一樣的王石去了國外,好像逐漸“軟化了”“可愛了”。“以前聊天,遇到不同意的觀點,他一定會當場反駁。現在的他像個學者,更包容了。好像馬上能從你的角度考慮問題。”
曲向東說,曾經的王石對東方文化多少有些悲觀。“現在有些改變,可能真的要走出去,才會感覺到骨子里的東方,以及那種文化的溫暖”。
全忠:他需要職場的“反對派”
(前《萬科周刊》主編)
王石屬虎。早年的他,被萬科員工私下叫做“王老虎”。脾氣大,說話愛用反問。80年代流行書桌上放塊玻璃板,底下壓照片的那種。王石桌上的玻璃板,都被拍碎過,無一幸免。他還曾一怒之下拿茶杯砸過萬科的一個副總,沒砸著,杯子磕破了。
那時候萬科還沒搬家,在深圳特區一棟改造的五層樓工業廠房辦公,條件一般。下班后,王石常待在辦公室不走,看書或者處理未完的業務。偶爾下面轉轉,看到還在加班的員工,會請他們到樓下飯館吃晚飯。旁邊有好的餐廳,有簽單權的王石也不去,自掏腰包去小飯館,花60塊錢請幾個人吃頓飯。房地產公司開發布會,別家給媒體“紅包”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可跑萬科的記者都知道,分文別指望。
“有人跑來問我,萬科老總王石裝修房子,還要借錢裝,你信嗎?我說我信。” 全忠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人們用廣東話講,說王石‘孤寒,就是吝嗇。但員工畏懼他,也服他。”
王石的自律能力驚人。創業初期,王石有一輛老式奔馳,毛病不少,車里空調常“罷工”。王石的司機天天開著接送老總,碰上其他房地產公司的同行,自己都不好意思。可王石就是不換車。“他說他要是換了,底下副總也都跟著換。”
1998年,萬科凈資產20億,王石的年薪是60萬。“副總們說,老王也不把自己的工資定高點,搞得我們最多也就能拿59萬啊。老王說,我何嘗不想定高,但萬科就這么點規模,拿多了對股東不好交代。”
有人說他摳,有人說他怪,但“王老虎”的做事風格,卻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一批萬科人。“現在回憶起來,那真是理想主義旗幟飄揚的年代。”
全忠初到《萬科周刊》,曾經寫過一篇經濟評論。評論發表后,突然有一天,接到王石打來的直線電話,一上午就打了三次。第一次,表示覺得評論不錯;第二次,鼓勵他再寫一篇續評;第三次,給他推薦了幾篇經濟評論。全忠回家跟太太說,這個老總感覺不太一樣。
那時候全忠剛從國企出來,深知該如何與老總保持“流暢溝通”。王石卻不喜歡,把全忠叫過來。“在你之前,萬科周刊經歷了三任主編,都是北大出來的,我說東,他們說西。跟你溝通,完全沒問題。但我不喜歡你這種風格,這樣說明你沒有自己的思考。”王石說,他需要職場的“反對派”。
王石看起來很矛盾。脾氣大,卻能容忍“反對派”;自律性強、規矩多,卻總能打破常規思維。
1998年,時任總理朱镕基到深圳考察。作為房地產企業代表,王石沒有匯報萬科的業績、未來宏圖,而是匯報了1994年前后,萬科交稅情況的變化。在場的市委領導沒聽懂,“什么意思?”朱镕基接過話來,“我來告訴你這是什么意思。”
1994年,朱镕基堅決用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替換之前的財政承包制,成為當時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最重要一環。而王石借用萬科一例,與總理找到了話題。
“王石從來不走尋常路。所以之后他的所有選擇,都讓人意外,但仔細想想,又不意外。”全忠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田樸珺:“想做的事情他會堅持到底”
(王石的女友)
“王石是我見過的最男人的人。”田樸珺并不吝嗇對王石的贊美。盡管初次見面時,她對王石的印象不是那么好。
和很多人對王石的第一印象一樣,田樸珺第一眼中的王石,看起來很牛,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直到王石講起登山的故事,田樸珺開始覺得這個男人很有味道。
王石講到了獨自走在冰壁上風雨交加,冰壁下面就是萬丈深淵,十米長的距離走了快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間,他的世界里風雨不再,因為太過專注眼前的路,狂風暴雨都可以被忽略了。
田樸珺看來,王石走過了很多世人不敢走的路。60歲再去學英語,每天書不離手,像一個處在旺盛青春期的人一樣渴望知識,渴望探索新的世界。“他做事情非常執著。很多人有小聰明,學得快。但他是有大智慧的人,想做的事情會堅持到底。只是有時候看起來大智若愚吧。”田樸珺對《中國新聞周刊》調侃曾被自己描述為“笨笨”的王石。
談到王石,田樸珺也順便說起自己的獨立。她曾表示過,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獨立,王石不會和她走到今天。
吳曉波:“身份的焦慮”讓他尋求新的自我
(著名財經作家,著《病人王石》,王石的朋友)
2004年,王石到杭州,約吳曉波在龍井山下閑談。聊到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往事,王石很感慨,突然問,“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么,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里繼承的?”吳曉波一時語塞。
10年以后,再回憶起當年的問題,吳曉波似乎有了答案。“王石他們這一代企業家,有著強烈的家國情結,這應該是來自儒家傳統。同時,他們崇尚西式文明和制度建設,信仰民主自由及階級獨立。所以,他們可以說算是‘雜交的一代。”吳曉波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吳曉波說,王石一代的覺醒,是時代的使然,是政府的作用,也有王石“身份的焦慮”。在民營資本被邊緣化、被調控和被重塑的年代,王石開始嘗試尋求新的自我,投身社會公益,倡導“企業公民”,參與社會重建。
與此同時,王石小心翼翼地保持著與政府的“一步之遙”。拿著城市里邊緣的地段,拿著邊邊角角的資源,一步步建出“萬科家園”。王石不行賄,不用做兩本賬,看似輕松地保持著清白。王石曾用吳曉波的話來概括自己,“過去三十年不是那么偉大,未來的三十年不是那么平坦。”
王石是硬漢,但也承認自己的病痛,在病痛中出走。吳曉波看出王石的“病人情結”。他把萬科當“病人”,所以要時時警覺、日日維新;把房地產業當“病人”,所以遏制欲望、躲避陷阱;把這個時代當“病人”,物欲橫流,到底什么才是人們真正的渴望?
吳曉波至今記得多年前審閱王石書稿時讀到過的文字:“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路軌旁拋扔著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彌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
那時的王石還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但他“病人”的身體里,總是迸發出對新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