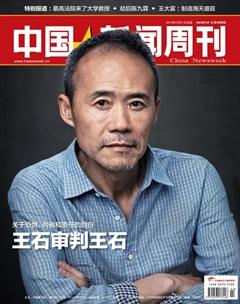美國“新絲綢之路”:且行且艱難
周瑤
今年3月,美國中亞南亞司的副助理國務卿蘇瑪爾(Fatema Z. Sumar)專門召開記者會,描繪了新絲綢之路的“宏偉藍圖”,雄心勃勃地表示,想借此“提升區域安全和經濟機遇”。4月,一組由美國政治家和專家組成的代表團將訪問塔吉克斯坦,懷揣著一份初具輪廓的鼓動人心的計劃。
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年度國情咨文中下定決心,今年年底前要從阿富汗完成撤軍。他表示,美國將繼續“關注”亞太,向盟國提供支持,為這一地區打造一個“更加安全和繁榮的”未來。
早在2011年,美駐阿軍隊已經從分批撤退。與此同時,一個被稱作“新絲綢之路”的戰略便開始浮出水面。
2011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印度金奈演講中,首次高調提出這一戰略。
它的愿景顯得十分美好:在貧瘠的阿富汗土地上,進行著繁忙的經貿活動。高速公路上汽車飛馳,鐵路網絡交織,電力貫穿整個地區。以阿富汗為樞紐連結起的中亞和南亞諸多地區也是同樣的情景。
“這意味著建造更多的鐵路,高速公路,能源基礎設施,比如在計劃中的從土庫曼斯坦開始,橫穿阿富汗,經巴基斯坦前往印度的輸油管道。”希拉里臉上一改招牌式的微笑,聲情并茂地描述,“這當然意味著要打通物資與人民流通的官僚政治障礙,意味著拋卻過時的貿易規則,因為我們彼此依存,我們都需要為21世紀采取新的行動。”

3年間,所有重大項目都未最后落實
作為貫穿亞歐大陸的交通動脈,絲綢之路涵蓋了文化、經濟等多重范疇。歷史上,東起中國,西至歐洲的這條大道主要為將中國的絲綢運輸出去,在沿線衍生了豐富的商貿活動。而美國的“新絲綢之路”戰略卻并非指這條古道,而是指廣泛的地區交通和經濟的聯系網絡,阿富汗是這片網絡的中心。
美國苦于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淖,花費巨大財力,國內反戰情緒高漲。新絲綢之路戰略應運而生。復旦大學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趙華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新絲綢之路戰略是美國為阿富汗的政治過渡所做的安排之一,目標是使阿富汗通過地區合作實現經濟自立。他說,“這既是地緣政治戰略,同時也是為解決阿富汗問題而設計。”
早在2009年,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及霍普金斯大學中亞和高加索研究所就提出美國的“新絲綢之路”構想,計劃的主旨是以阿富汗為中心,將中亞和南亞組建成一個大的區域。
希拉里在正式提出這一戰略三個月后,美國國務院向美駐有關國家的大使館發電報,要求將美國的中亞、南亞政策統一命名為新絲綢之路戰略,并向國際伙伴通報。由此,這一戰略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
為此,美國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別代表格羅斯曼(Marc Grossman)還特意重走了古絲綢之路,他風塵仆仆一路訪問了11個國家,包括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聯酋、土耳其、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卡塔爾,半個月的時間馬不停蹄,與各國專門討論新絲綢之路戰略問題。
對于美國來說,這樣一個戰略不是在本國實施,而是在大洋彼岸的大陸推行,需要多國支持,難度可見一斑。美國的中亞南亞司一直負責牽頭推進此事,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副國務卿伯恩斯(Bill Burns)、負責中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布雷克(Robert Blake)、助理國務卿幫辦艾略特(Susan Elliott)等也曾多次為推動新絲綢之路戰略奔走,可見重視程度之高。
過去三年間,美國的確做出了大量努力。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道(TAPI)和中亞-阿富汗-南亞電力網(CASA-1000)兩個項目,一直是戰略的重中之重。
CASA-1000項目原計劃投入10億美元,亞洲發展銀行原應投入40%的資金,但最終決定退出該項目,業內認為主要原因是擔心阿富汗的局勢安全。
今年3月,美國中亞南亞司的副助理國務卿蘇瑪爾提出美國政府未來幾年的主要舉措中,在地區能源上除了上述兩個項目之外,還計劃納入亞洲發展銀行的一個TUTAP的項目,同樣是用于電力網建設。
在貿易與運輸上,美國國際開發署建立了一個7800萬美元的項目,用于促進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貿易和增收。此外,還有一個命名為RESET的項目,用于創造區域能源網,以及支持當地需要的相應改革。
蘇瑪爾還表示美國將支持相關各國加入WTO,比如哈薩克斯坦,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等。
其他軟性的建設還包括將幫助創造習俗的和諧,創造開放而安全的邊界。他還聲稱,幾乎每個月,美國都在中亞和南亞國家不同城市舉辦論壇。
蘇瑪爾勾畫出了宏大的藍圖,但事實上,所有重大項目都還在談判之中,尚未最后落實。在實施上,新絲綢之路戰略的步履仍然且行且艱難。
中亞“角落”變“擁擠”了
中亞在當今國際政治中始終是一個相對遙遠和偏僻的所在。它地處亞洲內陸,相對落后封閉,除了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以及有時發生的動亂外,很少引起關注。然而近年來,俄羅斯的歐亞聯盟,美國的新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歐盟的“新伙伴戰略”等戰略相繼把眼光投往此處。按照趙華勝的說法,中亞“角落”變“擁擠”了,“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的一道特別景觀”。
美國似乎對于“絲綢之路”的概念情有獨鐘。早在1999年,美國政府就把旨在援助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政策命名為“絲綢之路戰略”(Silk Road Strategy Act)。可以看出,美國對于中亞的關注早就有跡可循。
趙華勝認為,美國希望借由新絲綢之路戰略達到多重效果。最明顯的是幫助阿富汗解決經濟發展問題,而后是推動中亞和南亞的經濟聯系,背后暗含的是抑制俄羅斯對中亞的控制。
俄羅斯打造區域一體化的歐亞聯盟由來已久,勢力也最為龐大。2011年10月,時任俄羅斯總理、即將參加總統競選的普京在報刊撰文,提出了他對歐亞新一體化的宏大設想,成為中亞響起的新號角。而這個設想的基礎是1995年就已經成立的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5國海關聯盟,以及2000年的歐亞經濟共同體。
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雖在2011年才提出,但它與此前的“大中亞計劃”一脈相承。小布什政府時期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助理國務卿R.鮑徹曾說,“我們要找到一個它(中亞)能夠獨立立足的地方,它可以和南方的朋友站在一起,成為世界上一個自成一體的重要戰略地區,不再是前什么地區,不再依賴任何人。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想的意思。”
美國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對俄政策表現得比較坦率,奧巴馬政府卻并沒有公開談及這一點,但從這一戰略本身,或多或少可以令人感受到這種用意。
趙華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就地緣政治意義上而言,新絲綢之路戰略帶有排他性。首要的就是俄羅斯和伊朗,其次是中國。”
阿富汗曾是俄羅斯的傳統影響范圍。從長遠看,美國這一戰略可以削弱中亞國家與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聯系,從而達到削弱俄羅斯對其傳統地區影響的目標。同時,也顯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國對這一地區的影響力。
盡管如此,美國助理國務卿R.布雷克2012年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次講話中表示,新絲綢之路戰略不是零和游戲,中國和俄羅斯也有機會對新絲綢之路戰略做出貢獻。
言下之意,美國也并不反對中國和俄羅斯在經濟上對新絲綢之路戰略做出貢獻。唯獨伊朗,美國既在政治上排斥,也在經濟上將其拒之門外。矛盾的是,伊朗不僅是阿富汗的鄰國,還是阿富汗極為重要的貿易伙伴。
“戰略失敗的風險很高”
趙臻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亞研究部助理研究員,也是美國“新絲綢之路”計劃專項課題的負責人。因為課題關系,她曾多次與美國方面打交道,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實美國國務院內部對于這個設想也存在一定爭議。”
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局勢仍然動蕩不安。新的天然氣、電力、鐵路以及貿易通道都要經過危機四伏的阿富汗南部,投資者因此顧慮重重。在趙臻看來,這會成為新絲綢之路戰略的最大困難。
美國也深知這一點。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布雷克曾表示擔心,新絲綢之路戰略的主要問題是地區不穩定、恐怖主義威脅、地區貿易水平低、社會貧困、婦女就業困難以及一些國家的非建設性行為等等。此前,駐阿美軍經巴基斯坦卡拉奇到阿富汗的后勤補給線就曾屢遭破壞,安全得不到保證。
與此同時,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和國內財政面臨壓力的情況下,在財政上也可能難以獨立支撐交通設施。趙華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阿富汗問題不能解決之前,新絲綢之路戰略難以說真正實現。”
盡管這一戰略對于中亞及南亞各國顯然有利,但是區域相關各國間的博弈與角力,也在無形中增加了推行的困難。
在趙華勝看來,俄羅斯希望在前蘇聯地區實現一定的影響,因此不希望中亞國家參加。這一戰略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但不大。他說,“從根本上來說,中亞國家不可能被完全拉到美國的方向去,這片區域是多元的。”
美國助理國務卿助理L.特蕾西(Lynne M. Tracy)在去年10月關于新絲綢之路戰略的一次講話中說,“新絲綢之路”戰略的目標不僅是把中亞、阿富汗、南亞連接起來,而且要使它一直通向東亞、中東和歐洲。
在此前美國官方的表述中,新絲綢之路戰略的范圍從來沒有提到“歐洲”。這一戰略意味著再一次拉長戰線。
趙華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上,美國預期的效果恐怕很難完全達到,在推進區域經濟的聯系上,新絲綢之路戰略會有所成效。”
美國留守中南亞的路程,顯然漫長。著名時事雜志《外交家》發表了名為《新絲綢之路無路可走》的評論,毫不客氣稱,“即使美國對于中亞的計劃是有價值的,但戰略失敗的風險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