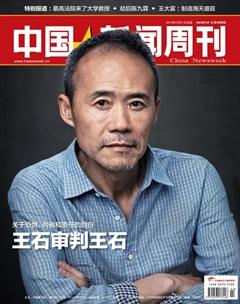發展服務業就是政府放權
陳憲
我從上海來,想從上海自貿區的背景來談一下服務業的發展。因為在自貿區方案里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服務業更加開放。
我們為什么要搞自貿區呢,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服務業更加開放,它涉及六大領域,包括金融服務業、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和社會服務六大領域。
但是到目前為止,應該說上海自貿區主要是做了兩件事,還沒有涉及服務業更加開放的議題。
第一件事,就是承諾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就是否定清單,以否定列表形式標明不符合規定的措施,除了清單上的禁區,其他行業、領域和經濟活動都許可,這等于將國民待遇延伸至投資發生和建立前的階段。)這個事情的國際意義比較大,奠定了中國和美國、中國和歐盟投資協定談判的框架,而且也表示了中國接受目前國際上最規范的投資規則體系。當然這個事情也關系到我們現在的很多審批權限改革。
第二件事,應該說就是立法。當然,立法和第一件事也有關系,因為要做第一件事就暫停三部法律,取消了三十多項行政審批。最近上海已經完成了自貿區管理條例,在上海市人大通過,如果中國在未來一段時期又在一些地方搞自貿區的話,上海自貿區條例就可能上升為國家的自貿區條例。這個法律問題的解決,對中國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再談談服務業更加開放的問題。大家知道,在上海自貿區28平方公里區域里,服務是無形的。因為上海自貿區并不太大,而且又是以原來的保稅港區為主,在這里,有很多事情做得很有限。最近有比較實質的案例。一個是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原來有一個行業的慣例,就是說會計師事務所在一個城市不能有分所,最近財政部有一個文件,允許本地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在自貿區設分所,這是一個比較有實質意義的舉措。還有是原來中國的旅游,中外合資的旅行社是不可以做境外游的,這次規定也出來了,在自貿區注冊的旅行社可以做除了臺灣地區的境外游。
事實上,服務業更加開放,是自貿區下一步的重點。而且更有意義的是,這一切和政府自身的改革相關,就是原來政府管理規定的變化。上海市政府也經常找專家問,服務業要更加開放,到底有什么辦法。其實從上面的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到,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不斷清理原來的制度、規定和審批權限。服務業的更加開放,可以寄希望于上海自貿區及自貿區以后的擴圍。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把服務業發展和開放問題放在自貿區背景下來討論。
我和原來一些同事,大概從90年代開始研究服務業貿易方面的問題,這些年來我們都在鼓吹中國服務業的發展,這也是現在的趨勢。但是我們最近觀察到一個現象,在中國有些地方政府,迫于一些成本的壓力,環境的壓力,產能過剩的壓力,有這樣一種跡象,就是去工業化。
簡單來講,在發達國家去工業化,一般是發生在人均GDP一萬美元左右,而且在整個國際分工體系里,在產業鏈里面,占據了高端。盡管這樣,金融危機以后,發達國家去工業化還是帶來了問題。所以美國為什么說再工業化,回歸實體經濟呢。
發展中國家有兩個特別典型的例子,巴西和印度。印度可以說是跨工業化,所以我們經常講,印度如果跨工業化走不通的話,大國發展模式就被顛覆了。還有是巴西,巴西也是農業人口占比較高,制造業發展水平很低。它在80年代后期就開始去工業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國家現在經濟的情形,它不僅僅影響到經濟增長,而且也造成了現在的社會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展開分析,對于它的過于民粹化都是有聯系的。中國現有的供給瓶頸,加之我們的生產性服務、高科技狀況以及需求不足的情況,如果出現去工業化的話,中國未來就可能出現產業空心化,就有可能出現經濟增長的下滑。
當然我們也試圖通過一些渠道,再做一些更多的研究——投資回報和全要素生產率等等的研究,這些問題都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證明中國服務業發展有低端化的趨勢,這種服務業的低端化趨勢,其實就像我們產能過剩一樣,都是政府過度介入的結果。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出現一種考核指標,考核什么東西呢?考核服務業占比,考核這個地方服務業就業占比,增加值占比,這些考核數據,不要說有沒有意義,在對服務業本身也沒有很好分類的時候,做這樣的考核有多大意義呢?因此我們發現,中國現在很重要的問題,還是制造業和服務業雙向的互動發展。因為中國整個工業化,可以說東部地區中偏后的話,整個中國工業化還是處在中期,應該說制造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所以講服務業的發展,雖然我唱了一些反調,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我們未來服務業發展更重要的還是生產型服務——和制造業相關的服務業的發展。
(作者系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院執行院長。本文是作者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EMBA教育中心“經濟學院院長論壇”上的發言,由經濟學院院長論壇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