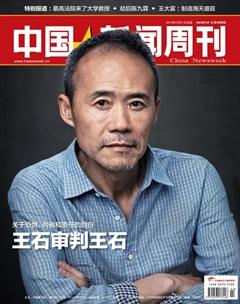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到底新在哪?
新型城鎮化新在哪?從不同角度會有不同回答,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新型城鎮化的起點與歸宿,都應當是人,而不是見物不見人,興城不興業的“房地產化”或“GDP化”。
想想三十多年前的農村經濟改革,成功之處就是把改革建立在農民需求基礎上,尊重農民的自主性,從而創造了市場,創造了農村聯產承包制,創造了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
三十多年轉眼過去了,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發展快當然好,但太快了,也會讓人忘記自己所處的位置。經常坐飛機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早晨還在上海,晚上就到深圳,第二天到北京,第三天在沈陽,這樣快速變化的結果是,會在某天醒來搞不清自己到底在哪。
永遠把發展的基點建立在尊重人的自主與市場機制上,這是中國改革三十多年最重要的成功經驗,也是我們搞清自己在哪的重要依據。
目前在討論新型城鎮化路徑時,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市場的作用被有意或無意地淡化了。“有意”,是針對既得利益者而言的,為了保護手中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做什么都強調審批與行政權力,從而獲得“權力尋租”的機會。“無意”,是針對民粹主義者而言的,為了實現理想中的公平,他們不惜用道德感召來替代市場機制,似乎保護農民利益,實現城鄉一體化,就要一步到位,就要社保等各種保障先行,用激進的“烏托邦幻想”來替代現實的發展路徑。
有句話說得好,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三十多年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再次聚焦農村,這應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有著共同的邏輯,那就是當農民這一群體被漠視,那就只能通過重新認識農民的作用,充分尊重其需求,讓其成為市場主體,站在市場的前端。只有這樣,才能找到改變城鄉差別的動力源。
就此而言,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并不是“被拯救者”,相反,他們是中國經濟新的市場力量,是啟動中國內需市場的“拯救者”。
一方面,到2013年底,中國大部分城市人均GDP已經超過8000美元,部分特大城市超過甚至一萬美元。按國際趨勢,收入進入這一階段,正是所謂“逆城市化消費”時期,意思就是說,城市居民大量的消費,無論是旅游玩樂,養生休閑,還是餐飲娛樂,消費的場所,消費的產品及內容,越來越出現逃離城市,趨向郊區或鄉村。
另一方面,農民階層,特別是外出打工群體,他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構成了另一大消費需求。所謂城鎮化,講的就是如何讓他們擺脫沒有基礎教育與醫療衛生服務的農村,融入到有著各種商業配套與公共服務的城鎮生活中。
正是這兩大消費需求構成了城鎮化的動力源。新型城鎮化的市場構建,就在于如何打通這兩大需求體系:一個是城市居民的需求體系,另一個是農民的需求體系。
按馬斯洛需求結構,城市居民的需求體系更多集中在第四、五層次,即尊嚴與自我實現階段。新鮮空氣,有機蔬菜,旅游休閑,度假養生,這些所謂的“綠色慢生活”,正是“逆城市化消費”的主要內容。而農民群體更多集中在第二、三層次,即安全與社會歸宿階段,他們需要安全的社會保障,渴求被全社會承認與接納。這兩個層次的需求一旦打通,就會形成兩股巨大的市場力量,創造出巨大內需。
首先,城市需求向城郊鄉村轉移創造的是多業態的產業,比如對旅游休閑,度假養生,有機農副產品,運動體驗,這些都會創造出相應的產業。有了產業,農民才有就業,經濟才能發展,社會才能持續。
其次,農民階層向往城市化所創造的需求,形成的是公共服務產業,包括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包括安全、教育、衛生與文化等服務,當然也包括住宅與商業地產的發展。
需要警惕一種傾向,那就是讓政府來包辦一切公共服務。這種傾向之所以很危險,是因為政府包辦的結果,必然導致市場力量衰退,導致權力腐敗。所以,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政府不僅不能包辦公共服務,反而要大力向民間資本開放,吸引大量的民間力量,這樣才能夠形成良好的市場環境,形成持續健康的投資機制。
所幸,中國已經進入了互聯網時代。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打通城市居民需求與城郊鄉村農民需求,離不開電商。電商打破了空間的限制,可以讓任何一個偏僻的市場輻射到全世界,這就大大降低了市場創新成本,從根本上講,也就降低了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成本。
電商就是城鎮化的翅膀。反之,沒有電商的城鎮化,就像鳥兒沒有長出翅膀呢。
姜汝祥
(北大社會學博士,北京錫恩咨詢集團董事長,著有《新執行》《差距:中國一流企業離世界一流企業有多遠》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