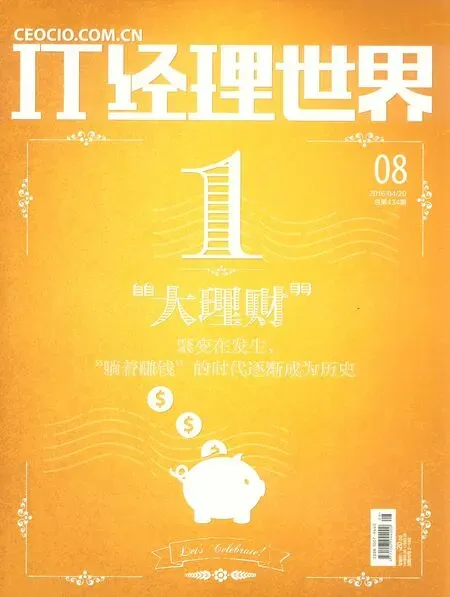美國科技產業的游說力量及其機制
3月底,由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聯合多位科技行業大佬組成的游說集團FWD.us(意為“前進吧,美國!”)再次高調地出現在眾多媒體的視野中。這個致力于推進美國移民政策改革的游說集團首先發表了最新的民調報告,稱共和黨人不會因其核心選民支持移民改革而受到任何政治傷害,強調再拖延移民政策改革的話,將非常不利于技術精英人才的集聚。與此同時,該組織在舊金山和紐約市分別舉行一個名為ThinkFWD的活動系列,提升公眾對于科技行業在夯實中產階級地位中所發揮的作用的認知度。
資金充裕的FWD.us組織獲得包括雅虎CEO瑪麗薩·梅耶爾、谷歌董事長埃瑞克·施密特、YouTube創始人查德·赫爾利、Instagram創始人凱文·斯特羅姆,以及微軟主席比爾·蓋茨和CEO鮑爾默等在內的高影響力人物的支持。
無獨有偶,另兩家來自硅谷科技行業的結盟機構(分別為“全球定位系統聯盟”和“互聯網協會”)也特地在華盛頓地區遴選專業的第三方游說公司,向國會和奧巴馬總統就行業政策走向進行納諫。“全球定位系統聯盟”的游說焦點圍繞聯邦通訊委員會日趨明朗化的網絡中立問題;而“互聯網協會”的聚焦則在隱私保護、網絡安全、知識產權和專利改革領域。
還有一家針對《數字千年版權法》(DMCA)改革的壓力集團叫FixtheDMCA.org,其背后支持機構則包括了Reddit社交網站、Mozilla基金會、O'Reilly出版公司、YCombinator創業孵化公司、EFF電子前鋒基金會和其他50多個科技行業公司。
誠然,以歷史觀來分析的話,“‘硅谷對‘華盛頓歷來敬而遠之”的現象亦不失為實。科技行業領袖們往往奉行“西海岸自由主義”,對卷入政治不感興趣。然而,現實往往催人警醒——1998年起微軟接連遭遇反壟斷訴訟,可謂成為美國科技行業從“對政治漠不關心”到“開始重視游說”的分水嶺。
之后,軟件公司努力嘗試讓政府放寬對技術出口的管制;互聯網公司成功地促成了一項網絡征稅案的叫停;國會山通過了一項法案保護包括電腦軟件在內的數字著作版權(盡管涉及電影和音樂數字版權的條款并沒有令所有互聯網ISP們滿意)。
到了本世紀初,圍繞網絡征稅的爭議繼續發酵,同期還有隱私和個人信息保護是基于立法還是公司自律、以及所謂“雙重用途”(本意是為民用的科技產品、但結果可能被訴諸軍事用途)的22大類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的議題,一直是美國科技產業與政策制定方之間的博弈。在2007-08年間,科技產業圍繞專利法規改革進行了巨大的努力,目的是使那些“專利流氓”難以成為公司棟梁;之后則有了增加H-1B簽證配額的放寬、科技經費支出與研發部門減稅等新的游說議題。
這幾十年一路走來,讓科技行業發現,“高科技”三個字在華盛頓的游說活動中其實是一張極好的通行證——因為,創新是所有政客都喜歡標榜的,支持高科技產業通常能幫他們烙上誠意支持創新的個性標簽(這不,公開數據表明,奧巴馬總統競選行動中前五大捐贈者陣營的兩個由微軟和谷歌員工構成)。因此,近幾十年來科技行業的一部“政治史”基本上都在書寫諸如“知識產權保護”、“支持海外營銷”、“幫助互聯網創新”、“提供政策優惠”等內容。
說起科技行業的政治游說,不能不提及“K街一族”——那些活躍在華盛頓西北區K大街上無數的職業說客。
如果說外界對于這些職業說客的普遍印象還停留在“神秘的權力延伸線”、“高薪”、“找關系、卡位置、謀利益”類似層面的話,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和加州大學聯席政治學教授Lee Drutman則在他于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發表的《使游說機制更完善》研究報告中表示,在包括科技產業在內眾多經濟游說活動中,說客們是“有價值的信息和專業知識的提供者”,尤其在國會人員本身的高流動率中把自己變得更為重要。Drutman教授援引一項美國“政策委員會”(Policy Council)調研顯示,三分之二的國會人員在受訪時認為,游說人員是“政策制定進程中必須的”,既是合作者,也是“教育者”。
按照美國的《游說公開法》,所有的游說人員需要進行登記注冊、游說活動申報(包括代表的什么客戶、游說議題是什么、游說費用是多少、與哪些政府部門已經或將進行接觸,等等)。盡管如此,信息公開之余,還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三位學者(Archon Fung, Mary Graham, 和David Weil)在他們的著作《全面披露:圍繞透明度的風險和承諾》一書中指出,信息完全披露并不意味著(信息)自動變得有價值,現行的美國游說公開制度中,尚欠缺能夠方便引導公民對于有關信息進行有意義的回應的機制。
艾博·索瓦爾 自由撰稿人,先后為Ad Age、BrandChannel、InterBrand等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