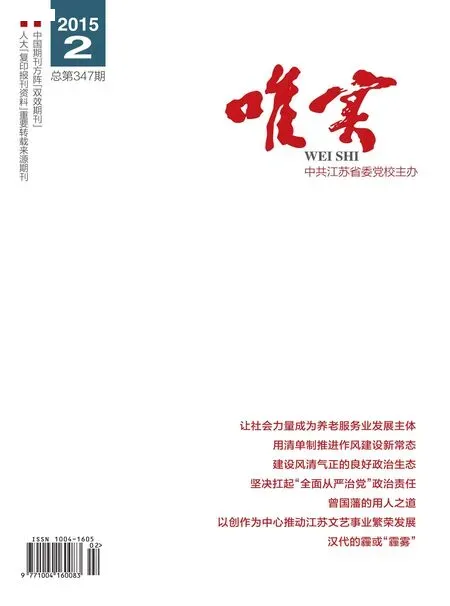城鎮化大背景下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難題的法律應對
上官丕亮
城鎮化大背景下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難題的法律應對
上官丕亮
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作為環境污染的一種新形式和特殊形式,具有更加隱蔽、分散的特點,易形成更深層次的環境污染,控制與治理的難度也更大。
一、目前防止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法律困境
就法律層面而言,環保立法滯后、環保執法受制于地方、環保司法救濟難,已經成為防止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法律困境。
環保違法成本低。雖然我國已有較為完善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但我國現行環保法律法規對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沒有作出應有的反應,缺乏專門性或針對性的禁止性規定,這是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不能得以防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前,我國所有的環保法律所規定的對違法排污行為的處罰太輕。“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我國環保法律的致命缺陷。即使是2008年新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設定的最高罰款也才100萬元。對污染環境者的處罰力度過低,是這些年來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不但沒有得到制止反而有加速趨勢的重要原因。
環保執法受制于地方。近些年來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問題突出,但許多環境污染事件并不是由政府的環保執法部門查出來的。在現實生活中,還有更多的污染農村環境的違法行為尚未受到環保執法部門的查處。為什么我國的農村環保執法不力,各地環保局在制止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方面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呢?究其原因,其中既有農村環保監管能力嚴重不足的因素,更有當地環保部門隸屬于并受制于當地政府而不敢執法的深層背景。那些高污染企業往往是當地的納稅大戶,當地政府正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才將那些高污染企業從城市招商引進到農村地區去的,怎么會允許自己下屬的環保部門去嚴格執法呢?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的環保部門,除了平時收取一點排污費外,其主要功能就是在環境污染事件發生時成為當地政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說些“對環境影響不大”等假話的“化解部門”,一些環境保護局成了“污染保護局”。
顯然,如果現行環保執法體制不改革,不解決環保執法受地方保護干擾的問題,那么我們寄希望于各地環保執法部門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嚴肅查處環境違法行為,制止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這一美好愿望就要落空。
環保司法救濟難。目前在我國通過司法途徑進行環保維權難呢,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傳統的民事訴訟制度難以應對環境污染侵權這一新問題,諸如歸責原則、因果關系等規定,往往對受害人不利。例如,2011年7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環境污染侵權案件,受害人就因為無法證明化工廠排放廢水廢氣與受害人種植的桃樹不能正常掛果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而被判決敗訴。二是由于傳統訴訟理論將原告資格限定為必須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對于農村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污染侵害,農民個人通常被認為與案件不具有直接利害關系,其原告資格不被承認,導致在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過程中生態環境等社會公益遭受侵害時,沒有人或者人們無法出面向法院提起訴訟。
二、遏制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法律思路
基于上述對我國目前法律困境的分析,我們應分別從立法、執法和司法三個層面采取應對和遏制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對策。
明確立法禁止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加大對環境污染的處罰力度。建議國家立法機關盡快對頒布于1989年、至今已20多年未作任何修訂的現行《環境保護法》進行修改,明確規定禁止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并建立更加嚴格的農村地區建設項目審批制度,特別是應明令禁止在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基本農田保護區等需要特別保護的區域內建設任何工業項目,以切實保障包括農村農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生命、健康、財產、環境等基本人權。同時,建議借鑒國外環保立法的有益經驗,盡快在法律上改變長期以來我國環保法律對違法排污行為處罰太輕的狀況,在《環境保護法》等所有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中加大對環境污染行為(包括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處罰力度,污染必重罰,要達到不治污染者關閉、違法排污者虧本、污染嚴重者判刑”的法律效果,強化環保法律的權威,扭轉“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尷尬局面,落實我國憲法關于“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精神,切實保護包括農村地區在內的生態環境。
環保部門實行垂直管理體制,加強環保執法。
目前國家所制定的環保法律主要依靠地方政府來執行,這種環保行政執法體制導致的結果是,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慮而陽奉陰違地“變通”執行、“打折扣”執行,甚至根本就不執行國家的環保法律,從而也就產生了當今中國的諸多環境污染問題,包括城市污染向農村加速轉移并且危害后果越來越嚴重的現象。顯然,要加強環保執法,讓環保部門在遏制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除了要強化環保部門執法人員的責任意識之外,更重要的是應當改革現行環保執法體制。
2010年10月10日,國務院在2004年發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提出“合理劃分和依法規范各級行政機關的職能和權限。科學合理設置政府機構,核定人員編制,實現政府職責、機構和編制的法定化”等規定的基礎上,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強調:“完善行政執法體制和機制。繼續推進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合理界定執法權限,明確執法責任,推進綜合執法,減少執法層級,提高基層執法能力,切實解決多頭執法、多層執法和不執法、亂執法問題。”2011年12月15日,國務院印發的《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提出:“建立跨行政區環境執法合作機制和部門聯動執法機制。”筆者認為,我們應當依照憲法第3條第4款關于“中央與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的規定,科學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執法權限,正如國務院法制辦公室青鋒同志所指出的“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執法權的重新配置”。建議借鑒國外環保執法部門直屬中央的有益經驗,明確中央政府在環境保護上的專屬執法權,環保部門實行垂直管理體制,直屬中央政府,以給予環保部門相對獨立的地位。只有這樣,才能從組織上確保環保執法不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保障環保部門嚴格執法,敢查敢罰,真正遏制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勢頭。
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完善環保司法救濟機制。針對傳統民事訴訟制度應對環境污染侵權的不足以及保護污染受害人權益的乏力,建議借鑒國外有關無過錯責任、忍受限度論、疫病學的因果關系等新型訴訟理論和制度,改造和完善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制度。在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法院完全可以借用這套理論來論證污染企業與農民受害之間的關系,從而簡化許多不必要的鑒定和法庭論證程序,最大限度地減輕農民的舉證負擔,及時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從而也達到遏制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效果。
為了保護環境鼓勵公眾對環保問題的參與和監督,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建立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值得我們借鑒。一般認為,環境公益訴訟可分為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是指無直接利害關系的自然人、法人、社會團體和政府組織,為了保護公共環境權益,對違反環境法律、污染侵害公共環境權益的企業和個人,依照民事訴訟程序向法院提起的、要求追究污染環境者民事責任的訴訟活動。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是指無直接利害關系的自然人、法人、社會團體和政府組織,為了保護公共環境權益,針對行政機關環保執法的不作為,依照行政訴訟程序向法院提起的、要求判令行政機關積極履行環境保護行政執法職責的訴訟活動。鑒于目前我國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分散性和隱蔽性以及農村環保執法力量的不足,特別是針對一些環境污染侵權無人管、無人訴、無法訴的狀況,建議盡快建立我國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允許10人以上的公民個人、5名以上的律師、民間環保公益組織、檢察機關等對污染環境的企業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對政府環保部門的行政不作為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法院所判的賠償費用和相關罰款,用于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和恢復被破壞的生態。為保障公眾的環保參與權和監督權,考慮到其公益性,建議環境公益訴訟免收原告的訴訟費和鑒定費,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被告負責舉證,真正讓環境污染者承擔起應負的法律責任,以確保在法律層面切實有效地遏制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

三、從法律層面多管齊下遏制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
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環保法律的規范、制裁和救濟功能,明確立法禁止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加大對環境污染的處罰力度,建立垂直管理的環保部門,加強環保執法,改造傳統民事訴訟制度并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完善環保司法救濟機制,多管齊下,形成制度合力,以切實有效地遏制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
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從深層次看,一些地方政府的發展觀和政績觀扭曲也是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一大原因。在一些地方,招商引資成為頭等大事、第一政績,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饑不擇食與發達地區的污染轉移一拍即合。當城市的落戶空間隨著治污力度的加大而越來越窄,高污染、高耗能的項目就轉戰農村地區。農村的山清水秀、良田萬頃,在對GDP的瘋狂追求面前變得無足輕重。因此,我們不僅要在法律層面多管齊下,而且同時還應當建立嚴格的綠色GDP考核體系,在考核地方政府及其領導干部時,不僅要考核其為當地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更要考核其任期內當地污染的發展變化及其治理情況,即把生態環境與污染治理納入各級官員政績考核的內容,生態環境惡化的、治理污染成效不佳的,主要領導干部不得提拔晉升,從源頭破解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問題。
(作者系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錢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