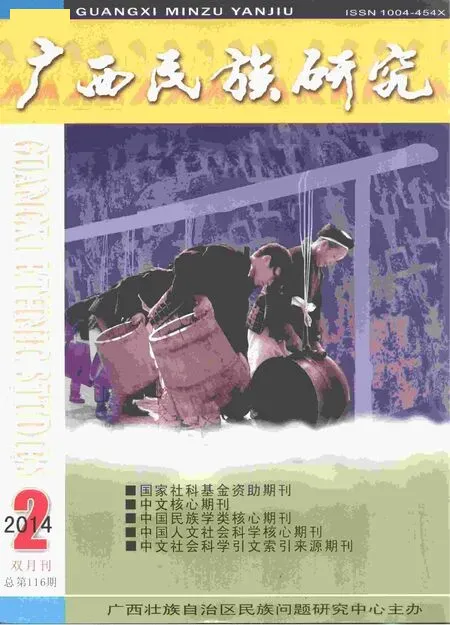論 “外出打工”的儀式過程與意義——基于桂西壯鄉伏臺的田野考察
李 虎
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民大規模地從鄉村流向城市,形成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動大潮,農民世代定居于一個固定聚落的傳統居住格局和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方式被顛覆。進入21世紀,“農民離開農村、離開土地”幾乎成為所有人的共識和努力方向,[1]1-19農民離鄉背井、拋家棄子,從農村走向城市務工的浪潮幾乎席卷中國的五湖四海和大江南北,成為當代中國農村最主要的時代特征。在這一背景下,世代定居于西南邊陲鄉村的壯族人也不例外,同樣卷入外出務工的浪潮中,外出務工成為壯族青年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經歷。越來越多的壯族農民離開生于斯、長于斯的原空間環境,進入到陌生的城市新空間中。
2012年1月至6月,筆者在廣西馬山縣西部的一個壯族村落——伏臺屯開展以外出務工現象為主題的田野調查。據調研期間統計,在伏臺屯734人中,共有397人的外出與務工相關 (包括務工和隨行),占總人數的54.09%。其中,務工者328人,占外出務工相關人數的82.62%;隨行者(即隨同務工者在外生活的老人或讀書的小孩)69人,占外出務工相關人數17.38%。外出目的地主要分布在廣東、廣西、海南等省區的各大城市,其中,到廣東各城市務工人數最多,共235人,占外出總人數的59.19%;在廣西區內次之,共124人,占外出總人口的31.23%;在海南務工者居第三,34人,占外出總人數的8.56%;其他省市者較少,僅有4人,占外出總人數的1.01%。可以說,村落基本已無青少年留守,形成社會學研究者所說的“空心村”。外出務工現象對整個村落的影響不僅是來自務工帶來的經濟收入,還包括來自城市的觀念、信息和現代技術,乃至大量青壯年人口外出對村落自身帶來的影響。因此,圍繞“外出打工”主題產生了以各種觀念、儀式和實踐等為表現形式的“打工文化”。
筆者曾有在福建、甘肅、云南、重慶等地的農村開展田野的經歷,這些區域的農村外出務工現象也基本成為常態,再結合當前的農村研究成果和網絡信息,可以發現,“外出打工”已然成為中國農村的普遍現象。因此,壯村伏臺不僅可以作為考察壯族地區農村外出務工現象的重要樣本,也是窺探中國大部分邊遠農村社會現狀的窗口。
一、理論回顧
自從“儀式”成為人類學的專業術語后,儀式研究一直備受人類學家的青睞,隨之形成的象征人類學也成為當代人類學最主要的理論流派之一。人類學早期的儀式研究主要集中于神話和宗教范疇,如著名人類學家泰勒 (Tylor,E.)、斯賓塞 (Spencer,H.)、史密斯 (Smith,W.R.)等都曾對神話儀式的研究做出貢獻,奠定了人類學儀式研究的理論基礎。法國社會學家兼人類學家涂爾干 (Durkheim,E.)和莫斯 (Mauss,M.)的研究主要是探索宗教儀式的社會意義,考察宗教儀式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作用和地位,為儀式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研究搭起一座橋梁。而隨后的范·蓋內普 (Van Gennep)、利奇 (Leach,E.R.)、特納 (Turner,V.)、道格拉斯 (Douglas,M)則進一步發掘儀式的社會內部結構、象征含義、本質屬性等,使儀式研究更加系統化和規范化。
涂爾干是最早探討儀式與社會關系的人類學家之一。他認為,宗教現象可以分為兩個基本范疇:信仰和儀式,而宗教信仰也表現出一個共性,即以神圣與世俗的對立作為分類前提,因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分為兩大類:神圣的部分和世俗的部分。[2]涂爾干這一“神圣/世俗”的著名命題后來成為人類學家在探討儀式內涵時不能輕易跨越的一個“原點”。[3]35-36范·蓋內普對于儀式理論的貢獻則主要來自于其對“通過禮儀”的研究。他認為,通過禮儀即“伴隨每一次地點、狀態、社會地位,以及年齡的改變所舉行的儀式”,[4]94而通過禮儀可以分為基本的三段結構,即分離(separation)、過渡 (margin-transition,又稱“閾限”)與整合 (reaggregation)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個體或群體離開先前社會結構和社會階層中的某一點,即與過去的日常生活狀態分離;第二個階段是介于“分離階段”與“整合階段”之間的過渡形態,受禮者進入神圣的儀式時間和空間,處于脫離日常時空的神圣世界中;第三個階段,受禮者回歸社會,恢復世俗生活的原態,但其社會角色或地位已發生質的改變。
象征人類學大師特納繼承并創造性地發展了范·蓋內普的儀式理論。特納在范·蓋內普通過禮儀三段式結構 (分離、過渡與整合)基礎上,提出新的三段式發展模式:前閾限 (preliminal)、閾限 (liminal)、后閾限 (postliminal)。在其看來,閾限階段是儀式過程的核心,它處于“結構”的交界處,是一種在兩個穩定“狀態”之間的過渡和轉換。他指出:影響“閾限”狀態重要性的原因是存在一種隱喻,即若沒有身處低位者,就不可能存在身處高位者,而身處高位者須切身體驗身處低位者的滋味。[4]97閾限階段是一種模糊不定的時空,此階段的受禮者處于一種神圣的儀式時空,處于中間狀態,所有世俗社會生活中的種類和分類都不復存在,甚至不存在地位、身份和階層等級的差異。
此外,人類學家利奇、道格拉斯等也在田野實踐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儀式理論研究。這些儀式理論豐富了人類學的成果,甚至成為后來不少人類學家研究宗教現象和社會儀式的“圭臬”。不少研究者立足人類學的儀式理論,探究生活儀禮、政治儀式、體育儀式、旅游現象等等。本文試圖借鑒人類學儀式理論的視角,基于一個桂西壯族村落的個案,分析當前中國農村社會中的“外出務工”現象,以及打工對于壯族村落社會個體的影響,剖析壯族社會和打工者對于外出務工的觀念和想法。
二、“打工”成為社會成員的“通過禮儀”
人類學家范·蓋內普發現,絕大多數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經歷一些重要的關口:從某一年齡階段進入另一年齡階段,從一種社會角色或社會地位進入另一種角色或地位。絕大多數民族或部落都要為個人在經歷這些人生關口時舉行儀式,即“通過禮儀”。[5]115蓋內普所說的“通過禮儀”,一般是指人一生中必須經歷的出生、成年、結婚和死亡等重要的人生關口。在傳統壯族社會中,這些人生禮儀是每個成員都要經歷的。然而,隨著外出務工成為壯族社區經常且持續發生的社會現象,它也成了具有與其他人生禮儀同樣意義和性質的“通過禮儀”。
筆者在田野中發現,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越來越多個人和家庭直接或間接地卷入到打工的浪潮中,打工已經成為壯鄉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打工文化已然滲透到社會成員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個人成長過程的必須經歷,甚至成為人生的一種“通過禮儀”和村落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模式。“打工”成為村民謀生立命的最主要選擇,是衡量社會成員是否勤快、有出息、乃至婚姻嫁娶的重要標準,因此也成為社會成員生命過程中的“通過禮儀”。打工由早期一種個體的自愿選擇,轉變為社會成員整體被動卷入的結果。
雖然很多青少年外出務工收入甚微,甚至沒有能力給家庭帶來實際的經濟貢獻,但留守村民在談到外出打工子女時,仍流露出明顯的自豪感。一位50余歲的村民稱:“我們家老三剛出去打工那年,過年回來的路費都沒有,但是沒有關系,只要出去就好,總比在家里天天伸手向我們要錢強。借了錢 (做路費)回來過年,然后我們再給他墊付回去的路費。”這位村民在談到其外出兒子時并未表現出不滿或不悅,仍然覺得年輕人能夠出去就是成功。
在2012年過年期間的一次家庭聚餐上①2012年1月25日在伏臺村民黃金世家的晚宴。伏臺有一個習慣,過年期間家中的飯桌一般不收拾,桌上擺上各式酒菜及電磁爐,若有客人進門,主人立即會邀請坐下,打開電磁爐煮火鍋,喝酒聊天。,餐桌邊除了筆者還有其他5位村民,其中兩位中年人,一位已有一年外出經驗的16歲打工者特弟②“特”是壯族人在稱呼小輩或平輩男性時的前綴詞。,一位18歲的高中生特懷,一位外出多年的23歲打工者特連。聊天時,特連掏出一包玉溪牌香煙發予眾人,先發給兩位長輩,后欲按距離遠近依次發給特弟、特懷和筆者。但發到特懷時,其中一位長輩發話了:“特懷不能抽煙,他還沒有成年。”特懷伸出的手,又縮了回去。特連接上話,呵呵地笑著說:“特弟應該比特懷小吧。要說未成年特弟才是,特弟都可以抽煙,特懷已經18歲,更可以抽了。”特連說這句話時順便將一支香煙遞過來,筆者擺擺手說:“我不抽煙”,謝絕了。另一位長輩接著回答:“話不能那么說,特懷還在讀書,還向家里伸手要錢,那就是未成年;特弟不一樣,出去打工了,獨立了。不過特虎 (指筆者)可以抽啊,雖然在讀書 (指讀博士)自己也已經有收入。”筆者接著問了一句:“那怎么才算成年啊?”這位長者回答:“去廣東了,不用向家里要錢。”筆者慚愧地笑了笑說:“有時候我還向家里伸手 (要錢)呢。”另一位長者笑呵呵地說:“你不一樣,你可以不算我們這里的人了。”從這些對話中,可以總結出經濟獨立是當地人認為一個年輕人成年與否的重要標準,而經濟獨立與否則基本與是否外出務工直接關聯,年齡甚至是次要的。因此,有時候當地人會把是否外出打工視為年輕人是否成年的標志。在這一背景下,很多年輕人為了追求經濟獨立,或是為了得到村落社會的認可而外出。
在這一前提下,村落中年輕人外出打工成為常態,非過年或家中無重大事情時在家賦閑則被看成一種異態。有些人在外出受挫后,即使暫時返鄉休養,但期間來自村落的壓力使其很快又選擇外出。田野調查期間,有位在家待了一段時間的受訪者說:
我這次回家是因為覺得在那里上班太累,想回來休息一段時間調整一下,再重新下去換個工作。但在家待著一點都不爽。不是過年的時候在村里待,不僅僅是無聊,最受不了的是村里老人們的異樣眼神以及各種差不多一樣的問題:怎么還在家里?還不出去?在家待著干嗎?什么時候出去呢?很煩的,所以我都基本上不出門,問的問題都一樣,懶得回答。①2012年2月23日訪談資料。受訪者:黃福盛;地點:其伏臺家中。
很明顯,這些問題的言外之意是,年輕人怎么不在外面好好混,不是過年過節跑回來干什么?是不是混不下去了?年輕人在家待著沒有出息,還是趕緊出去吧。而這位受訪者當然能聽得出這些意思,所以才顯得“煩”,只好選擇不出門來回避。此外,有位受訪者說:“平時在村里,沒有一個年輕人,沒有人一起玩,一點意思都沒有。”另一位年輕人指出:“在村里待著根本娶不到老婆,女孩都出去了,而且你不出去打工,在家待著那些女孩也看不上你。”一位24歲的年輕人說:“本想著過年前早點回來,年后在家待一段時間專門找老婆的,沒想到反而找不到。很多工廠過年的假期只有一個星期左右,女孩都是年前放假才回來,年后幾天工廠一開工就走了。”由于大多數年輕人都在外打工,村內沒有談婚論嫁的適齡青年,所以在家待著找對象顯然不符合實際。在外打工的青年男女僅過年期間才會回家待數日,很多青年男女只能趁這一時間找對象,但仍略顯匆忙。年輕人若在外打工時無法找到合適對象,欲回家找對象則只有看緣分。因此,當地人對這句話的評價是,現在找對象在家待著反而找不到,年輕人都在外打工,留在家里者多是老弱病殘,還不如在打工地找。簡言之,隨著務工潮的來臨,外出打工已經成為壯族村落社會對其成員的要求,也是社會環境促使個人必須做出的選擇。
務工潮形成前,外出務工雖然具有經濟上的因素,但這一時期個人仍然可以自行做出選擇,既可選擇外出,亦可選擇留守村中。當務工潮席卷壯鄉時,外出務工已成為村民是否有出息,是否有能力的重要評價標準。大多數村民認為不外出務工的年輕人都是好吃懶做、游手好閑、沒有出息的。打工是否成功甚至成為衡量一個人成才與否的關鍵,也是婚姻選擇的重要標尺。換言之,隨著打工成為社會成員成長過程中的“通過禮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拋棄了過去對方家中是否有足夠土地、是否耕種好手、是否會唱山歌等傳統的擇偶標準,而將是否外出打工、打工成就的高低視為擇偶的重要依據。從這一方面也可體現出現代擇偶標準更注重實在,如打工行業、打工收入、未來的發展潛力、家中的經濟狀況等。總而言之,對于年輕人而言,外出務工不僅僅是一種謀生手段,儼然已成為他們成長過程中必須經受的儀式洗禮,與生老病死這樣的“通過禮儀”具有同樣的地位和意義。
三、“打工”:一種“神圣的旅程”
在特納的儀式理論和“共睦態”②Communitas一詞目前在國內翻譯不一,有“共睦態”、“社區共慶”、“集體歡騰”、“交融”等,本文共引用兩次,均遵照原文,故出現不同譯意。(communitas)術語提出后,學者麥坎內爾 (MacCanell)便將其運用于旅游現象的研究,石破天驚地揭示:旅游是社會不同人群所上演的一種儀式。[6]旅游人類學者納爾什·格雷本 (Nelson H.H.Graburn)則從儀式性質、儀式結構與閾限體驗等方面將儀式與旅游進行比照,得出旅游既是一種“世俗禮儀”,更是一種“神圣的旅程”的論斷。旅游人類學的理論之所以能夠運用于對外出務工現象的分析中,是因為外出務工猶如一次長時間的旅行。兩者之間具有一定的共性,都是離開曾經熟悉的地方,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去感受、體驗。
大多數外出務工者,并不奢望通過打工留在城市,而是希望能在經濟上有所收益以實現經濟的獨立,豐富人生閱歷,學到某種技能以便于返鄉創業。尤其是在外出務工成為一種村落文化后,部分年輕人甚至不自覺地卷入到外出大軍中,因為只有外出務工才可能受到村落社會的認可。因此,借鑒格雷本的觀點,從務工者的生命歷程來看,外出務工不僅僅是“世俗禮儀”,更是一種“神圣的旅程”。
格雷本受到法國社會人類學家休伯特 (Henri Hubert)和莫斯的影響,結合利奇、范·蓋內普的儀式理論,提出旅游儀式性進程的分析模式。受這一模式的啟發,本文力圖通過儀式的過程對人口流動進程及其對個人影響進行分析,并將其稱為人口流動儀式性進程分析模式。格雷本在闡述其旅游儀式性進程的分析模式時,描繪了一個形象的結構圖 (見圖1)[7]245-246。下文將直接借鑒這一模式圖分析人口流動的進程及這一過程對流動者的影響,以便更清楚地認識流動人口在不同階段中的行為和意義。
A-B階段與狀態:流動人口在A-B階段處于“期待”外出的階段。如果將外出過程視為一個完整的、具有明確“閾限”價值的模式,則相當于“進入階段”(Entries)。這一過程的流動人口可能包含兩種行為和心理上的表現形式:一是在確定要外出務工后,流動者會有一段時間,幾周甚至幾個月,開展外出的安排和準備工作,包括資金預算及各項籌備工作。在這一段時間里,流動者會表現出一種期待的心理,但也會出現某種矛盾的思想狀態,主要表現為對外出地選擇的考慮、外出行業和收入的不確定、外出期間家庭留守成員的安排以及外出的適應狀況等復雜的心理活動。二是在外出務工那一個短暫的、真正“進入”的“閾限關節”。它是流動者從實際準備和心理期待到具體實現的“漸進”過程,這一過程的完成就意味著流動的開始。
C-D階段與狀態:C-D處于一種“接受洗禮”的階段和過程,它具有象征意義上“神圣”的“閾限”意義,處于完全脫離農村的日常生活而在城市中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狀態。這種狀態正是流動人口所期待甚至夢寐以求的。事實上,這一階段同樣也充滿著矛盾的狀態,流動人口會因為工作壓力、城市生活中的各種不適以及受到的各種歧視,而有返鄉的期望和沖動,但基于種種現實的考量又使他們選擇留在城市。
D-F階段:D-F是處于返鄉的階段,同樣體現出返鄉者的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外出務工者即將成功與久別的家人團聚,另一方面打工并沒有像期待的那樣容易出人頭地、成就偉業,一些打工者辛苦一年之后,身上所剩無幾,甚至沒有返鄉的路費。
在A之前和F之后的是一種“世俗”的日常生活,即所謂“出去”(Exits)階段。后一種階段是打工之后的狀態,對于打工者而言外出務工使其獲取某種經驗,甚至在家庭和村落內獲得身份的提升。
格雷本的“世俗—神圣—世俗”理論實際上承襲了范·蓋內普的“分離—過渡—整合”及特納的“前閾限—閾限—后閾限”的結構發展模式,三者存在本質上的結構契合。旅游前后即為“世俗”,旅游過程謂之“神圣”。這里印證了人類學者彭兆榮的觀點:涂爾干的“神圣/世俗”與其說是一組人類學、宗教學的概念和工具,還不如說它旨在間隔出一個結構的空間范圍。[2]“神圣/世俗”同樣將“外出打工”過程間隔出結構的空間范圍。對于邊遠地區的壯族人而言,城市意味著“先進”、“文明”、“富裕”,而鄉村則包含“落后”、“蒙昧”、“貧窮”的隱喻。欲洗脫“蒙昧”,只有依賴于到城市中接受洗禮以提高自身素質。外出務工者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重復著“世俗—神圣—世俗”的過程,接受著儀式般的洗禮。與格雷本對旅游的分析不同的是,人類的旅游活動更多的是自愿選擇,而外出務工的過程還包含著農村社會的期待,以及社會環境話語的推力。因此在這一外出務工的過程中,個人的從眾心理及村落中的社會輿論發揮著重要作用。
外出務工行為的推進還體現在個人的從眾心理。當外出務工成為村落社會評價其成員社會化不可或缺的標準,而眾多年輕人在求學之路上無法走得更遠時,即使再“胸無大志”、“缺乏遠大抱負”,也會受同伴影響匯入到外出的洪流中。“大家都去,我當然也要去了”——這一從眾心理使許多年輕人甚至失去判斷,不知不覺成為外出務工大軍中的一員。
四、“打工”與“返鄉”:結構與反結構的儀式意義
春節作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目前已經在中國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流行。全國統一的春節長假為長期分離的務工者與留守者提供難得的聚首機會。正如《歡打功》①歌詞為古壯字,于2012年6月12日由壯族歌師陸仕章演唱、記錄并提供。所唱:“廣東賴 錢,合年稱到扒……舍 依 裔,悲廣東千年;母憂欄西涼,歐錢不魯夠。”其大意為:去廣東可以掙到很多錢,一整年才能回一次家,老母親和幼子孤獨留守家中,然而錢是永遠掙不夠的。可見,務工者拋家棄子在外謀生,家中老小無人照拂,親情難以維系,只有過年是分離者一年當中唯一的回鄉團聚機會。然而,分離者春節短暫的聚首,常常沒有想象中那么舒適和美好,不少返鄉者常因返鄉期間各種應酬和緊湊的社會活動而不停忙碌,與家人的聚會反而很短暫,與親屬的聚首時間和交往范圍也非常有限。
春節期間外出者的返鄉生活充斥著各種需要完成的事務,最常見的如春節期間物品的籌備,青年會聚會、“幫”②“幫”,指壯族青少年達到一定年紀 (伏臺一般是十五、六歲)后,在特定日子里特定年齡段成員結伙到本村村廟聚餐,并結成村落中的一個年齡組。“幫”成員有義務在村內的重大事務中,相互團結、互相幫助,發揮作用。成員的聚餐、各類親屬和擬親屬的往來,各種婚禮、滿月宴、同學朋友聚會,祖先墳墓祭祀及大家庭的團聚等等,再加上其他雜事和家務纏身,大多數外出村民在返鄉期間幾乎都閑不下來,甚至不少居住地很近的村內成員都無緣碰面。即使是田野期間筆者為了抓住這一時期尋求更多的訪談資料,而常到村內各戶家中走訪聊天,但也有不少返鄉者無緣碰面。事后,當問其留守家人,你們家某某春節沒有回來嗎?怎么沒碰到?答案常常是,回來了啊,不過就待幾天,家里的凳子都沒坐過幾回,一直在外面跑。
長期的離別,加上春節期間難以碰面,不少村民之間甚至部分親屬之間也變得陌生。春節期間,在村落中最常見的初次見面打招呼用語是:你是哪位啊?是不是誰誰?回應則是:我叫某某,你呢?很多年沒見,都認不出來了。隨后便是:原來是你啊,很多年不見了,什么時候回來的?現在哪里混呢?做什么的?什么時候下去 (指外出打工)?可見,同一村落中的村民由于長期未謀面,使原有的熟悉社會出現短暫的陌生,同村村民不相識并不罕見。同時,隨著春節期間外出務工者的返鄉,打工相關的話語再次占據村民交談的主題,返鄉者與親人碰面、返鄉者之間偶遇或聚會無不談及打工,打工文化變得更加濃厚。
外出務工者返鄉的目的是與家人、族人、村人團聚,然而返鄉時間如此短暫,而離別期間無法從事的一些事務也通過時間的轉移,改為春節期間完成。因此,返鄉者短暫的春節變得更加繁忙甚至“擁擠”。春節期間,常常聽到不少返鄉者表示,回家本想跟家人團聚,坐下來聊聊天,也讓自己放松一下,可以吃好睡好,但卻總有這樣那樣的事情忙來忙去,坐下來說話的時間都很少,甚至覺得比在外面打工還累。
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在進行儀式研究時,不僅在范·蓋內普“過渡禮儀”論述的基礎上分析了儀式閾限階段的重要性,而且提出結構、反結構等重要概念。特納將人類社會關系分為兩種狀態:一種稱為“位置結構”(Structure of Status),即日常生活狀態,在這一狀態下,人們的關系保持相對穩定或固定的結構模式。此處之“狀態”,既指個體被社會承認的成熟情況,如“嬰兒狀態”或“已婚狀態”,以及個體于特定時間內的生理、心理或感情狀態;也指一種“相對穩定或固定的狀態”,包括法律地位、職業、職務、等級相關的社會常數。另一種被稱為“反結構”,即不同于日常生活與社會關系的儀式狀態,而儀式過程就是對儀式前后兩個穩定狀態的轉換進程。[8]133-134特納進一步指出,日常社會以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階層與階層的等級關系和矛盾為主線,等級關系和沖突是社會的結構。在儀式期間,社會的矛盾、沖突、分裂及等級關系暫時得到緩和,出現“社區共慶”(communitas)的形態,儀式結束后參與者又回到原初的社會地位和群體分化的局面。以此觀之,儀式的程序是從結構出發,進入反結構狀態,再回到結構,其結果是從象征上強化結構。[9]389
對于打工者而言,長期在輸入地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是一種“相對固定或穩定的狀態”,即所謂的位置結構過程。過年短暫的返鄉期間,打工地辛苦地上班攢錢與回到老家大方地花錢,停止他鄉日常的工作而忙于春節各式事務都形成鮮明對比,即務工者的返鄉生活擺脫了常態,而處于一種“不同于日常生活及社會關系的儀式狀態”,即特納所說的“反結構”狀態。可見,從打工者返鄉的角度而言,過春節具有一種“儀式”的意義。
從打工者一生的趨勢來看,打工生涯也可以視為生命歷程中的重要“儀式”,同樣經歷著“結構—反結構—結構”的狀態,即大多數外出者基于自身能力和現實的因素而無法留在輸入地,因此希望通過年輕時的打拼,在掌握一定技能和積攢一定資金后返鄉創業或年老返鄉生活。從這一生命歷程可以看出:外出務工前,村民在村落中出生、成長,并習得和遵循傳統生活方式,處于一種“相對固定或穩定的狀態”,即結構;而外出務工期間,務工者在生產生活方式上與傳統村落生活有著較大的差異,且處于與村落的親人、村人、祖先、神明及傳統文化分離的狀態,即“反結構”的狀態,而當最終因年齡或其他因素返鄉時,又重新回到村落生活中,在村落中隨年齡而老去,即所謂的結構狀態。
五、結語
隨著外出務工浪潮的席卷,打工成為邊遠地區壯族農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整個村莊充斥著各種外出打工相關的話題,城市成為大多數村民向往的新空間。村落打工文化的形成,使“打工”成為壯族社會成員生命中的“通過禮儀”,是否外出打工被村落社會視為年輕人是否成年、獨立,是否適合嫁娶,是否有追求、有出息的評價標準。因此,無論是基于何種原因,無論是否情愿,年輕人若無力通過升學之路外出開拓新空間,必然有意無意地加入到外出務工的隊伍中,因為打工已經成為壯族年輕人進入新空間最主要和最便捷的方式,也是社會文化對年輕人成長過程的一種基本要求。
對于務工者而言,外出務工是一種“神圣的旅程”。從其生命歷程的角度來看,可以分為務工前、務工過程及務工后三個階段,大多數成員寄希望于通過外出務工完成生命的升華。短期來說,外出務工可以受到村落社會的認可;長期而言,則是通過務工積攢資金、經驗等,以求返鄉重新創業和生活。因此,無論現實中的城市務工生活如何艱難,但務工者仍然希冀通過外出的歷程,獲得村落社會地位的提升,為社會角色的演變提供基礎。這不僅體現“神圣—世俗—神圣”的儀式過程,而且反映著“結構—反結構—結構”的儀式意義。當然,具體到打工者返鄉而言,“打工”也具有儀式的意義。務工者長期的城市工作和生活是一種“相對固定或穩定的狀態”,即位置結構過程。過年短暫的返鄉生活與之形成對照,即大方花錢、忙于應酬等不同于務工地的事務。換言之,務工者的返鄉生活處于“不同于日常生活及社會關系的儀式狀態”,即“反結構”狀態。
[1]朱啟臻,趙晨鳴.農民為什么離開土地[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
[2]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理論的知識譜系[J].民俗研究,2003(2).
[3]E·杜爾干.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M].林宗錦,彭守義,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4]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M].黃劍波,柳博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5]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文化研究的歷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6]趙紅梅.論儀式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兼評納爾什·格雷本教授的“旅游儀式論”[J].旅游學刊,2007(9).
[7]彭兆榮.旅游人類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8]張曉萍,李偉.旅游人類學[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9]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閩臺三村五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