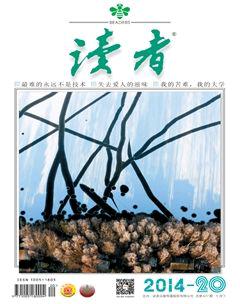一封沒有貼郵票的信
2014-05-14 11:40:57劉若英
讀者
2014年20期
關鍵詞:學校
劉若英

難得的下午,一個人坐在咖啡廳,窗外突然下起了大雨。心想這天氣倒極像我的脾氣,不來則已,一來,爽快下完,也就跟沒事似的。
突然一個人奔進了咖啡廳,像要躲雨,她試圖擦拭身上其實不可能去除的濡濕。我認出她來了。是的,二十多年沒見,我還是可以一眼認出她,因為她臉上有一塊形狀跟臺灣地圖一樣的紅色胎記。上小學時那些壞同學總說她臉上的胎記是她媽媽懷孕時在她臉上留下的糞便,我卻覺得那是她最漂亮的地方,紅紅的,彎彎的。
我走過去,她一看見我就叫出了我的名字,然后非常不好意思地問我怎么記得她。我指了指她臉上的胎記,然后她也指了指我臉上狗咬的疤痕,兩人一起笑了。
坐在我對面的她,看起來素樸爽利。她問我:“現代美容技術那么發達,怎么沒有想過去除疤?”我說:“怕老同學不認識我啊!”她又笑,說習慣鏡子里的自己了,如果沒有了“臺灣地圖”,她可能就忘記自己是誰了。
兩個“疤女郎”坐在沾滿水珠的落地窗前,突然安靜了下來。
她是我小學最要好的同學,個子很小,功課也好,總坐第一排。雖然她爸爸是我們學校收垃圾的工友,但是她每天都很干凈地出現在課堂上。
我們倆各梳著兩條辮子,常拿著冰棒,坐在學校操場的高臺上,晃著脫了鞋襪的雙腳,看著天空發呆。
上小學時,她就總說希望有一天能當老師,住在學校隔壁,每天跟爸爸一起去學校上班,寒暑假還照樣有薪水拿。
然后很快,我們畢業了,上了不同的中學,慢慢很少聯絡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小學生必讀(中年級版)(2022年9期)2022-02-16 09:53:02
意林(2021年11期)2021-09-10 07:22:44
小讀者(2020年2期)2020-03-12 10:34:12
快樂語文(2018年36期)2018-03-12 00:55:56
文學少年(有聲彩繪)(2017年9期)2017-10-23 01:34:46
留學生(2016年6期)2016-07-25 17:55:29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6年5期)2016-05-14 12:21:05
小朋友·聰明學堂(2014年7期)2015-01-15 12:07:06
中學生英語·外語教學與研究(2008年2期)2008-02-18 01:5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