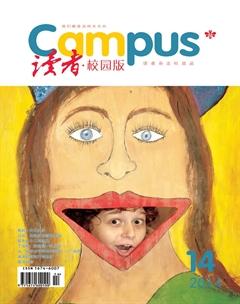初三的城市漫游
編者按:青春是葳蕤絢爛的夏花,青春是悠揚(yáng)動(dòng)人的歡歌。盡管時(shí)光荏苒,青春易逝,但每個(gè)人都有過(guò)不一樣的流金歲月。近期,我們約請(qǐng)了一些知名學(xué)者、媒體人、專(zhuān)欄作家,撰文回憶自己的中學(xué)時(shí)代,和廣大讀者朋友一道分享他們的青春之歌。我們從2013年第14期開(kāi)始,連續(xù)刊發(fā),敬請(qǐng)大家關(guān)注。
楊早,1973年生,知名文化學(xué)者,先后畢業(yè)于中山大學(xué)、北京大學(xué),著有《野史記》《民國(guó)了》等,譯著有《合肥四姊妹》。
跟很多人一樣,我的童年有一多半在爺爺奶奶身邊度過(guò),而且是斷斷續(xù)續(xù)的。被送回爺爺奶奶身邊的理由五花八門(mén),有時(shí)候是因?yàn)楦改腹ぷ髅φ湛床缓茫颐纥S肌瘦;有時(shí)候是因?yàn)槲野忠V州讀研究生,我媽帶著我壓力比較大;有時(shí)候是因?yàn)榘謰尮ぷ鞯乃拇?lè)山地區(qū)有地震……總之,我的小學(xué)履歷里寫(xiě)滿了轉(zhuǎn)學(xué)的經(jīng)歷。
轉(zhuǎn)學(xué)并不好玩,剛剛熟悉的老師和同學(xué)又要換一批,學(xué)校要換,口音要換,有時(shí)連教材也要換——正是五年制六年制轉(zhuǎn)換的當(dāng)口,成都已經(jīng)試點(diǎn)六年制,縣里卻還是五年制。
1987年我14歲,眼瞅著要上初三了。這時(shí)我爸已經(jīng)研究生畢業(yè)分配回成都,我媽也調(diào)動(dòng)了回去,只有我還窩在爺爺奶奶身邊。可是,戶口隨母,我的戶口與學(xué)籍都在成都,我得回那里去考高中。
初中前兩年,我上的是富順二中。這是一所省重點(diǎn)中學(xué),歷史悠久,人才輩出。如果非要我說(shuō)一個(gè)大家都知道的校友,好吧,郭敬明。不過(guò)我更愿意說(shuō),以“厚黑學(xué)”名世的李宗吾先生,是二中的老校長(zhǎng)。
盡管富順二中在川南聲名赫赫,但其中的一名學(xué)生轉(zhuǎn)學(xué)到成都,卻半點(diǎn)入不了稍好一點(diǎn)的中學(xué)的法眼。太差的學(xué)校,父母也不愿意讓我去。到處托人,通過(guò)一些拐彎抹角的關(guān)系,我被送進(jìn)了黃瓦街中學(xué)。介紹人說(shuō),這所中學(xué)雖然不大,倒是以嚴(yán)格出名。
黃瓦街中學(xué)真是“不大”——首先,它只有初中;其次,校本部只是三進(jìn)的小院,全是平房,所有的教室加起來(lái),只夠初三6個(gè)班上課,初一初二只好到附近的少年宮借教室。我在這里念了一年書(shū),幾乎沒(méi)見(jiàn)過(guò)初一初二的學(xué)弟學(xué)妹——這說(shuō)明幾乎也沒(méi)什么全校性的活動(dòng)。
操場(chǎng)是有的,雖然很小,但有兩個(gè)籃球架,一根旗桿。這操場(chǎng)小到?jīng)]法劃出標(biāo)準(zhǔn)50米的跑道,橫豎都不夠。體育課跑步是走出校門(mén),繞著學(xué)校跑一圈。測(cè)驗(yàn)的時(shí)候,將校門(mén)前的那條小街兩頭放些障礙物堵住,就在馬路上跑50米。
我在這里度過(guò)了初三的生涯。27年后回頭看,之前我在富順二中就讀,高中轉(zhuǎn)去廣東佛山,在佛山最好的一中上學(xué)。黃瓦街中學(xué)在我的求學(xué)之路上,是少有的不帶“重點(diǎn)”二字的學(xué)校,我甚至猜測(cè),在中國(guó)數(shù)以萬(wàn)計(jì)的城市中學(xué)群里,它的規(guī)模怕也只排在倒數(shù)的前列。
但我在這里獲得了一年的美好回憶。即使有升學(xué)的巨大壓力,碰到了兩三次校外流氓的勒索,也沒(méi)有沖淡記憶的光暈。真是一件奇異的事。
這樣一個(gè)小學(xué)校,學(xué)生多是附近街道的居民。似乎我是住得較遠(yuǎn)的一個(gè),而且還不會(huì)騎自行車(chē)。理所當(dāng)然,中午就留在學(xué)校吃飯。
這里居然也有一個(gè)食堂,應(yīng)該說(shuō)有一個(gè)廚房,因?yàn)槟抢锊o(wú)就餐的桌椅,買(mǎi)了飯須回教室吃。我又發(fā)現(xiàn)了一種神奇的狀況:整個(gè)初三,似乎常常只有我一個(gè)人在學(xué)校搭伙。
于是,我必須在早讀后去一趟食堂(離我的教室只有一二十米),告訴廚師,我今天中午要搭伙。到了12點(diǎn)放學(xué),我就拿著飯盒再去。廚師一般只炒一個(gè)菜,回鍋肉、蒜苔肉絲或是青椒肉絲,我一半他一半;再蒸一缽飯,1斤左右,你要打3兩4兩隨便。
我端著飯菜回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攤開(kāi)一本書(shū),慢慢地邊看邊吃。有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佐飯的書(shū)是汪曾祺的《晚飯花集》。因?yàn)槲业淖娓甘歉哙]人,且是汪曾祺的表弟,我對(duì)這本寫(xiě)高郵民國(guó)生活的書(shū)頗有親近感。吃著成都的飯,看著高郵的往事,陳小手、高北溟、王淡人、陳泥鰍。中午的學(xué)校安靜極了,偶爾有住校的雜工炒菜的“刺啦”聲。書(shū)中的這些人事遼遠(yuǎn)而沉靜,看到《鑒賞家》里季陶民在畫(huà)上題“風(fēng)拂紫藤花亂”,學(xué)校院子里,教室通往辦公室與食堂有一道花架,也有紫藤似的花。新學(xué)年開(kāi)學(xué)未久,初秋的風(fēng)還很溫柔。
飯后去洗碗,回來(lái)接著讀書(shū)。《晚飯花集》終于讀“熟”了,就換一本。過(guò)了一個(gè)學(xué)期,進(jìn)入考前沖刺階段,還從家里帶了一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版的《儒林外史》。有時(shí)中午如廁,也帶著書(shū)。那本書(shū)實(shí)在太厚,終于有一次在擋板上沒(méi)擱牢,掉進(jìn)了廁坑里。Ade,我的杜少卿和匡超人!
新到一個(gè)學(xué)校,我用書(shū)本與沉默構(gòu)筑了一堵墻。下午上課前有同學(xué)陸續(xù)進(jìn)來(lái),也不輕易與我說(shuō)話,大家待在座位上各做各的事。不過(guò)大城市的孩子還是比我要活潑得多。漸漸有人跟我打招呼,也說(shuō)上兩句閑話。有一次,一位女同學(xué)看我在讀一本《圍棋天地》,很好奇地湊過(guò)來(lái):
“這是圍棋哇?咋個(gè)下喃?”
我就簡(jiǎn)單地說(shuō)了兩句,最基本的,一顆子有4口氣,如果4口氣都被堵死,該棋子就要被提掉。
隔天中午,我正低頭看書(shū)。突然聽(tīng)見(jiàn)“嘩啦嘩啦”的腳步聲進(jìn)了教室,而且“嘩啦嘩啦”地放大,向我靠近。一抬頭,愕然,前面的椅子上,左邊和右邊各站了一位女同學(xué)。
“哈哈,你沒(méi)氣啦!被提掉啦!”
果然,后面的左右邊還站了兩位。我只好認(rèn)輸,跑到一邊,表示被提掉。經(jīng)過(guò)這一番鬧,同學(xué)之間的距離感少了許多。
慢慢熟悉了新的生活,戒心也少了。我嘗試著飯后走出校門(mén),往右走,50米(正好是短跑測(cè)驗(yàn)的長(zhǎng)度),就到了黃瓦街口,打橫是一條長(zhǎng)街——東城根下街。
我立刻發(fā)現(xiàn),不少同學(xué)中午并沒(méi)有回家,他們只是不在學(xué)校搭伙。
街口有一家賣(mài)葉兒粑的,號(hào)稱(chēng)“三不粘”(不粘鍋,不粘筷,不粘牙)。往左走(南方人分不清東南西北),街對(duì)面各有一家賣(mài)面食的,女老板坐在店門(mén)口包抄手,筷子頭在餡碗里略一蘸,在淡黃色的抄手皮上一抹,手一轉(zhuǎn),一只抄手便丟進(jìn)撒了白面粉的篩籮里。左邊的那家一碗會(huì)多給一兩只,右邊那家是一對(duì)姐妹開(kāi)的,自制的熟油海椒,滋味似乎的確好一些,一碗下肚,讓人渾身燥熱,雨天特別受歡迎。
再往前走,有一家賣(mài)刀削面的。下面的伙計(jì)并不炫耀地將面團(tuán)頂在頭上,只是隨意地擎在手中,一大塊鐵片嗖嗖飛舞,大小未必均勻的面片飛進(jìn)店門(mén)口的大鐵鍋中。撈出來(lái),加上油乎乎的肉糜,幾根青菜。中午總有好幾個(gè)學(xué)生站在門(mén)口輪候。觀察半年后,我覺(jué)得這伙計(jì)撈面的時(shí)候,給女生要比給男生的多,女生的3兩相當(dāng)于男生的4兩。
吃的沒(méi)有了,往前走只有臺(tái)球鋪。反過(guò)來(lái)往右走,仍然有刀削面、抄手,但味道沒(méi)有左邊的好。
再往前是一個(gè)集市,綠油油的碗豆尖,白生生的蘿卜,青郁郁的甘蔗,灰樸樸的地瓜。一兩個(gè)攤點(diǎn)賣(mài)衣服,完全不放在我的眼里。
走到集市中間,一個(gè)鍋盔攤!玻璃柜子擦得锃亮,里面擺放著白面鍋盔、肉鍋盔、酥油鍋盔,不要那些,我要正在烘的紅糖鍋盔,一吃一口糖,滴滴答答往下流,舉起來(lái),熱熱地捏在手心里。要是沒(méi)有紅糖的,就來(lái)兩個(gè)混糖的,沒(méi)那么綿軟,可以揪著吃,舌尖有隱隱約約的甜。
走完了這個(gè)集市,能看到一個(gè)頗大的茶館,幺師來(lái)來(lái)去去地沖水,茶客們仰面向天,或趴在桌子上打瞌睡。也有向茶館租了一副圍棋在下賭棋的,一點(diǎn)都不斯文,棋不是下的,也不是日本式的“打”,而是“砰”的一聲丟在木棋盤(pán)上,再用一根手指去戳正位置。不少棋子已裂成兩半,那又有啥子?難道半顆棋不算?下到收官,棋盒見(jiàn)底了,棋子不夠數(shù)!
“喂,說(shuō)好,這塊棋死了哈,我收來(lái)用。”
“啥子喲!老子還要留來(lái)打劫的。”
“打個(gè)鏟鏟!……數(shù)嘛,兩個(gè)劫材,等會(huì)兒讓你兩步就是!老子劫材多得很!”
“對(duì)嘛!哪個(gè)怕哪個(gè)?”
罵罵咧咧聲中一盤(pán)終了。輸家丟一張皺巴巴的大團(tuán)結(jié)(10元人民幣)在棋盤(pán)上。
哎呀!看得太久了,都要上課了得嘛!趕快跑!
學(xué)校果然嚴(yán)格。初三了,要升學(xué)了,別的法寶沒(méi)有,拿時(shí)間夯,每天加課加考,到晚上8點(diǎn)才放學(xué)。
每天5角錢(qián),5點(diǎn)鐘加一次餐。從外面訂的圓面包,食堂的廚師捧一個(gè)大笤箕,上面蓋著白布,掀開(kāi),半溫的一人一個(gè)。
最后一個(gè)鐘頭總是各種考試,不交卷不準(zhǔn)走。數(shù)學(xué)我一般會(huì)卡在最后一道大題上,雖然觍著臉,也只好去拉前面女同學(xué)的大辮子。一拉,她的背靠過(guò)來(lái),我輕聲說(shuō),最后一道。她趴回去了,一會(huì)兒,一個(gè)紙團(tuán)輕輕巧巧地掉在我的課桌上。
其實(shí)紙團(tuán)里的答案未必正確。管它的,只要能寫(xiě)滿試卷,便走得心安理得。每天都要考,明日等老師講評(píng)。
化學(xué)最麻煩。化學(xué)老師瞪著銅鈴般的雙眼,一遍遍地在桌子間巡視。
最累但最不心驚膽戰(zhàn)的是語(yǔ)文。語(yǔ)文老師坐在講臺(tái)后面看報(bào)紙,她不喜歡把考試當(dāng)成老師的法寶,不過(guò)也違拗不得校方的規(guī)定。初三的模擬試卷,知識(shí)點(diǎn)遍布初一到初三的6冊(cè)語(yǔ)文課本。6冊(cè)全的課本,全班只有一套,目下放在我的桌肚里,我一道題一道題地翻,十幾張卷子,做完一張,就有人取走一張,全班50來(lái)人都在抄我的卷子。
8點(diǎn)放學(xué),晚上的街道黑燈瞎火,不夠安全。學(xué)校于是規(guī)定家住同一方向的3個(gè)同學(xué)一道走。我跟另外兩位女同學(xué)分成一個(gè)回家小組。
她們倆手拉手在前面走。我不好意思跟她們并排走,拉開(kāi)幾米跟在后面。暗夜里只聽(tīng)見(jiàn)“唰唰”的腳步聲和偶爾的笑聲,有時(shí)其中一位女生會(huì)輕輕地哼一首歌,《雪絨花》或是《大約在冬季》。
有時(shí)老師開(kāi)恩,不考試(比如周末),放學(xué)的時(shí)候正是薄暮,但還是習(xí)慣地3人一道走。前方有影影綽綽的兩個(gè)背影,低低的語(yǔ)聲,不知道在說(shuō)啥。想走近點(diǎn),又抹不開(kāi)面皮。直到岔路口,她們先到家,兩人轉(zhuǎn)過(guò)來(lái),招一招手作別,連臉都看不清了。
4年過(guò)去,我從廣州返回成都,見(jiàn)到其中一位女同學(xué),她很高興地說(shuō)起從前的某事某事。
“這個(gè),我不知道呀!”
“怎么會(huì)不知道,就是初二上學(xué)期我們?nèi)コ鐟c……”
“我是初三才轉(zhuǎn)過(guò)來(lái)的呀。”
“哦?我怎么覺(jué)得咱們一起讀了3年……”
那時(shí)我才知道,這小小的黃瓦街,有清一代,是成都八旗駐防區(qū)域的中心。清制宗室準(zhǔn)用明黃色。成都的貝子與覺(jué)羅們將一條街的房瓦全刷成明黃色,故稱(chēng)“黃瓦街”。
從東城根下街的集市再往前走一條街,就到了著名的寬窄巷子。那是成都從前最美麗的所在,住的都是達(dá)官顯貴。連綿的小院,街兩邊都是粉墻,墻內(nèi)綠樹(shù)掩映,竹影婆娑。戶門(mén)的匾額,落款不是于右任,就是張大千。
這樣的好地方,整整一年我竟從未去過(guò),只是吃了上百個(gè)鍋盔,看了幾十盤(pán)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