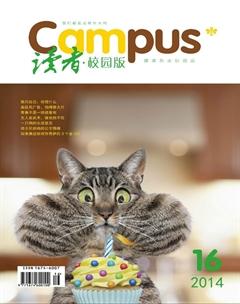給你講個笑話,你別哭啊
囧叔
“嗨,給你講個笑話,你別哭啊,就算不好笑也別哭。”
這是我媽在講那個笑話之前的心理活動寫照,我猜的。我媽年輕的時候沒怎么讀過書,不是文青,不那么細膩。很多凄慘的事情她都面不改色地當笑話講了。這一點都不奇怪,有些人天生粗線條,總是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而不自知,其實他們是善良的。高中時我有個哥們兒,特別憨厚老實。畢業前我倆坐在馬路牙子上喝黑加侖(其實是他畢業,我留級了),他說:“我給你講個笑話吧。”
接著他說:“昨天她來了。”他喜歡一個附近學校的女生,是個假小子,學校女子籃球隊友誼賽的時候來過,他一眼就喜歡上了。他說:“我在樓道里遇見她,她來找我們校隊的女生約暑假的比賽,我一咬牙,就鼓起勇氣說:‘你放學能不能等我一下?結果那女孩一笑,說:‘好啊,我一會兒來找你。你在教室等著吧!”
“結果你猜怎么著?”他一拍我后背,自顧自地憨憨笑起來。一陣“呵呵”后,他說:“結果,老子就在教室傻等。一會兒就聽見樓道里嘩啦一聲巨響。老子一個箭步沖出門一看,樓道的卷簾門關了!然后老子就在教室過了一夜,哈哈哈……”
“這根本不是一個笑話。”我生氣地說。一個18歲的男孩,就因為喜歡的女孩子隨便說了一句,就在教室等了一個晚上。當時同樣18歲的我覺得這事兒一點也不好笑。我都快哭了,但又沒有哭的理由。不過現在想起來,這確實只是個笑話。誰的青春沒有傻過呢?
當然,我媽講的笑話比這個水平高多了,畢竟是有60年閱歷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想的,把那些慘絕人寰的事情當笑話講。而且我看得出來,這樣的人在這么做的時候,是發自內心地覺得這沒什么。他們就算中了一槍,大概都能當笑話在臨死前講一遍。我上大學的時候,一個高中同學來找我玩,就講了這么一檔子事兒。
“嘿,”他見面先擁抱了我一下,跟熊一樣有力,“給你瞧個新鮮的!”
他伸出右手,張開五指。小指的形狀很奇怪:最后一個關節向一旁微微扭曲著,怎么也伸不直。看上去確實有點好笑,但又有些猙獰。
“怎么弄的?”
“打架弄的。”他說,“被人按在鐵柵欄上拿桌子腿砸的。”
說完,他“嘿嘿嘿”地笑了起來:“但是哥們兒后來把他們都干翻了。哥們兒當時還以為能演《新上海灘》了。”
笑話真冷。我很想說:“你這算殘廢了你知道嗎?”這個朋友好久沒有見面了,只是偶爾打個電話。不知道他的手指是不是一直都這樣。他是為了女朋友打架的,而現在女朋友當然早就換人了。
我媽講完笑話,我立即想到了這兩個朋友。水平固然差得遠,但性質差不多:他傷害了你,還一笑而過。他們不是故意要傷害你,而是神經比較大條。
我媽是在看《知青》的時候講她的笑話的。電視里,一個返城知青坐大巴去探親,把大衣忘在車上了,車上一位姑娘在長途車站苦等。
“你知道嗎?”我媽拿出慣用的民間故事開頭,她正在嚼提子干,“我插隊的時候,你姥姥干過一件特別可笑的事兒。”
我媽是笑點特別低的那種人。她給你講一個笑話,還沒講完呢,自己得先樂一會兒。“咯咯咯”樂完,她接著說:
“那年我正在內蒙古插隊呢,你姥姥啊,有一天想我想得不行了,也不知怎么就干出那么件事兒來。”(笑)“她也沒跟家里人說,就跑到長途汽車站去,先在那兒站了半天,不知道想干嗎,然后突然開始見人就問:‘內蒙古的車來了嗎?今天有沒有內蒙古來的車呀?你們知道內蒙古的車什么時候來嗎?你說你姥姥是不是精神不正常?”
講完,她嚼著提子干,沒事兒人一樣輕松地笑著。
我當時特別想罵娘,可惜她就是我娘,不知道怎么罵。我看了看我爹,他一副已經30多年了習慣了的表情,淡定地嚼著花生米。我又看了看我媽,她用30多年養成的固定的頻率嚼著提子干。
看著她的側臉,我發現我好像有二十幾年沒仔細看過她了。她才60歲,竟然長出一個提子干形的老年斑來。我一下子就想起一個笑話。小時候我爸我媽兩地分居,我跟我爸在保定上學,寒暑假回家,開學前回保定。有一次開學前,我爸帶著我進火車站,我“哇”地哭了。“我要我媽!我要我媽!”我不停地喊,不讓我媽走。我媽特摳門兒,從來不買站臺票。她在柵欄外面,攥著柵欄,臉貼著鐵棍,使勁喊著跟我說:“媽不走,媽一直在這兒呢,你放寒假回來,一下車媽就在這兒呢。”
哈哈哈哈哈!這個笑話好笑嗎?我看著提子干形的老年斑默默地咬牙切齒。但我不忍心把這個笑話講出來。
我媽看電視的姿態過于淡定,好像剛剛講的是一件別人生命中不值一提的、有點可笑的小事兒。她好像一面墻,墻內風起云涌六十載,墻外風平浪靜一瞬間。獨有一枚提子干形的老年斑在那里,讓我浮想聯翩。那一瞬間我簡直是弗吉尼亞·伍爾芙。
“你才精神不正常。”我默念著。我要哭了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