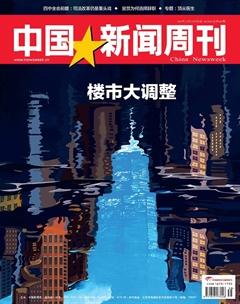圍繞“珍珠鏈”的是是非非
何亞非
近來,習近平主席訪問了印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南亞和印度洋國家,顯示了與周邊國家共同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良好愿望。然而,國際上有些人借機散布“中國威脅論”,稱中國為確保以印度洋為中心的海上生命線,正穩扎穩打地推進援助有關國家擴建港口的戰略,中國的“珍珠鏈”戰略已經令美、日、印等國“神經緊張”等等。
這樣的言論由來已久。這個說法最初是由美國國防部咨詢公司2004年一份內部報告提出的,當時并沒有多少人關注。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壯大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珍珠鏈”一說被西方政府和媒體熱炒。這顯然是想通過渲染中國加強與南亞鄰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交往,給中國戴上軍事“擴張”的帽子。
稍有海洋常識的人都知道,“珍珠鏈”是杜撰出來的,現實中根本不存在。雖然印度媒體也跟著議論過一陣,但印度政府心里很明細,并沒有把這類媒體炒作當一回事,因為沒有現實基礎。
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則需要力避陷入國際關系中所謂的“囚犯陷阱”,即一方的行動將引發另一方的負面反應,觸發惡性循壞,到頭來損害各方的根本利益。他們尤其需要放棄利用“第一/第二島鏈”或者“亞洲民主菱形”態勢來削弱中國海權的圖謀,這是典型的“冷戰思維”和“里根主義”的遺留物,目的是封鎖中國的出海口并挑起中國與鄰國的軍備競賽。
毫無疑義,南亞對穩定中國西南部邊陲、確保海上安全通道具有戰略意義。習近平主席去年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既是中國發展的需要,也是亞洲一體化的重要戰略構想,是對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頂層設計的重要貢獻。
最近習近平主席足跡所及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上;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則在“海上絲綢之路”上;而印度更是“一帶”和“一路”兩線一肩挑。這充分顯示上述南亞國家是“一帶一路”重要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交通樞紐,也是中國和非洲海洋運輸的重要驛站。南亞已經涌現出一些區域合作框架,如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等,都與建設新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絲絲入扣。可見區域國家“英雄所見略同”,建設“一帶一路”符合各方利益,已成為共識。
建設新海上絲綢之路將把中國的海岸線與東南亞、南亞次大陸、地中海以及非洲東海岸連接起來。在印度洋沿岸各地建設港口,圍繞港口設立出口加工區,可以加強中國與這些國家經濟貿易和能源通道的相互依存,讓中國發展成果迅速惠及周邊鄰國。正是看到這樣共同發展、互惠互利的美好前景,印度媒體在此次習近平主席訪問印度期間呼吁印度政府積極參與這一戰略構想的實施。
目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缺口很大,今后十年每年需要一萬億美元,而亞洲開發銀行最多只能提供150億美元。中國提議設立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就是希望發展中國家相互幫助,中國在這方面的強大產能和豐富經驗能有助于周邊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惠鄰”的實際意義正是在其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中國與南亞國家加強合作是雙贏、多贏的好事。中國希望與周邊國家共同建設新的絲綢之路、與周邊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共同實現經濟發展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基本考慮就是亞洲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應加強經濟一體化建設,推動區域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減少金融風險,鞏固亞洲各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并實現升級。中國愿意為此做出自己的貢獻,中國企業走出去也將放在這一框架內予以籌劃。
現在讓我們站在全球戰略的高度來觀察中國周邊的海洋通道問題。印度洋無論從海權還是陸權角度看,戰略地位之重要勿庸置疑。作為世界第三大洋,它連接中國所在的西太平洋和大西洋,在四大洋中居中并貫通亞洲、非洲、大洋洲,是重要的戰略大通道、運輸大動脈和安全生命線,更是中國重要的貿易、能源通道。中國80%以上的海運都要經過印度洋。
具體而言,多佛爾海峽、直布羅陀海峽、蘇伊士運河、馬六甲海峽和好望角被稱作是“鎖住世界的五把鑰匙”。印度洋就揣了三把。其中馬六甲海峽是東亞諸國通往中東航線的必經之路,最窄處僅3.7公里,真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咽喉。就中國而言,“珍珠鏈”純系子虛烏有,倒是上述美國及其盟友鼓搗的“第一/第二島鏈”和“菱形態勢”確有其事,已經對中國的運輸通道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日本則是“拉虎皮做大旗”,正企圖在中國海洋通道附近構建所謂“菱型”海洋包圍圈。安倍曾公開宣稱,要想牽制中國,日本、夏威夷(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應該聯合起來形成“鉆石型”包圍圈。日本海洋戰略核心是日本和美國的海權問題。最近日美再次擴大“日美安保條約”的適用范圍,就有將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從西太平洋擴大到印度洋的考慮,企圖構筑由澳美日印組成的“保衛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公海”的“菱形態勢”。
日本的所作所為自然是異想天開,不會成功,然而中國周邊的安全環境近年來因為域外國家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和日本等國上述一系列“零和”舉措確實較前嚴峻得多。中國國防現代化、維護能源通道安全等發展利益都要求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充分考慮這些因素,這完全在情理之中,與軍事擴張毫無關系。
現實情況是,中國在海外僅有2000多維和人員,也沒有任何軍事基地。什么“鏈條”都與中國沒有干系。
印度洋的地緣政治和軍事重要性還體現在南北走向分布的三串島鏈:西部的索科拉島、馬達加斯加島、塞舌爾群島;中部的拉克代夫群島、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和東部的安達曼群島、尼科巴群島、蘇門答臘島。這些島嶼大多數具有戰略和軍事價值,主要依賴陸上大國和海權強國的保護,早已成為一些大國重要的軍港和空軍基地。
美國海權戰略家馬漢預言,“21世紀將在印度洋上決定世界的命運”。話雖然說得有些絕對,但凸顯印度洋戰略地位。
目前,在印度洋有海洋控制權的是美國,迪戈加西亞軍事基地就是其中要害。印度視印度洋為自己的后院,并有安答曼·尼科巴戰略基地做支撐。
印度洋有難以替代的資源和地緣戰略價值,扼守著海上能源命脈和貿易通道,戰時還能掐住對手的咽喉,并能有效影響西亞、中東、南亞甚至中亞地區,自然成為大國博弈、“逐鹿中原”的必爭之地。
現在的敏感問題是,中國不管是發展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經濟和海洋往來,還是為能源通道安全與這些國家展開合作,都需要進入印度洋,在該區域有一定的存在。如何增強互信,減少猜忌,避免與美國和印度發生矛盾,是中國海洋戰略的重要課題。
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在印度洋的影響并不大。二十多年前,美曾指控中國“銀河號”貨輪向伊朗運輸制造化學武器原料,并派出兩艘軍艦和五架直升飛機,非法扣留銀河號長達三周。“銀河號事件”讓許多人清晰地看到,在海洋上被“扼住喉嚨”的危險性。中國能源進口和貨物貿易航線70%途經印度洋,進口石油80%通過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及其周邊地區對中國就是生命線。
隨著中國經濟利益的拓展,從地區大國向全球大國邁進,對印度洋的依賴會增大。為維護國家利益,中國不能也不用懼怕種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包括所謂“珍珠鏈”一說,而放棄印度洋。中國海軍有必要在印度洋維護國家運輸線的安全。中國這樣做只是為了自身經濟的安全,絕無威脅他國之意。建設“21世紀新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的實施,將為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互利合作提供更大的平臺。
隨著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中國有必要在事關國家戰略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問題上施加更大影響力。中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體現力量和存在絕不是炫耀武力,而是確保自身的戰略利益,何況中國的武力還遠遠落在一些國家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