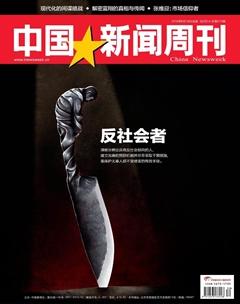現代化的間諜暗戰
席志剛
8月4日,中國官方公布,一對加拿大籍夫婦因涉嫌從事竊取中國國家軍事和國防科研秘密的活動,被遼寧省丹東市國家安全局依法審查。
次日,官方又公布了一起哈爾濱某高校航天專業碩士為境外情報人員搜集提供內部資料的泄密案。而此前在5月4日,廣東破獲了一起由境外間諜機關通過網絡勾連策反境內人員、竊取中國軍事秘密的案件。如此多的間諜、泄密案件集中公開,這在以往并不多見。
軍事領域諜影憧憧
“中國官方近期公布的間諜案,只是境外勢力在華從事間諜活動的一部分。”熟悉國家安全部門處置間諜案件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些間諜案件不予公開,低調處理是出于多種考慮。
在可公開的間諜竊密案中,境外人員直接竊取軍事國防情報的間諜不算太多。此次加拿大籍夫婦間諜案案發前,上一次公布境外人員直接竊取軍事機密的間諜案,是在2010年。當時,4名日本人擅自進入河北省某軍事管理區,并對軍事目標進行非法錄像被審查;也是在同一年,兩名日本人在新疆非法測繪,涉及竊取軍事信息。
更多的間諜竊密案,是境外間諜機構在中國大陸拉攏、收買、策反個別出賣國家秘密的人員,其中不乏軍隊將領、高官、學者。
此外,一些軍隊、軍工、專業院校等內部期刊、報紙等從個別“地下”渠道被境外機構完整地予以收集,導致泄密的案子這些年也時有發生。殲轟-7的泄密,即是由內部期刊管理不慎引發的。
在境外間諜機構眼里,解放軍、軍工企業內部報刊一度成為覬覦的對象,價格亦水漲船高。軍事分析人士指出,境外情報機構可以據內部報刊上的內容,大概分析判斷出目前解放軍一些兵力部署、部隊調動、演習規模、訓練水平,以及新型武器裝備的研發、試驗、建造、入列,以及形成戰斗力等某些具體動態。
另外一種竊取情報的方式,是以各種合法外衣作掩護,直接竊取國家和軍事機密。
在中國有的軍用機場、軍事基地、軍用港口、營房等軍事設施附近,乃至國家重點科研和建設項目的周邊曾出現過問題,有飯店、賓館、茶樓、娛樂場所十分可疑,沒多少買賣,但照樣經營得風生水起。這些場所被用以通過技術等不同手段進行竊密。
有些經營場所則成為情報人員以金錢美色等,利誘、拉攏、收買涉密人員或設立情報的接頭交易地點。據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二院保衛處人士透露,此前內部發過通知,該單位人員不得進入附近幾個街區的飯館酒店,嚴防泄密。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軍事抗衡、政治沖突逐漸被商業競爭代替。間諜攻勢已經不再是刀光劍影,也不再局限于軍情刺探,而是滲透在各個領域之中。
“西方如今對華情報工作,比任何時候都密集。”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除了傳統軍事國防領域,經濟領域的間諜活動日趨嚴重。
“和平時期的最大外患是情報戰、間諜戰的失敗,無防可設、無密可保,國家機密情報大量外泄。”軍事專家戴旭表示,很多大國的間諜前期一般都是著眼于商業情報,到后來往往會將手伸向更尖端、更機密的軍事情報。
商業領域成為重災區
“中國經濟開放度高,難免受到經濟間諜影響。”江涌表示,和傳統間諜(軍事間諜,主要針對國防、軍事、政治領域)不同的是,經濟間諜、商業間諜(工業間諜)案中的失竊者所受到的損害不是立竿見影地顯現出來,而是直到對手采用新策略、攜其新產品大規模地殺過來,自己才猛然醒悟遭人“暗算”。
“中國已經進入商業機密的諜戰高發期,一些外資機構中甚至存在第三國的情報人員。”江涌表示。
進入中國的商業間諜,通常以商務人員、銷售人員、經營人員,駐華代表等合法身份作掩護,此外還有技術人員、訪問學者等身份。
一般商業間諜和商業賄賂密切相關,商業賄賂是很多商業間諜打造圈子和人脈的慣用手法。與間諜活動相比,商業賄賂的性質更為復雜,手段也更為隱蔽。“所以,涉案分子覺得比較安全,很大膽地接受商業賄賂。”江涌分析說,“不過最有效的手段莫過于金錢、美色,商業間諜中的美女與俊男間諜最為搶手,總是無堅不摧。”
在江涌眼中,商業間諜無孔不入。國外評級機構給中國企業評級,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跨國會計師事務所給中國企業審計,給中國充當賬房先生;跨國投資銀行給中國做咨詢顧問,為中國企業乃至政府“出謀劃策”。這中間可能隱藏著大量情報人員,他們以各種合法的身份做偽裝,竊取中國的商業情報和商業秘密。
他們有的熟諳中國國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脈,想方設法接近各級領導,進行商業游說,影響相關決策,為商業活動鋪路;有的對有關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給予豐厚的課題經費,讓他們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影響為跨國企業集團謀利、鳴鑼開道,對中國相關部門決策與立法施加影響;有的積極培植為外國政府、跨國企業集團服務的買辦或掮客;還有一些利用安排出國觀光、子女境外就讀、協助轉移資產等手段,收買可提供有用情報信息的人員。
有關專家表示,這些商業賄賂行為,往往跟中國政府官員、國企高管的腐敗牽扯在一起。
國家保密局的報告稱,力拓的商業間諜“迫使中國鋼企在近乎訛詐的進口鐵礦石價格上多付出7000多億元人民幣的沉重代價”。但江涌認為,在中國,“力拓算不上太大的案子”。
“間諜案和普通的經濟案件、刑事案件的處置方式不一樣,很多時候是被當作交易、交換籌碼來使用。”江涌說,除了力拓案以外,還有很多典型案例不方便公布。“除非客觀需要,大量間諜案都不會公布。”
“商業間諜里的高手也不在少數。”江涌表示,大間諜的潛伏能力很強,力拓案中的胡士泰十分低調,和他的團隊苦心經營了六年之久后,才東窗事發。
間諜轉戰互聯網
互聯網的興起,使得上世紀遺留的傳統搜集軍情手段在不知不覺中已然升級,對手竊密不再以單一的重金美色相誘,而是轉戰網絡。
互聯網已經成為全新的竊密工具。有的是在網絡上擺渡、植入木馬等病毒,儲存機密的U盤、MP3等載密介質一旦聯網,那些悄悄植入解放軍重要部門和圈定人物的電腦的木馬病毒,便自動下載走全盤信息,令人猝不及防。有的則是動用各類先進網絡偵聽設備,竊聽盜取情報信息。
網絡間諜攻擊手法也越來越多樣,越來越隱蔽,境外情報機構除了重點瞄準中國軍事、軍工單位和重要政府部門的網絡以外,也將目標投向網絡上泄露的各種信息。一些國家在諜報機構中成立了“公開信息中心”,其任務就是每天在全球各個網站、論壇里搜集各種軍事情報。有國外諜報機構聲稱,在該國獲得的情報中,約80%來自公開信息,而其中又有近一半信息來自互聯網。
中國國家安全部公布的資料顯示,在已抓獲的間諜中,其中60%的間諜承認一些重要情報是在網絡社區中獲得的。他們往往在側面得知一些零星情報后,在各大網站論壇里發帖,引誘網民為他們搜集情報。
軍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對網絡管理不善,或網民缺乏應有的國家和軍事安全意識,互聯網將會成為泄露國家、軍事機密的重要渠道。用極其簡便的手段,付出微不足道的成本,諜報機構就能獲得十分重要的情報。
據了解,網絡諜報人員主要從官方、半官方、民間的網站公開發表的資訊中收集信息。在一些論壇的聊天室,也可以收集情報信息。比如,如果要收集空軍的情況,通常先貼個帖子,說“某空軍如何不堪一擊”等,馬上就會有人跟帖反駁,說空軍如何厲害。或者,以“有誰知道我國空軍現狀”為主題發帖,也會有人回應。
以這些回帖為參考,再對已有情報加以研究分析,就可得出大致的情形。前述熟悉國家安全部門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網絡泄密的情況觸目驚心:個別網站和論壇為了吸引眼球熱衷于揭秘,一些人缺乏保密意識在網絡上隨意談論軍事秘密,甚至在網絡地圖上標注軍用機場、雷達陣地、部隊駐地等軍事秘密。
中國有關部門權威人士透露,目前境外有數萬個木馬控制端IP緊盯著中國大陸被控制的電腦,數千個僵尸網絡控制服務器也針對著大陸地區,甚至有境外間諜機構設立數十個網絡情報據點,采用“狼群戰術”“蛙跳攻擊”等對中國進行網絡竊密和情報滲透。
盡管中國大陸很多保密單位的內部工作網都不與互聯網連接,但仍從中發現了境外情報部門植入的木馬。調查表明,一個重要的途徑是擺渡攻擊,利用的是像U盤、移動硬盤之類的移動介質。網絡安全專家提醒,網絡間諜得逞,往往與其攻擊方的管理不善有關。
“總體國家安全觀”下嚴防泄密
2010年7月,中國軍方開始成立網絡監控隊,嚴查互聯網泄密。
在國家層面,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對網絡涉密、泄密有了嚴格的界定。中共中央軍委根據該法同步修訂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保密條例》,其中對網絡涉軍信息做了明確限制。
網絡領域的防軍情泄密,是世界各國軍隊普遍性的難題。解放軍除了網管有“十條禁令”外,還規定軍隊人員不準使用3G手機。此外,解放軍每年都會出臺各類禁令法規,以約束在職軍人的言行舉止,嚴防泄密。
2014年2月,中國設立了習近平掛帥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負責加強網絡安全方面的工作。網絡安全被置于國家安全委員會“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下,層級可見一斑。
繼今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條例》生效后,4月下旬,中央軍委印發《關于做好新形勢下保密工作的意見》,系統提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保密工作的指導思想、 總體目標和重點任務。
今年5月19日,美國司法部以所謂網絡竊密為由宣布起訴5名中國軍官。近期,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旨在確保國家技術部門安全的措施:中央機關所有采購計算機類產品不允許安裝微軟Windows 8操作系統、禁止采購賽門鐵克及卡巴斯基殺毒軟件、棄用IBM的高端服務器。外界據此認為,這是中國采取的報復行動。
“保密機制存在漏洞,缺乏專門法律、領導、協調機構,也缺乏相關的意識。”江涌表示,防不勝防的隱形間諜無處不在,在經濟領域里,安全和保密概念被淡化,保密意識在各個企業極度欠缺。因此,制定有關反經濟間諜的法律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