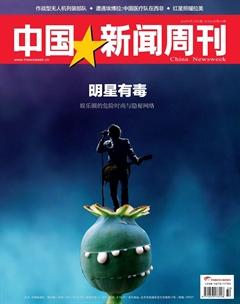遭遇埃博拉:中國醫療隊在西非
陳君

“當地政府和醫療機構開始越來越重視埃博拉疫情的防控。盡管醫療設施和生活環境還是很差勁,也不可能一下子提高到什么水平,但畢竟比疫情剛出現的時候,重視多了。”8月22日,與王耀平通話時,他正在開車回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路上。作為中國援塞拉利昂醫療隊的隊長,王耀平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說,這幾天心情還好,“不算太緊張”。
從火車站、機場到鬧市區,塞拉利昂越來越多的人戴起口罩,注意保持距離塞拉利昂人開始學著改變習慣,去防控前所未有的埃博拉病毒,“打開電視和收音機,你能知道隨時播報的埃博拉疫情,這也是人們議論的中心話題。酒店里、商場里,到處張貼著手寫的或印刷的防控宣傳告示,大家再也不敢不重視了。”《弗里敦新聞》記者法盧亞達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我說的是大城市,但在農村,情況還比較糟糕。”
令王耀平安心的是,中國醫療隊10名醫護人員至今安然無恙,“內科醫生王煜為埃博拉患者治療過,一度被隔離觀察,萬幸的是他沒有被感染。”幾天前,王耀平從機場接回國家增派來的公共衛生醫療專家,“我們也陸續接到了很多防護設備,真的感覺到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據媒體報道,繼4月向幾內亞、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幾內亞比紹四國各提供100萬元人民幣防控救治物資后,中國政府8月初再向西非三國提供總價值3000萬元人民幣的緊急人道主義救援物資,包括醫用防護服、監護儀、噴霧器及藥品等,并分別派出公共衛生專家組。
世界衛生組織8月22日發表聲明說,當前埃博拉疫情仍被嚴重程度被低估。截至20日,西非地區累計出現確診、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2615例,已有1427人死亡。
在塞拉利昂:與埃博拉不期而遇
2013年初,衛生部組派中國第16批援塞拉利昂醫療隊,任務下達到湖南,岳陽市領命,從市縣幾家醫院抽調1名主任醫師、8名副主任醫師和1名廚師,醫療隊組建完成,市衛生局副局長王耀平任隊長,去年4月出征,抵達塞首都的金哈曼路醫院。
中國從1973年3月起向塞派遣醫療隊,至今已經是第16批。和之前的隊友一樣,王耀平他們剛到的時候對很多事都不習慣,“從生活居住到醫療衛生條件,都很差。有人開玩笑說,這里和國內的差距,不亞于從塞拉利昂到北京的距離。”他說。
現實比玩笑殘酷得多。常年內戰,積貧積弱,塞拉利昂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基礎設施毀壞嚴重,國民經濟瀕于崩潰,公共衛生醫療系統更加薄弱。在這個有著610萬人口的國家,注冊醫師卻不到100人,而人們普遍不相信現代醫學
王耀平和他的戰友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中與埃博拉不期而遇。
7月,一個腹痛腹瀉的病人被送到醫院,他還伴著大量嘔吐,“癥狀特別像疑似疫情。我們把他放在病床上,安排在相對獨立區域,馬上通知塞拉利昂相關衛生機構來抽取血樣。”所謂“相對獨立區域”,也只不過是醫院走廊一角,就在王耀平辦公室門口。
病人最終確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并很快死亡。王耀平清楚地記得,那天還停電,病房里很悶熱伴隨著病人死亡,病毒像個幽靈,潛伏在不知道病房的哪個角落,或與大家擦肩而過。
這里實在太簡陋了。不論是正規病房、病床還是常用的醫療設備、專業醫護人員都短缺,醫生們一個頂幾個用。這無形中都加大了被傳染的幾率。
口罩、手套、眼罩、一次性防護服這些救命的防護用品也都是從國內運來的。每天早晨,醫生們都要在約十平方米的休息室“武裝到牙齒”, 如電視上看到的,大夫們都包裹得嚴絲合縫,然后開始面對病人,“大家每天相互提醒,務必嚴格按照程序穿戴、丟棄、處理。”
“尤其在非洲,那種熱是你無法想象的,完全不透氣。”已退休的內科醫生李士祥感嘆道。他曾兩次隨隊援助西非。
科學程序是安全的保證。“比如洗手和測體溫,進入公共場所,尤其是機場、醫院,要用消毒水洗手、測體溫;吃飯前,用自來水、洗潔精和肥皂,依次洗,這是必須的步驟。急需的物資我們可以援助,但電和水,就沒辦法了”。 李士祥說,像在幾內亞等落后國家,總是停水,他們用各種方式儲水,這也成了每屆醫療隊的必修課。
從金哈曼路醫院門口到走廊、診室,彌漫著消毒氯水的氣味,所有人都要用消毒水洗手后才能進入醫院,政府派來的軍人在門口維持秩序。
據介紹,中國醫療隊已幫助醫院建立了比較齊全的診療科室,疫情暴發后,來這里看病的普通患者也沒有減少,病毒威脅也隨之而來。
每天,先由“全副武裝”的護士們在分診臺,測量病人體溫,詢問情況,如有可疑病例,立即送到指定區域,雖然首都弗里敦不是重災區,中國醫療隊所在的金哈曼路醫院也不是重點接收埃博拉病例的醫院,但每個人都不敢掉以輕心,“比如,對疑似病例進行初步判斷時,我們的醫生都要用醫用膠帶把手套和防護服袖子的接觸部分封上,反復檢查眼罩是否戴好”王耀平介紹說。
在距離弗里敦約20公里的塞拉利昂-中國友好醫院,一批批中國醫生被當地人當成救命的唯一希望,其中故事無數。
塞中友好醫院也是塞拉利昂最好的醫院。門診樓、醫技樓和住院樓相連而立,一共兩層;綠植和草坪環繞四周,四處張貼著宣傳疫情防范的海報。
8月15日抵達塞拉利昂的專家組,立即投入工作,協助使館分配醫療物資,指導醫務人員學會使用,向當地政府提供防治疫情的建議。同時,對使館人員、中資企業人員、中國醫療隊等進行防控培訓。專家組組長、中國疾控中心生物安全專家李振軍希望,得確保讓援助物質盡快用到實處。
8月中旬之后,這里大門緊閉,格外安靜。出現埃博拉病例后,與病人接觸過的7名中方醫務人員和一些塞方人士就地隔離觀察,所幸至今未出現癥狀。
“等隔離期結束后,我們好好慶祝一下。盡管埃博拉出血熱要比非典兇殘100倍,但我們有自信,有大家的支持,有抗擊非典疫情的經驗,我們不怕。”一位醫生在短信中寫道。這些來自不同醫院的中國援助醫生每天都要跟原單位聯系,報平安、討論醫療方案、獲得技術支持等。
在幾內亞:曾離埃博拉最近的中國人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里克8月22日宣布,世界衛生組織下周將出臺一個應對埃博拉疫情6至9個月的戰略計劃。中國駐幾內亞醫療隊隊長、北京安貞醫院副院長孔晴宇格外關心這樣的動態消息。
今年3月,他所在的中國-幾內亞友好醫院在近20天時間內,接診了12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幾內亞第一例埃博拉病例就是我們中幾友好醫院接診的,是個男性,44歲。”心外科專家孔晴宇多次對媒體介紹說,醫療隊對常見熱帶病都有所了解,但當時對埃博拉并不是很了解。那個男性病人被送醫的第二天晚上就死亡了,隨后他的4名親屬也陸續去世,醫生們才驚覺:埃博拉出血熱是多么可怕。
很快,病人感染了9名醫生和護士,其中6人去世。有過接觸的兩名中國醫療隊隊員也被隔離了兩周,所幸未被感染,其中就包括普外科醫生曹廣。
“在給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治療時,我曾為患者體檢,徒手翻開過患者眼瞼,且隔了很長時間才去洗手。后來,由于先后與兩名感染者有過接觸,醫院通知我要隔離觀察。”曹廣的“心路日記”在他的微博賬號“救命鼠CG”上發布,被廣泛傳播,讓人們認識了這個“離埃博拉最近的中國人”。
他清楚地記得,“患者死亡當天,左眼白眼球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顆紅得讓人害怕的像兔子一樣的眼珠。更讓人費解的是,患者的左臀部肌肉注射點,不予壓迫,居然會有鮮血不斷地緩慢溢出,把床單都弄濕了。”這個現象在曹廣當醫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見到。
“在這里根本沒有什么傳染病報告制度,至少我沒有看到,在我們醫院根本就沒有傳染科。醫院的防護安全意識更是低下,我們手術室的手術巾就是那一條,早已經是血肉模糊了,還在用。有時候上手術我們都沒有手術衣,光膀子,穿日常服裝手術,我都經歷過。”他記錄道。
現在,西非三國政府逐漸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開始采取實質性防控措施。比如,在塞拉利昂,政府出臺法規,將藏匿埃博拉患者定為犯罪,違者最高判處兩年監禁。
和曹廣一起接受隔離觀察的還有內鏡專家吳素萍醫生,她駐地宿舍墻上還貼著中國蛇年的卡通形象,兩個人在“隔離觀察”期間“相互支持、相互鼓勵”。吳素萍有時熬些粥給曹廣送過來,他有什么好吃的也給她送過去。
在隔離觀察期間,即便是一個平時性情粗獷、見慣了生死的外科醫生,也會不自覺地開始仔細注意身體上所有細微的變化:“隔離期間,體溫是頭等大事,試表即便顯示體溫剛到36.9℃,也會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早上起來洗臉,要在鏡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出現了跟患者相仿的眼結膜出血;白天有一點頭暈就會緊張,擔心出現了發病的先兆;就連身上起了一個小疹子,都要聯想是不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隔離期間,曹廣父母在北京時間早上5點、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時間晚上9點時,會準時守在電腦前聽兒子匯報體溫。“哪怕我晚報了一分鐘,都會讓他們整天心神不寧。”等到曹廣相對安全的那一天,曹廣愛人給兒子講述了這些經歷,10歲的小男孩聽到后哭著求媽媽立刻打開電腦,“我要看看爸爸現在到底有沒有生病。”
終于,曹廣和吳素萍熬過了21天的隔離觀察。“在這21天里,我害怕過、傷心過,但同時也感動過、欣慰過。它讓我懂得了。‘活著是一件多么幸福而美好的事情。”4月14日,他們走出了隔離室。
而3月17日與曹廣一起給第一例埃博拉患者診療的普外科主任蓋斯姆,沒有闖過埃博拉的鬼門關,于4月1日去世。
蓋斯姆曾在武漢同濟醫科大學留學近十年并獲得博士學位,講中文時偶爾會蹦出幾句地道的武漢話。他也是中幾友好醫院第一位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去世的醫務工作者。
醫療隊員、麻醉醫生車昊經常和蓋斯姆一起工作。平時,車昊總是稱呼蓋斯姆為“蓋先生”。在車昊眼中,“蓋先生”是醫院最負責任的醫生。很多次,車昊問他為什么這么玩命地干活,蓋先生總是用五個字回答:“為人民服務。”
在吳素萍印象中,蓋斯姆很友好。每次見到,蓋斯姆都說:“老師,你好!想家沒有?”蓋斯姆還曾在胃鏡室用中文給吳素萍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朋友蓋斯姆的離去也讓曹廣悲痛萬分。“這對我們普外科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作為醫生,對于死亡并不少見,但是真切感受到突發的疾病無聲無息地襲來,心中還是充滿了無奈。”
“他說他有很多愿望希望能早日實現:他想在這家醫院多向遠道而來的中國專家學習,以提高自己的手術技術,等練好了技術后,能去其他一些稍微發達的國家去當醫生。他還想和夫人一起生5個孩子,而現在已經有了一兒一女和一個正在妻子腹中的胎兒。為了他們,他寧可累一些,也要賺更多的錢,好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有機會再去中國學習,再去看看那個曾經屬于他的大學校園,再去看看那些曾經教導過他的老師。”曹廣說。
“埃博拉恐慌”比疾病影響還大
埃博拉疫情期間,為了盡可能切斷傳染鏈,醫療隊的例行會議都改在醫院操場舉行。
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郊區的中幾友好醫院,曹廣所在的中國第23批援幾內亞醫療隊的19名醫護人員已在這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兩年。
2012年4月投入使用的中幾友好醫院,是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期間,中國向非洲國家承諾援建的30所醫院之一。當年8月,中國醫療隊抵達科納克里,“我們剛來時,醫院還沒有步入正軌,病床大都空著,病人的治療環境很好。而現在,醫院的120張病床總不夠用。”孔晴宇曾向媒體回憶說。
“對具體參與的醫生來說,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從報名那天起,其實就做好了遇到各種困難的準備,只是這次的困難比較大,甚至威脅到了我們的生命安全。”曹廣說。
當地時間8月20日,他們回到中國。四天前,由北京友誼醫院10名醫護人員組成的中國第24批醫療隊,和北京市疾控中心傳染病所副所長楊鵬、地壇醫院傳染病專家李鑫、協和醫院重癥監護室副主任隆云等醫療專家,接過重任,來到埃博拉陰云籠罩的幾內亞。
22日,專家組參加世衛組織召開的例會,了解疫情最新動態。會后,他們對駐地進行了一次徹底消毒。李鑫描述說,大家身穿防護服,戴著護目鏡和口罩,每個人都背著幾十斤重的消殺工具,“汗流浹背,毫不含糊”,經過3個多小時工作,終于完成了消殺任務!當晚,一鍋牛肉面是對專家們的報償。
這幾天,楊鵬忙著給中資企業做防病與健康知識培訓,“晚上經常停電,要抓緊時間備課。”在他看來,“埃博拉恐慌”比疾病影響還大,雖然病死率高,沒有特效藥,但只要正確了解并掌握傳播途徑,做好個體防護,就能保證安全。
對于恐慌,曹廣也有切身感受,“我在這邊看到一個紀錄片,內容就是講述人們在遭遇疫情時候的表現。片子說在疫情中死亡的人,很多是因為恐懼。還假設說如果有1萬人死于疾病本身,就會有5萬人死于恐懼。就我而言,我還是外科醫生,當時盡管僅處于健康隔離觀察,但內心的糾結還是難以超脫”。
李鑫是自己報名要求來到幾內亞的。8月14日上午,他正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討論中醫藥治療埃博拉出血熱問題,接到醫院緊急通知,“說是明天就出發,前往幾內亞。”
李鑫早已習慣“臨危受命”:2003年進駐非典病房;2007年遠赴新疆,完成一年援疆任務;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發,第一批進駐甲流病房此后,他常年工作在艾滋病診療一線。如今,李鑫正在攻讀西學中第二個博士學位。
在中幾友好醫院完成交接工作后,李鑫和曹廣合了一張影。此時,另一個“重災國”利比里亞的首都蒙羅維亞,中國援利比里亞醫療隊所在的利比里亞首都醫院,美國、埃及的援助醫生三四個月前就全部已撤離了,而9名中國醫生至今仍堅持接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