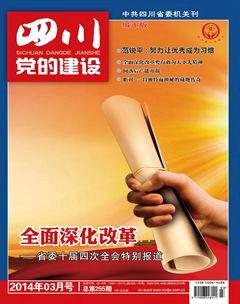八面來風
(責編:張微微)
文學告訴你……
●文/莫言

我們應該用我們的文學作品向人們傳達許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蓋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如果房子蓋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們要讓人們記起來,在人類沒有發明空調之前,熱死的人并不比現在多。在人類沒有發明電燈之前,近視眼遠比現在少。在沒有電視之前,人們的業余時間照樣很豐富。有了網絡后,人們的頭腦里并沒有比從前儲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沒有網絡之前,傻瓜似乎比現在少。
我們要通過文學作品讓人們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們失去了旅游的快樂,通訊的快捷使人們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過剩使人們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們失去了戀愛的能力。我們要通過文學作品告訴人們,沒有必要讓動物和植物長得那么快,因為動物和植物長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沒有營養,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藥。
我們要通過文學作品告訴人們,貪欲刺激下的病態發展,已經使人類生活喪失了許多情趣且充滿了危機。
我們要通過文學作品告訴人們,悠著點,慢著點,十分聰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給子孫。
我們要用我們的文學作品告訴人們,當人們在沙漠中時,就會明白水和食物比黃金和鉆石更珍貴,當地震和海嘯發生時,人們才會明白,無論多么豪華的別墅和公館,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團泥巴。
我們的文學真能使人類的貪欲有所收斂嗎?結論是悲觀的。盡管結論是悲觀的,但我們不能放棄努力,因為,這不僅僅是救他人,同時也是救自己。
(摘自莫言在東亞文學論壇上的演講)
北京十一學校的幾件“怪事”
●文/崔永元
北京十一學校里發生的很多事都很“奇怪”。第一件事,該校的李希貴校長有一次陪我到學校各處看看。我們到了一間教室,一開門,那里有兩個孩子在自習,李校長馬上說:“對不起,打擾你們了。”離開的時候校長又說了句:“對不起,打擾你們了。”這是我第一次見一位校長這樣。
第二件事,那天我拿出一支煙在學校里抽,忽然聽到有個學生說:“誰在抽煙?”然后旁邊的人就說“崔永元老師在抽煙。”但那個聲音毫不遲疑,接著說:“把煙掐了!”我趕緊把煙掐了。這雖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們平時很少見到。我想,這個孩子是在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這個學校是他們的,他們說了算!
還有一次我去參加該校狂歡節。我是倒數第二個上臺,校長是倒數第一個。我很自信,我想當我和校長上臺時,孩子們的歡呼聲一定會更大。結果輪到我出去時,臺下的雪球鋪天蓋地地砸過來。而我很快發現,更多的雪球是給校長準備的。我知道,誰被雪球砸得多,誰就更受學生的愛戴。讓孩子們覺得學校是他們的,我認為這件事太重要了。因為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這樣,當孩子們在學校時認為學校是他們的,當他們走上社會時,他們才會覺得國家是他們的,才會真正做到“匹夫有責”,否則他們永遠只是旁觀者。
(摘自《解放日報》)
以理性點亮歷史
●文/熊建
“民國時期京滬鐵路全程僅需8 小時”、“淞滬會戰國軍炸沉日艦‘出云號’”、“張學良晚年后悔發動‘西安事變’”……網上經常能看到這類新穎獨特的“歷史新知”,雖然大多經不起考證,可每次出現都會引起大量的關注、轉發、評論,而辨偽的聲音往往堙沒無聞。
這些段子的供給方——始作俑者,抱著什么樣的心理不得而知,但是從需求方來看,其能屢屢蒙騙世人卻有著天然的土壤——不少人缺乏歷史理性。
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國人喜歡了解歷史、評論歷史。其實不對,因為如果那樣的話,人們應該更愛看裴松之注的《三國志》,而不是《三國演義》。中國人其實是喜歡歷史故事。這一點,清代97 歲中舉的郭鐘岳說得好:“呼鄰結伴去燒香,迎面高臺對夕陽。錦繡一叢齊坐聽,盲詞村鼓唱娘娘。(《甌江竹枝詞》)”
過去我們一直靠勾欄瓦肆里的“負鼓盲翁”來普及“歷史知識”。即便今天,人們歷史知識的積累,更多也是停留在教科書時期;但是對歷史知識的需求,卻又遇上“快閱讀”時代。正是這種錯位給大量似是而非的歷史段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市場經濟中,如果你的需求層次低,那么供給的檔次就不會高。對于真假參半的歷史段子,我們要提高免疫力和辨別力。
(摘自《揚子晚報》)
根本沒人注意你
●文/劉曉鷗

圖/CFP
朋友的女兒畢業于北京某名牌大學,后到英國讀研究生。朋友是個虛榮心強的人,恨不得讓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女兒多優秀。有時和對門鄰居一起乘電梯,互問兒女情況,她總算找到炫耀的機會,可下一回再見面,又談起同樣的兒女話題,人家根本就沒印象,讓她很是郁悶。
美國學者馬克·鮑爾萊因在《最愚蠢的一代》中有這樣一句話:“一個人成熟的標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發生在自己身上99%的事情,對于別人而言沒有任何意義。”我們這些普通人實在沒有必要在意別人的評判議論,因為根本沒人注意你。所謂“人言可畏”,那也主要是對阮玲玉那些名人而言,而平頭百姓,根本沒有值得外界評頭論足的新聞價值。
即便是紅極一時的明星,想引人注意也不是件容易事。所以,常見那些明星出演的影視劇即將上映之前,就往往故意鬧點真真假假的緋聞,或發生情變,或夜店買醉,或與導演鬧翻,或另結新歡,或朋友生隙,花樣百出,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引人注意,以換取收視率。
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就會輕松很多。既然沒人注意,我們堂堂正正做人,就不會再留意那么多的風言風語,不會給自己增添那么多精神負擔,就會坦然自若干自己想干的事,直抒胸臆說自己想說的話。
(摘自《今晚報》)
被科技盜去的時光
●文/薩姆·利思

圖/楊永
從小我就為數字而著迷,尤其是那些難以統計的數字。在我們一生的時間分配當中,25年在睡覺、15年在工作、6年在吃飯、1年在上廁所,甚至還有8年的時間在發呆;一生中要花費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刷牙才能杜絕口腔問題,并可以因此延長幾周的生命;人的一生中花在接吻上的時間大約是四周……
當然,這些列表上的時間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更新。比如,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生命中的相當大一部分時間都在和互聯網打交道。一項新近的研究表明,目前人一生中至少有5年時間用于上網。
邊走路邊在頭頂舉著手機尋找3G 信號:3 周;翻調料柜,尋找食譜里面一種并不重要的配料:8 天;尋找最合適的手機套餐、水電費、電視和互聯網交易資費:7 個月;一邊假裝照顧孩子一邊在智能手機上玩憤怒的小鳥、水果忍者游戲:11 個月;徒勞地按F5 刷新頁面,希望收到某人的郵件:3 周;等待人工服務重置自動付款機:6 周;等待買來的水果慢慢成熟,最終卻將早已腐爛的水果通通扔掉:26 個月,諸如此類。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長久以來人們期望技術帶來休閑生活的夢想,在我們行將就木之前早已破滅。
在后消費時代的不斷變化中,對科技文明無休止的欲求給我們創造了更多的休閑時間,同時又出現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誘惑使我們去浪費這些時間。
(摘自《青年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