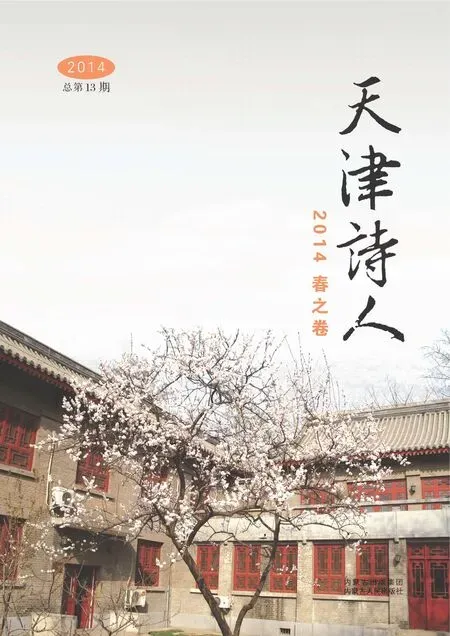一首詩(shī)寫了30年
徐敬亞
我開始寫詩(shī),由于兩個(gè)人。一個(gè)是普希金,一個(gè)是賀敬之。
1971年深秋,在長(zhǎng)春昏暗的小屋里,一本《歐根·奧涅金》和《普希金抒情詩(shī)》讓我讀得如醉如癡。俄羅斯式的憂傷,多少年深深影響在我的心里。
1972年春夏,在九臺(tái)縣卡倫公社雙泉公社的玉米田邊,每天早晨我都大段大段背誦賀敬之的《放歌集》。最后幾乎把整本詩(shī)集背下來(lái)了。
在七十年代初的很多場(chǎng)合,一個(gè)年輕的東北語(yǔ)文代課教師,總是當(dāng)眾念誦自己的詩(shī)。在與朋友的書信贈(zèng)答中,在大大小小的婚禮上,在學(xué)校的新年晚會(huì)運(yùn)動(dòng)會(huì)上……我的那些所謂的致辭都非常個(gè)人化,學(xué)著普希金的口吻(普有四分之一的詩(shī)是寫在女人披肩手絹上)。而人們的世俗贊譽(yù)也給我?guī)?lái)了最初的創(chuàng)作沖動(dòng)。那些略帶憂郁,略帶詼諧的句子,和當(dāng)時(shí)的政治背景很不一致,投稿是不可能的。
1976年10月后,我開始投稿。可能由于特殊的年代,在近十年的創(chuàng)作中,我的詩(shī)中并沒有太多出現(xiàn)普希金那種個(gè)人化生活化的傾向。我寫的大多數(shù)詩(shī),都是給雜志編輯們看的,是給所謂讀者看的。或者說(shuō)是為了所謂文學(xué)史而寫作的。所以我至今不敢出版詩(shī)集。
但《我告訴兒子》實(shí)實(shí)在在是給兒子寫的,給自己寫的。
我的兒子取名懷沙,不是文學(xué)的矯情。沒辦法,他生的那一天正是端午。
1984年,是我一生心情最不好的一年,兒子虛三歲。
寫詩(shī)的人都知道,“告訴兒子”,其實(shí)是告訴我自己。在整個(gè)世界向我壓來(lái)的最無(wú)著落之際,對(duì)著兒子自言自語(yǔ)。
忘記了這首詩(shī)最開始寫作的季節(jié)。可能夏天也可能秋天。
王小妮有一首詩(shī)寫出了那一年的殘酷:
那個(gè)冷秋天呵!
你的手
不能浸泡在冷水里
你的外衣
要夜夜由我來(lái)熨
我織也織不成的
那一件又白又厚的毛衣
奇跡般地趕出來(lái)
到了非它不穿的時(shí)刻!
那個(gè)冷秋天呵
你要衣冠楚楚地做人
…………
我本是該生巨翅的鳥
此刻
卻必須收攏翅膀
變成一只巢
讓那些不肯抬頭的人
都看見
讓他們看見
天空的沉重
讓他們經(jīng)歷
心靈的萎縮!
那冷得動(dòng)人的秋天呵
那堅(jiān)毅又嚴(yán)酷的
我與你之愛情
王小妮《愛情》(1985年)

這是我的詩(shī)人妻子、我兒子的母親在特殊的年代,惟一一次在我們之間使用了“愛情”這個(gè)詞。而我九十年代在一篇文章中,也寫過(guò)對(duì)這首特殊詩(shī)的幾段評(píng)價(jià):
“第一次讀這首詩(shī),我首先為‘詩(shī)’這種藝術(shù)感到驕傲!在苦難像鵝毛大雪一樣降臨時(shí),誰(shuí)能夠解脫我們?什么藝術(shù),能與它的柔弱與堅(jiān)強(qiáng)相比?幾百個(gè)字組成的短短幾行,代替了全部戰(zhàn)爭(zhēng)中的勇氣,也代替了基督發(fā)出的全部饒恕……
任何天才的文字編造,都不能給一個(gè)女人這種切膚的疼痛和堅(jiān)毅!……
我終于相信了曾經(jīng)讀過(guò)的、歷史上那些用苦難真情蘸著血寫下的詩(shī)篇。王小妮,從來(lái)就不是柔弱的女人。她具有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cè)诖箫L(fēng)雪中奔赴千里萬(wàn)里的信念與勇氣!……她的身上絲毫沒有女人那種思緒的混亂與糾纏。沒有把自己作為低等動(dòng)物向男人獻(xiàn)媚或故做高深的、或卑或亢的作態(tài)……
應(yīng)該垂淚鼓掌的是:歷史傷害一個(gè)詩(shī)人,可能意外地打破了她詩(shī)的一種僵眠狀態(tài)。它在制造人間苦難的同時(shí),可能恰恰送給了詩(shī)一根根飛起來(lái)的羽毛。盡管這羽毛上會(huì)滴下帶血的淚水。常人身上的傷痕,總會(huì)脫痂總會(huì)痊愈。而詩(shī)人發(fā)達(dá)的淚水卻永不會(huì)干涸。她那帶著深深劃痕的精神絲綢,不安地起伏著,在比常人更加疼痛的精神之病的翻滾中,她將孕育出心中強(qiáng)大的反力,從而把一種可怕的不安氣息,通過(guò)傷心的渠道,無(wú)形地注入時(shí)代……
詩(shī)人,它的肉體在代替著自己的靈魂受難。而它自己的靈魂卻在代替其它的肉體超度。那靈魂常常越過(guò)了它本身的傷疤,而把放大了的惡毒呼吸,噴向全體人類。這不是靈魂的高尚,也不是肉身的心胸狹隘,更不是形而下的報(bào)復(fù)--這僅是歷史喚醒詩(shī)人的另一種不友好的方式。也同時(shí)是詩(shī)人作為證據(jù),交付給人類文明法庭的一滴真實(shí)的眼淚……
在不幸降臨之時(shí),我也曾伏在我的肉體上哭泣,但我現(xiàn)在卻簡(jiǎn)直慶幸:回頭凝望那走過(guò)來(lái)的人生崎嶇,我寧愿發(fā)自內(nèi)心地為兇手們追贈(zèng)變了形的獎(jiǎng)杯……”
這就是《我告訴兒子》最初的寫作背景。
第二次改是1999年。兒子18歲。我51歲。
怎么改的記不得了。
那一年兒子即將上大學(xué)。我正在全國(guó)飛來(lái)飛去。
2013年,今年,第三次改。兒子32。我65了。
這次修改很痛快。我再不考慮什么詩(shī)不詩(shī)。想怎么寫就怎么寫。
就當(dāng)是與兒子對(duì)話,與自己對(duì)話。
對(duì)于我,這不是一首詩(shī),或者說(shuō)不是拿來(lái)發(fā)表的那種詩(shī)。因此看到有的評(píng)論我的感覺十分怪異。你們?cè)u(píng)的是詩(shī)啊。而我寫的是一個(gè)父親的話啊。和兒子說(shuō)話,你能說(shuō)哪句必要哪句不必要。
說(shuō)得精彩的部分,是我們最終與生活與生命達(dá)成的默契。說(shuō)得不好之處,是我們還在和這個(gè)無(wú)聊的世界糾纏。
終于明白了一個(gè)道理:詩(shī)人角色,注定終生。
小說(shuō)家和畫家可以放下筆轉(zhuǎn)身進(jìn)入人群,他的心里殘存的人物與色彩之念也可能永不中止,但其病不足致命,尚可能重返人間。而詩(shī)人卻注定一去不返。詩(shī)是一個(gè)不可擺脫的魔咒。他與世界平行的念頭足以腐蝕一個(gè)人全部的思維方式、語(yǔ)言方式,誘導(dǎo)一個(gè)人的性格產(chǎn)生偏離,進(jìn)而致使全部生命方式發(fā)生變形。這就是為什么一個(gè)人寫了詩(shī)之后再難回頭。
兒子,對(du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