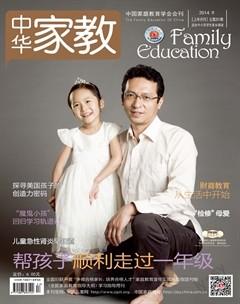巧用“機會教育”幫女兒學數學
盡管我和太太年紀都很大了,女兒年紀卻還小。每每聽到周圍中國朋友的孩子如何有出息,總有些壓力。我們經常對彼此說,也對孩子說:“我們不和別人比,只要自己盡力就行。”但完全否認這種壓力顯然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我數學好,英語差,所以好幾次“語重心長”地對女兒說:“爸爸英文不好,你只有靠自己努力了。爸爸會幫你學數學,但你也要自己配合。”數學怎么個幫法,說來容易,做起來卻不那么容易。
小朋友不會喜歡上課式教育,勉強聽了,事后也很容易忘掉。何況在學校聽老師上課是沒辦法,干嗎回家還要聽爸爸媽媽上課?一次偶然的機會,太太說了一句“機會教育”讓我恍然大悟。
于是,我開始留意女兒在家庭作業中出現的機會,進行“機會教育”。從三年級開始,她每次做完數學作業都要讓我過目。做錯的題目我會指出,但不許她“改正”,否則老師就以為她什么都懂了,從不犯錯。有時候她做對了題,但方法欠佳,我也會指出。
做除法總是比較困難,她至今還沒完全掌握。我就對她說不要著急,連計算機做除法都比加減乘要慢得多。她瞪大了眼睛:“真的?”我告訴她以前的計算機做加減乘與除法的時間比大約是1:5,現代計算機是1:2.3,爸爸測試過的。
她喜歡圖形規律,但有點走火入魔,連做選擇題也要從四個選項中找點“規律”。我告訴她尋找規律是一個很寶貴的優點,門捷列夫從已知的50多個元素中尋找規律,從而制作出包含近100個元素的化學元素周期表。但選擇題答案的字母順序是隨機的,要尋找規律就是浪費時間了。
除此之外,我更喜歡抓住日常生活中的機會,引經據典,激發她對數學的興趣。
有一次出去旅游,她問了一個關于金字塔的問題,我就給她講了關于多面體的歐拉定理:多面體的頂點數V、棱數E及面數F有簡單關系:V+F-E=2。結果,有段時間她看到任何多面體,不論是華盛頓紀念碑還是水晶蠟燭臺,都會情不自禁地停下來驗證歐拉定理。
當然,這種“機會教育”需“投其所好”。我有一位朋友是相當有名的北卡大學教堂山校區的博士。有一次我和他兩個女兒(大女兒和我女兒一樣大)聊天,我女兒也在場。我給他們講了拉丁方的故事。4種花色的撲克牌共16張,如何把它們排成4X4方陣,每一行每一列不能有同樣大小、同樣花色的牌。現在假定一副牌有6種花色,能不能把6種花色、6種大小的牌排成6X6方陣,要求與前面的4X4相同。我也給她們講了問題的起源——腓特烈大帝閱兵的真實故事。我告訴她們,大數學家歐拉這次也出錯了。自從知道了“歐拉定理”,歐拉成了女兒的偶像,偶像出錯,她簡直覺得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我接著對朋友的女兒說:“這個問題最后是你爸爸學校的數學家解出來的。”大家可以想象,小女孩聽到這兒有多么激動,她說要回去告訴爸爸。
因為我見縫插針的“機會教育”,女兒覺得數學是一門饒有趣味的學科,學習的熱情也大大提高。當然,要進行這種“機會教育”,施教者必須博覽群書,且過目不忘。
(樊一中 上海松江人,現居美國。著有《華爾街數學——我的數學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