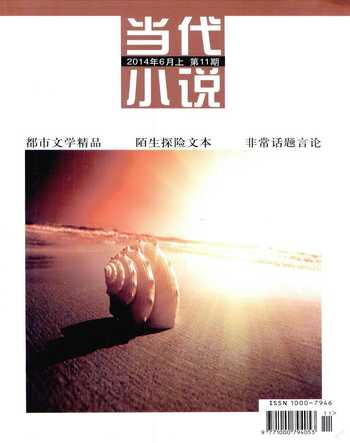刺猬,或者蝴蝶
徐先進
關上房門的一剎那他突然產生一絲疑惑,范麗真的已經離開了家,跟著她的老板到南方去了嗎?她說8點鐘從家里動身,然后打的直接去機場,和老板在機場會合,乘坐10點鐘的班機飛往南方。現在還不到9點,她會不會因為什么意外還滯留在家里?比如。從手機上查到航班誤點。她要推遲去機場的時間。亦或許。老板臨時改變主意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取消了這次可有可無的飛行?因為范麗說過。這次去南方,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任務,作為新提升的銷售業務主管,老板想帶她到南方那個城市熟悉一下圈子,打通一下人脈。老板是在那個城市起家的,對那個城市有著特殊的感情,至今那個城市還有他不少的老主顧,保持著生意上的來往。
他還是不自覺地掏出了鑰匙,在鑰匙插入鎖孔之后他又猶豫了片刻,然后像是被誰推了一把似的果斷旋轉,迅速打開了家門。不知為什么,他想都沒想就直接去了衛生間。衛生間的毛玻璃門是關著的。里面隱約有一個灰蒙蒙的人影。他的心隨之快速跳動了兩下。但等他定睛再看時,灰蒙蒙的人影卻霧一樣的消失了,他才確信剛才的一瞬間不過是產生了一絲幻覺。他隨即推開毛玻璃門,往洗臉池的右側掃了一眼,那里有一個擺放洗漱用品及化妝品的無門柜子,擺放在玻璃擱板上的化妝品數不勝數,高高低低占滿了兩層擱板。但他一眼就發現,那兩瓶最高檔的化妝品不見了。不用說,是范麗帶著它們遠走高飛了。
接下來他去了臥室,先是在床沿上正襟危坐。目光掃視著一排排緊閉著的柜子門。不用打開它們他也能猜得到。那件范麗非常喜歡,但平時很少穿的駝色風衣應該是不見了。同時不見了的還應該有其它幾件物品。范麗雖然表面上喜歡追逐潮流,實際上她是一個有些保守的人,骨子里始終隱藏著一股小家子氣,一股在小縣城度過青春期后烙在骨子里的猥瑣,以及為了掩飾這猥瑣而刻意表現出來的開放。他懶得再去猜測她還帶走了些什么,順勢從床沿上滑下來,一屁股坐到地板上,雙手斜斜地撐在身后,頭大幅度后仰著,目光倒視著一切。這無賴相讓他想起小時候每每遭人誤解時,他就不由自主地擺出這種不愿與人合作的姿態。
其實他很明白,為了這次出行,范麗做了不少鋪墊。范麗確定無誤地告訴他要實施這次出行是在三天前,但半個月之前她就開始打伏筆。那天下午范麗特意提前一個小時下班,回家燒了一桌好菜,并擺上一瓶紅酒和兩只高腳酒杯。他一跨進家門就被這突如其來的氛圍弄暈了,他有些懵懂地在飯桌邊坐下來。范麗端起高腳杯晃了晃里面的酒說。我知道你要問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我還是免得你瞎猜吧,今天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就是一個很平常的日子。說完她示意他端起酒杯。他很別扭地捉住酒杯的細腿舉了起來,也像范麗那樣將酒晃了晃,可他并沒有像范麗那樣抿上一小口,而是等著范麗說下去。范麗接著說,以前只顧在工作上打拼,忽視了家庭生活,今后要彌補這方面的缺陷,其實工作不就是為了生活嗎,我們不能本末倒置。他聽后感覺有些欣慰,又有些不置可否。按說生活和工作的關系應當是兩條簡單的平行線,像兩條鋼軌一樣,除了在一些重要的節點上換軌。它們很少糾結在一起。可現如今的情形誰能說得清呢,工作的邊界在無止境地拓寬,已經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這一代人已經永遠不能像他父母那樣,將工作和生活區分得涇渭分明,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完全投入到家庭生活,其間看不到任何工作的影子。就像工作這檔子事不存在一樣,完全自足地享受家庭生活。沒過幾天,范麗又如法炮制。在繞了一圈家庭情趣之類的話題之后。她像是不經意地抱怨起來,說銷售主管這個職務是很煩人的,免不了經常出差。他沒覺得什么不對勁,反倒寬慰她說,作為銷售主管,出差聯系業務是天經地義的,沒必要為此糾結。直到三天前,范麗告訴他要和老板飛一次南方那座城市時,他才感到事情變得復雜起來。他問范麗,和老板一起去?就你們兩個人?范麗晃了晃高腳杯里的酒說,是的,這次去沒什么實質性的事務。就是熟悉一下那個城市他的朋友圈子。他沉默下來。咂摸了一下范麗所說的話,過了一會兒他猛地喝了一口酒說,你老板他為什么要這樣做?范麗沒有解釋老板為何要這樣做,而是說,你要相信我,不然我可以隨便撒個謊把這件事情瞞過去。他很想大度地謝謝她的坦誠,可是一股說不清的沮喪讓他失去了冷靜,他沖口而出,你不許去,一對孤男寡女沒什么特殊的事務飛到另一座城市,想想就叫人受不了,你的同事會怎么說,我的朋友知道了會怎么說?我的父母知道了我還有何顏面?范麗也沉默了,她不停地晃動酒杯里的酒,有一下沒有把握好晃動的幅度,酒被灑了兩小片出來。但他十分清楚,范麗是不會輕易屈服他的,她那由骨子里的猥瑣而反生出來的傲慢會讓她一條道走到黑。果然她放下酒杯說,信不信由你,反正事情無法改變。末了她還感嘆了一句,你什么時候才能改掉小縣城里養成的小家子氣!
再次關上房門他顯得有些決絕,門鎖的咔嚓聲還沒有消失,他就像一只被人追趕的小兔子噔噔噔地下了樓。出了樓道,他掏出手機看了一眼,還好,時間還算充裕,于是他放緩腳步,緩慢步行到小區門口。出了小區就是一條主干道,雖然上班的早高峰已經過去,但大街上仍然車流如織。城市就這樣連軸轉地忙碌著,沒有一刻的消停。他看見一輛打著“空車”牌子的出租車,伸手去招,可人家理都沒理就直接從他身邊開走了。過了好一會兒,才又有一輛空車駛來,他招了招手,出租司機問他去哪兒,他說去火車站,司機說火車站不去就把車開走了。連著攔了幾輛空車,司機都說不去火車站,說那里堵車堵得厲害。看看時間耗得差不多了,最后他強行上了一輛出租車,答應多付二十塊錢的車費,司機才沒有再啰嗦。
臨近火車站,車子果然堵得厲害。看著車子拱豬一樣一拱一停,他不免著急起來,這樣下去,肯定會錯過接站的時間。于是他干脆下了車。從車縫里穿行而過,花了一刻鐘左右終于來到了出站口。他來不及擦一下額頭上的汗,趕忙從口袋里掏出一張折疊的紙。展開后雙手高高舉了起來。這是一張八開素描紙。上面印著一只彩色蝴蝶。昨天晚上,在和臨風確認了接頭方式后,他在網上搜了一個多鐘頭,才決定將這只他自認最漂亮的蝴蝶打印下來,粘貼到素描紙上。
出站口人流涌動,他不清楚臨風所乘的那班車是否晚點。如果不晚點的話,正是這班乘客出站的時候。他很想打個電話問問臨風。可是臨風昨晚有言在先。今天在見到她人之前,不要再打電話聯系。他當時想,她要的可能就是這種神秘感吧。于是他趕緊把目光投向一張張涌動的臉,努力把手中的紙舉得更高。
人們對他有些滑稽的舉動無動于衷。一個個奔命似的急于逃離出站口。眼見著人群越來越稀疏。他的心情漸漸低落。難道臨風所乘的這班車真的晚點了?或者是她后悔了,單方面取消了這次約會?最糟糕的是,她一開始就沒打算赴這次約會,只是想戲弄他一下?對于初次見面的人,不讓打電話聯系,怎么說都像是一個拙劣的借口。想起關于網友約會的種種傳聞,加上自己如此滑稽落寞的樣子。他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一想到此刻范麗正和她的老板肩并肩地在天上飛,他還是咬牙堅持下來。再等等吧。
身后傳來一聲細細的咳嗽。他轉過身來,一下子顯得手足無措,站在他面前的正是臨風。臨風笑盈盈地看著他,落落大方地向他伸出一只手來說,你就是玉樹先生吧,看上去比視頻上的帥氣。他臉唰地一下紅了,遲疑著將手伸了過去,輕輕碰一下臨風的手指就又收了回來。他急于想說一句輕松俏皮的話來掩飾目前的窘態,可說出口的卻是一句非常平庸的大白話,你好,很高興見到你。臨風果然恥笑他說,搞得這么正經,跟國家大使見面似的。他再一次臉紅,內心懊惱地想,別看在網絡上還算放得開。一旦跌入現實生活中,自己還真像范麗所說的那樣,改不了在小縣城培養出來的小家子氣。和范麗相比,自己實在是差了一截,范麗雖然骨子里也同樣有這股小家子氣,但早已被她外在的形象遮蔽得嚴嚴實實。
接著他又為自己接下來的一句話感到懊惱,在沒找到貼切的話題之前,為了避免尷尬的冷場。他問她,要不,我們先住進旅館再說?好在臨風一點也不做作,她譏笑說,你也太急了點吧,我才不想這么快進旅館呢,說不定進了旅館之后我們很快就會分手,男人不都這樣嗎。得手之后趕緊找個理由溜掉。他有點傻地笑了一下,說出的話仍然顯得笨拙,像表決心似的。我不是你說的那種男人。臨風咯咯笑了起來,反問他,那你是哪種男人?至少不是好男人,好男人不會背著妻子出來跟別的女人幽會。這就合上他們以往在網絡上說話的語調了。他有些輕佻地說,那你也承認自己不是好女人了,好女人更不應該背著丈夫出來和別的男人幽會。讓他沒想到的是,聽他這么一說,臨風的臉迅速黯淡了下來,嘴里冒出一句冷冰冰的話,你歧視女人。
,就這樣邊說邊走,他們穿過站前廣場來到湖邊。這個湖面積很大,是這個城市的名片之一。這處的湖邊其實就是站前廣場的邊沿,一條百米來長的木板臺子懸空架在湖邊,臺面高出湖面六、七十公分,臺沿上坐滿了人,有單獨一人的。有五、六個一伙的,當然也有很多成雙成對的。他們大多把腿從臺子上放下來,不少人用腳試著去戲水。他想,這些成雙成對的人當中,會有多少對像他和臨風一樣,不是夫妻呢?但鑒于臨風剛才的突然變臉,他不敢再貿然亂說。好在臨風又恢復到輕松大方的姿態,看著滿湖怡人的風光,她興奮地說。我們先在這里坐會兒吧。于是他們找到一處空臺沿坐下去,臨風一坐下來就急于用腳去戲水。
不知臨風說他看上去比視頻上帥氣是不是真心話,他倒是真切地覺得,臨風看上去比視頻上更漂亮。她皮膚白皙,身材高挑,穿著入時,氣質高雅。如果不是近在眼前,他打死也不相信,這樣的女人會從網絡上走下來,偷偷地和他幽會。他覺得,這個時代,尤其是這個時代的女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了。
一年前他和臨風相遇于一個網絡論壇。那時他工作不順,也許真是小縣城里養成的小家子氣在時不時地作怪吧,新來的老板老是說他保守僵化甚至迂腐。工作上業績平平倒也罷了,讓人忍受不了的是。同事間的關系也變得微妙起來,為了得到新老板的賞識,大家暗自較勁,甚至不惜編造謊言排擠他人。他沒有把煩惱告訴范麗,而是一頭扎進網絡。他對網絡不是很熟悉,經常像逛大街一樣東溜一下西溜一下,后來他溜到一個帶點文藝性質的論壇里,看了幾篇文章后,勾起了他對高中生活的回憶。他讀高中時喜歡在學校附近的一個租書店里租小說看,他租的小說很雜,武打的言情的科幻的甚至名著他都租來看。說起來他能夠和范麗走到一起。恐怕還要歸功于這租來的小說呢。有一天中午他忘了把租來的小說放進課桌抽屜里就去食堂吃飯,吃完飯回到教室發現范麗正捧著那本小說看得入迷,他沒好意思要回來,范麗也沒有立即把書還給他,而是過了兩天把書看完了才還給他。當然他們沒有就此親近起來,但幾年后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誰能肯定不是那時埋下的種子呢。世間的事情別看它千變萬化。其實十有八九是由種子的性質決定的。他就在這個論壇駐足下來,注冊時發現他喜歡的“玉樹臨風”早已被人搶注,他干脆取其一半注冊了“玉樹”這個用戶名。沒過幾天,壇子里有一個叫“臨風”的找到他。說他霸道。把她喜歡的“玉樹”給搶注了。當然她最喜歡的也是“玉樹臨風”,“玉樹臨風”被人搶注了她就想注冊“玉樹”,結果只能是一退再退注冊了“臨風”。也許是他看了不少小說的緣故吧,他在這樣的論壇里混得很是愜意,跟的帖子輕松活潑,不乏幽默。他回答她說,那我們結合成一體,就“玉樹臨風”了。從此兩人漸漸熱絡起來,彼此交換了QQ號碼,先文字交流,進而視頻聊天,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他家的電腦突然壞了。兩人的交流也就戛然而止。一個月后他換了一臺新電腦,不知是不是那小家子氣又跳出來作怪,還是在單位里多多少少順氣了一些,他不想再面對臨風了,他幾乎不上QQ,即使上也是隱身。大多時間是看看新聞,潛水逛一逛文藝論壇。直到三天前,范麗明確無誤地告訴他要和老板飛一次南方時,他才帶著極大的委屈打開了QQ,臨風就像是一直等著他似的,她沒有責備他這么長時間的不告而別,而是一上來就和他熱乎地聊了起來。越聊他心里越委屈,說話的方式由自嘲向自虐的方向演進。臨風呢。也像是受到了極大的委屈。她火上澆油。最后兩人都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委屈的人。那么好吧,前天晚上他向她說。我們兩個最委屈的人能否見上一面?臨風立馬答應了下來。
湖邊的人有增無減,走了一撥又來了更多的一撥,他們一個個顯得悠閑至極快樂至極。雖然火車站就在身后不遠處,但聽不到一丁點嘈雜的聲響。微風吹拂著湖面,水面漾起絲綢抖動一樣的微瀾。女人們的長發也被吹得飄逸起來。湖對面這個城市的地標性建筑巍然屹立,像一個不動聲色的傾聽者。似乎時時刻刻在提醒人們,這是一座優雅的城市,一座有耐心的城市。他不知道臨風是不是被這樣的情致感染了,她顯得特別安靜,一改剛見面時的熱絡大方,大多時間就這樣坐著一動不動,可是時間已經不早了,他提出去找個地方吃中飯。
雖然在這個城市生活不少年了,但他對這個城市的許多領域還很陌生。他帶著臨風穿過了好幾條街道。吃不準什么樣的餐館才是合適的,還是臨風比較有經驗,她從外面透過玻璃墻看到一家餐館用屏風分隔出一個個簡易的包間,她說就這家吧。兩人進去找了個靠窗的包間坐下來,將窗簾拉上。陽光透過淡橙色的窗簾滲進來,小小的空間立即充滿了曖昧的情調。在點好菜后他問臨風要不要來點酒,臨風說,當然要酒,葡萄酒。
不知你是否有過與網友見面的經驗,反正有一點是肯定的,不管在網絡上混得如何熟絡,一旦在現實中見面,還是顯得很生疏,這算不算是對人的多面性的一種注解呢?拿他自己來說,網上網下就判若兩人。臨風也只是剛見面的時候表現出輕松大方,似乎是網上風格的一種延續,但之后更多表現出沉思不語,心情不是他想像的那么好。為了避免冷場,他竭力尋找話題,很快那只粘在素描紙上的蝴蝶跳進他的腦海。他說,你喜歡蝴蝶?
臨風喝了一口酒說,我討厭蝴蝶。
他愕然,那你干嗎還讓我用一只蝴蝶迎接你?
臨風回答得極快,我想受刺激。
接著她反問他。你呢,最討厭什么動物?
他腦中開始搜索。他在小縣城出生小縣城長大。除了偶爾見到貓和狗,他對動物實在沒什么印象,小縣城里除了人似乎再沒有其它活物。不過他很快想起來,他高中畢業那年,考完高考之后,十多個同學相約去鄉下一個同學家里玩,那同學的父親在山上逮了一只刺猬用雞籠罩在家里的一個墻角處,十多個同學立即圍著雞籠看新鮮。雞籠是用竹篾編的,網眼雞蛋那么大,上方有臉盆那么大的一個洞口。刺猬蜷縮著,花白的硬刺像鎧甲一樣緊貼在身上,有人想伸手去撫摸,但由于害怕,手剛伸進洞口就又縮了回來,他也有樣學樣地把手伸進去,可他剛想把手縮回來時,范麗惡作劇地把他胳膊向前推了一把,刺猬瞬間變成一個刺球,一根硬刺扎在了他的中指肚上,他把手收回來時看見豆大的血珠不停地從刺口處冒出來。當時可能他在揣摩范麗惡作劇的意圖吧。沒來得及對刺猬產生好惡之情。現在被臨風這么一問,想想那一刻所受的驚嚇以及那種棰心的刺痛,他說,我討厭刺猬。
臨風不無譏誚,一個大男人害怕小刺猬?有什么故事吧?
他不想把這個故事告訴她,掩飾說,其實也算不上討厭,只是不喜歡而已,你呢,作為一個女人,不應該討厭一只蝴蝶呀?
臨風又喝了一口酒,她的臉越發顯得嬌艷。她不停地晃動酒杯,葡萄酒像舞女的紅裙子在杯壁上不停地飛旋。她的眼眶濕潤了,目光漸漸迷離。聲音低沉得像是從冰窖里發出來的,她說,蝴蝶是我丈夫的小三名字諧音。
臨風和她的丈夫大學同學。臨風的父母是國家干部,在那個城市有頭有臉。不時在市電視臺新聞節目里露個臉面。她丈夫出生偏遠的農村,家里窮得丁當響,姐弟三人,為了供他讀書,兩個姐姐早早外出打工。臨風的父母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還算滿意,因為他長得比較帥,可是當了解到他家的情況后,帥不帥就一文不值了。臨風癡心不改,頑抗到底,最后她的父母不得不接受現實,并走關系把他們的工作在市里安排好。都說窮人的腦瓜要么像一潭死水一動不動,要么像火車的輪子一樣飛速地旋轉,她丈夫的腦子就沒有一刻停止過轉動。他公務員沒干幾年就辭掉了,開起了一家裝潢公司。利用她父母的人脈關系迅速把公司做大做強。她不無炫耀地對她父母說,我的眼光不錯吧,她父母點頭稱是并做出深刻反思。感嘆說。人才是第一生產力呀。更讓她得意的是。發達后的丈夫對她更呵護體貼,老是對她說,沒有你就沒有我的今天,你不僅是我的妻子,還是我生命中的貴人。可是誰能想到呢,半年前她的父母相繼退休。他不久就對她冷淡下來,很快她發現他在外面有了小三,通過私家偵探的調查。她知道那個小三叫胡蝶,是一個學畫畫的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
如果這是從電視或者報刊上看來的故事,他會覺得俗不可耐,但這故事發生在身邊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他還是感到很震撼。他有些不知所措,很笨拙地說,那你,這次來是想報復他?
臨風回答得很干脆,對,就想報復他。
他感到有些悲哀。自己被當成工具了。但反過來想,自己何嘗不是利用她來報復范麗呢。臨風又喝下去一大口酒,有幾分醉意地說,不過我確實討厭蝴蝶,初中的時候和一個女同學到公園去玩,看見一只非常好看的蝴蝶趴在一朵花上,我伸手去捉,結果弄得兩個手指的指肚上全是蝴蝶翅膀上的粉末,那粉末藍幽幽滑膩膩冰涼涼的,讓人心里直發毛,從此我就開始討厭蝴蝶了。
走出餐館已是下午兩點多鐘,街上人流如織。車水馬龍。臨風和他并肩走著,神情略顯渙散。他知道,接下來他們不得不面對最核心的問題,去不去賓館開房?他內心跳動得很厲害,腳步也就邁得很是猶疑。他很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并非是貪圖意外之歡,可是從臨風身上散發出來的氣息還是讓他身體不由自主地產生了躁動。他不知道臨風此時是怎樣的心態,身體對于女人來說是最可寶貴的財富,也是她們最后的本錢,如果她愿意用自己的身體去報復一個人,那說明她所受的傷害是無以復加的。現在正處在一個重要的關口,他相信此刻臨風的內心不會像她的外表這么平靜,任何一個微小的因素都會影響后面事情的走向,以至于一拍兩散。于是他委婉地問臨風,現在去哪兒?
臨風沒有立即回答。過了一會兒才低聲說,去開房。他們選擇了一家中檔的全國連鎖店,在服務臺登記后他們乘電梯來到六樓,穿過U字形的走道,他找到號房。在插房卡時他的手不聽話地顫抖起來。連插了幾次才終于把房門打開。臨風一進門就鉆進了衛生間,他則在沙發上坐下來,聞到房間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他擔心臨風會受不了,就把窗簾窗戶和房門全打開,讓房間透透空氣。
半個鐘頭后臨風從衛生間里出來,他窘迫地瞅了她一眼。從時間上判斷,她應該進行了沐浴,并且補了一層淡裝。先前柬著的頭發披散開來,衣服也換成了一件白底碎花連衣裙。她對他笑了一下,然后安靜地坐在床沿上。
他還陷在窘迫之中,雖然全身的血液在燃燒。身體在急劇地膨脹,但黑色的沙發就像是一塊巨型磁鐵,把他牢牢地吸附住。他缺氧般地呼吸著,眼前呈現出一片混沌的黑暗。要不是黑暗中傳來一個縹緲的聲音,你后悔了?他不知自己能不能最終擺脫沙發巨大的吸附力。
他也去洗了個澡,出來后發現房門已經關上,窗簾也拉起來了,他不再猶豫。直接在床沿上靠著臨風坐下來。在他伸出雙臂抱住她的一剎那,臨風像發瘧疾似的顫抖了一下,豆大的淚珠從眼眶里掉了下來。但他已經顧不了那么多了。他加大了雙臂的力量,將嘴向臨風的臉上貼過去。
世界靜得像黑洞一樣。可就在他們要倒下去的時候,門外驟然響起急促的腳步聲和大呼小叫的人聲,這聲音讓他們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動作。他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想到了捉奸。身體也隨之僵硬起來。
他坐在床沿上一動不動,等待著有人破門而入。
門外嘈雜的聲音在不斷地膨脹,不時夾雜著一兩聲尖叫,可是房門卻遲遲未被打開。這種坐以待斃的滋味很不好受,不知過了多久,他起身悄悄地走到門邊,把耳朵貼在門縫上,就在這時他又聽到一片尖叫,他要跳了。要跳?跳什么?看來這嘈雜的聲音跟他們無關,一定是外面發生了什么緊急的事情。倒是臨風很敏銳,她不假思索地說,肯定是有人要跳樓。
于是他們來不及整理一下被弄皺的衣服就打開了房門。門前擠滿了人,一個個踮著腳,脖子伸得老長,向他們隔壁房間里看去。他們在人縫里擠出一個位置,由于他們的身材都比較高,不用踮腳也能把隔壁房間里的情況看得清清楚楚。
一個男人站在窗外。只看得見他半截身子,也不知道他的腳踩在窗外的什么地方,如果撒開鉤著窗戶的手指。無疑會掉下樓去。從他的衣著和蓬亂的頭發來看。他應該是一個農民工。他黝黑的臉上滿是淚水,嘴里在念叨一個人的名字。地上滿是煙頭,中間倒伏著一只酒瓶,里面還剩有一些白酒,濃重的酒味和煙味從房間里散發出來,直嗆人的大腦。一個應該是賓館管理人員的女人站在離窗子兩米遠的地方,她反復勸說男人,讓他不要做傻事。從她不停的勸說中,大家漸漸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來這男人的妻子跟另一個男人跑掉了,他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尋找。才終于得知他們就在這個城市里。現在他只想見上他妻子一面,然后在她面前跳下樓去。女人幾次試著靠近他,但都被他激烈的警告一次次逼退,成功逼退女人后他都要大聲呼喊他妻子的名字。
樓道里又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幾個消防員跑了過來。他們分撥開門口的人群一下子沖進了房間。在和女人進行簡單的交流后,一個消防員走到門口。讓門口的人全部離開,然后反身關上了房門。人群一窩蜂地散去。爭著往樓下跑,想去樓下接著看事情的進展。
他和臨風跟在人群后面,在走道里剛拐過一個彎,就聽見后面有人呼喊,讓他們等一等。他們停下來,剛才那個勸說跳樓男人的女人跑過來對臨風說,你能不能幫幫我們,幫我們勸說一下?臨風經過短暫的沉默后一口答應下來,兩個女人又風馳電掣地跑回去。
他繼續沿著走道往前走,電梯已經被關停。只好從樓梯上下去。他想,那女人到底想讓臨風幫什么忙呢?難道他們想用女人來感化那個跳樓的男人?她自己不也是女人嗎?不過她也確實沒多少女人的味道,年齡大不說,還穿著賓館里冷冰冰的制服,她恐怕對自己的女性特征毫無信心,才讓臨風去試一試吧。
樓下站滿了人。一個個仰著頭。120救護車已經來了,消防員也在窗下放置好了充氣墊子。一個應該是指揮官的人拿著對講機不停地說著什么。他這才看清跳樓男人的腳踩在窗外墻上裝飾性的橫檔上,那橫檔不過五公分寬,能看見他一半的鞋底,只要稍一閃失,他必定無疑會栽下來。他在呼喊他妻子的名字,說她好狠心,連見他最后一面也不愿意。
他終于看見了臨風。臨風離窗子有些近了,看得見她胸部以上的部分,從動作看,她在說話,但聽不清說什么。跳樓男人也不理睬她,他仍然面朝窗外。隔一會兒就呼喊他妻子的名字,然后要么哀求、要么咒罵他的妻子。
仰著的頭有些累了,他把頭低了下來。從口袋里掏出一根煙來抽。等他抽完煙再抬起頭來。看到事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臨風已經貼近了窗子,跳樓男人雖然還在不時地喊他妻子的名字,但他卻頻頻回頭看著臨風,一邊回頭一邊說著什么,似乎和臨風對上了話。這樣相持了大約十多分鐘,他吃驚地看到。臨風隔著窗子抱住了跳樓男人的腰,跳樓男人伏在臨風的懷里放聲大哭,房間里的消防員小心翼翼地來到窗邊,把他從窗外拉進了房間。
不一會兒,消防員架著跳樓男人下來了。120的幾個醫生護士把他扶進了救護車。人群迅速地散去。
回到樓上。他看見臨風在房間里收拾東西。雖然他很清楚臨風這是要離開的意思,但還是忍不住問了一句,這就走嗎?臨風似是而非地笑了一下,點頭說,我想回去了,晚上10點正好有一班火車。他也似是而非地回笑了一下,沒做任何挽留,盡量顯出真誠的樣子說,那好,我送你上車。
把臨風送上火車。回到家已經11點多鐘了,他感覺這一天下來從未有過的累。簡單洗漱了一下他就爬上了床,很快就滑進了夢的深淵。他夢見兩個毫不相干的動物在追逐嬉戲。先是蝴蝶追著刺猬飛,然后停在一根樹枝上,刺猬攆過去停在樹枝下面,蝴蝶俯沖下來想停在刺猬的身上,刺猬瞬間變成一個刺球,刺破了蝴蝶的翅膀,藍色的汁液不斷從蝴蝶翅膀里流出來,世界頓時變得一片瓦藍。
責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