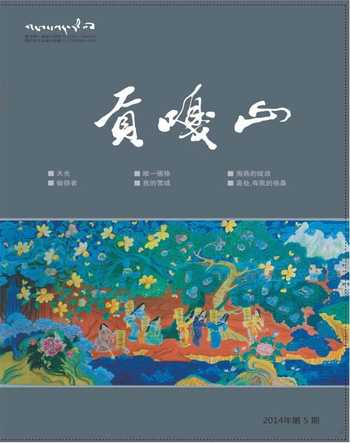唯一德格
賀先棗
三千萬年前,因為印度板塊與歐亞大陸的撞擊,青藏高原隆起。無處不在的大山,以它們的形體語言,至今還在向人們講述撞擊瞬間的驚心動魄,傷殘了卻又拼接起來的大山,更多展示的卻是讓人心動的陽剛與壯美。德格,就靜臥在青藏高原東南邊緣的大山皺折里。
一座小城,始建于藏歷第八饒迥之土龍年(公元1448年)。從金沙江邊遷到這座小城的“噶爾”家族,因受過法王八思巴稱贊其具有“四德十格”之福份,此時已經自稱“德格家”。家族名和地名由藏傳佛教教義演化而來。德格,含義豐富而吉祥,譯成漢語,簡言之,意為“善地”。這個閃光的地名,其實是一個千古的話題。
德格土司鼎盛時期,自號“德格甲波”(德格王),統轄地區包括如今四川省的石渠縣、德格縣、白玉縣、西藏自治區的江達縣、青海省玉樹自治州一部等地區,那個“天德格地德格”的說法一直流傳至今,意思就是“德格甲波”疆域遼闊,權勢無邊。集政教大權于一身的第十二代德格土司兼六世法王曲加·登巴澤仁時,德格家族的勢力更是如日中天。
時過景遷,如今,德格只是一個行政區劃的名稱偶爾讓人提及,除德格本地和相鄰地方,以及一些研究者,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德格,而德格到底不應該被人們忽略和忘記。
現在的德格,縣域幅員面積有一萬多平方公里。境內高山雪峰聳立,自然風光秀麗壯美。一座名叫“措拉”(雀兒山)的大山更是綿綿百余里,將德格全縣分隔為東西兩部份。東北部,高原草地一望無際,遼遠空曠,舒展平緩。西南邊,山勢猙獰溝深林密,峽谷縱橫,江河交錯。山上、草地上湖泊星羅棋布,湖光山色恍如幻景。行走在德格的廣袤土地上,置身于千萬年的山水間,如在夢境,如回到了遙遠歷史某一特定的時刻。
德格,是一塊可以寄情歷史又可以寄情山水的土地。
當年德格土司把自己的官寨修建在如今德格縣城的“歐普隆”溝口,不是心血來潮,因為在那個時候,德格這塊土地正在離開完全的游牧經濟,進入了牧業與農耕文明相結合的經濟時期。這塊約有5萬多平方公里土地,7萬戶人口的地盤成為了歷代德格土司表演土司絕對權力的巨大舞臺。
站在曾經受到佛學家、藏地橋梁建筑大師、藏戲開山鼻祖唐東杰布祝福過、地呈“八種吉祥”的“歐普隆”溝口遙想:只見德格土司治下的三十大部落頭人,八十小部落頭人紛紛下馬,低頭哈腰,魚貫而來,在這個傳說能挖到銀子的溝口,他們幾乎不敢仰視其實不算巍峨的土司官寨,官寨大門外或嘈雜、或肅靜,都是他們心目中德格土司的赫赫威勢。那時,這溝口的官寨豈止是號令四方的中心,還是一處不可褻瀆冒犯的圣地。
只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永遠稱為中心,就如沒有一個王權可以永恒。多少文治武功、興衰榮辱,多少悲歡離合、喜怒哀樂,都在高原的罡風里化為了傳說和記憶,散落在浩如煙海的典藉中和牧場、村莊野老的閑談里。
唯有這連綿起伏的群山還在,這蒼茫無涯的草地依舊,它們無言地見證了歷史長河經過這方水土時發生的一切,留下的一切。德格的山水中,隱藏著一個民族血液中獨有的文化遺傳密碼。如今盛行相互抄襲、快速復制,而且能把很多東西視需要統統冠以“文化”標簽。面對德格山水中生長出來的文化,現代的能人卻沒有辦法復制。他們無奈的發現,歷經無數憂患變故的德格,在高原深處保持著一種古典的沉靜和肅穆,以高原大山的剛毅,以高原江河的執著,靜靜地繼續只屬于自己的傳奇。
德格,唯一的德格。
智者說,一切都是過眼煙云。卻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德格印經院。最初,德格印經院叫做“更慶寺印經院”,是號稱大廟的更慶寺的一部分。更慶寺是德格土司的家廟之一,后來稱為德格印經院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沒有人指點,如今沒有人會想到,德格印經院是在去德格土司官寨的必經路口,然而,咫尺之遙地的土司官寨早已蕩然無跡。或許,有朵飄過的白云還有記憶,只可惜,白云無語。
在今天看來,印經院不過就是一座三樓一底的建筑,可卻經歷了四代土司、三十多年時間,由不知數的信眾以支差、捐贈的方式才建成。印經院的全名很長,譯成漢語是:德格吉祥如意多門大聚慧院。清朝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曲加·登巴澤仁發宏愿,收羅天下佛經于一堂,傳播光大弘揚佛法于天地之間。后世有人評論說,這是曲加·登巴澤仁為了鞏固自己統治的帝王術,卻有人說,這是曲加·登巴澤仁的佛教情結,也有人說,這是一代土司的文化良知。
真應了那句話,千秋功罪任爾評說。
然而,曲加·登巴澤仁力主創建的這座印經院,卻把有史以來的最大榮光爭取到了這塊土地上,這是德格對后人所稱的“康巴文化”、康藏文明薪火相傳的最大貢獻,這也奠定了康巴德格與衛藏的拉薩、安多的夏河三大藏文化中心齊名的地位。在藏地的三大方言中,德格話成為“康方言”里的標準化語言,在冥冥中和這座印經院究竟有沒有一點聯系?想來,它起碼發揮了強化的作用。
印經院的出現并不是偶然,印經院的發展延續則是一種必然。
公元838年,佛教在西藏經歷了一次大劫難。在朗達瑪的瘋狂中,佛教典藉被焚,僧侶東逃西躲。他們中有的人居然在德格找到了可以避難的廟宇,找到了一處可以傳播佛教教義、傳播衛藏文化而相對安寧的凈土。在其后一個不長也不短的歷史時期中,德格之地,佛號披野,高僧輩出,他們傳播佛法,誠心建寺。德格的土地上,藏傳佛教的“五大教派”都有了自己的寺院,都擁有自己的信眾。
而到了曲加·登巴澤仁主政時,德格的富裕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曲加·登巴澤仁建造的印經院,把散落在民間的佛教經書木刻版本聚集起來,如有破損、殘缺,又組織人力重新雕刻。有一個著名的傳說:為了雕刻的質量,他讓匠人用自己刻好的經版插入裝滿金沙的皮口袋里,抽出后,那些金子就是工錢。于是,匠人們在雕刻經版時格外努力,格外用心。經版雕刻深,那怕印刷的次數多,也能保證印刷出來書籍的質量。以致,有個沒有到過德格、名叫大衛·麥克唐納的美國人在他的著作《旅藏二十年》里說:有一付為《甘珠爾》專設的鐵板,這東西保存在喀木地區的德格地方。
有信眾的擁護,加上土司的權威和財力使曲加·登巴澤仁組織的這項不朽工程能夠不斷推進,直至數代土司。曲加·登巴澤仁當年可能沒有想到,他所創建的德格印經院,成為了一處藏文書籍的集中保存地和重新擴散地。經書的本質還是書,而書就是一片土地上文明長存的火種,收藏書及其書版,終極意義仍然是為了廣泛的傳播,這種傳播從德格印經院出現到如今,一直不曾中斷。
曲加·登巴澤仁可能也沒有想到,德格印經院在事實上還成為了一處藏族歷史文化博物館,在將近27萬塊的木刻雕版中,保存有數千年前青藏高原上使用的、當時寫在貝葉上的文字“瑪爾巴”;有一千余年前藏文創造者吞彌·桑布扎所著的《藏文文法》;有以藏文、梵文、烏都爾文刻制定的《般若八千頌》;有在佛教發源地印度早就失傳的《印度佛教流源》等珍稀典藉。
曲加·登巴澤仁可能也沒有想到,德格印經院提倡、培育出的精湛木刻技藝,獨具特色的木刻雕版的保存方式,又讓德格印經院在不經意間成為了一處藏族木刻技藝的保存、弘揚地。
曲加·登巴澤仁更沒有想到,他的這一舉措,讓后來的普通人們在眾多的土司名字中只記住了他的名字。
德格是一塊包容的土地,印經院就是一種體現。
雖然是以保存佛教經書刻版和印刷經書為前提,但是德格印經院珍藏的典藉遠不止佛教內容,從佛學理論到天文歷算、醫藥學、詩賦文學、歷史哲學、繪畫藝術、音樂辭書等諸多領域都有著作保存。現在有好多人都不知道的一個細節很說明印經院的性質,在印經院初成的年代,就印制了一批書籍,主要是《甘珠爾》、《丹珠爾》兩部佛學典藉,同時印制了《四部醫典》一書,在書的刊后里有如下一段文字:“德格·登巴澤仁,一片虔誠,為眾生利益,推廣醫學。第十二熱窮之水牛年于更慶大殿”。這一年,是公元1733年,是德格印經院開建以來的第四年。而當后來的研究者在印經院的木刻雕版中發現了記錄藏族音樂類似“五線譜”的刻版時,在“工巧明”類的典藉中發現機械制造原理時,人們終于意識到把德格印經院當作純粹宗教產物是一種偏頗看法。有外來的人說,這其實是座“印書院”,這也許比較公允,因為這與德格民間對印經院“巴孔”的簡稱有暗合之處,民間稱為“巴孔”其意似為“書籍的房屋”,而不是專指經書。
在當時的高原上,因為機緣巧合,佛教的傳播成為文化交流的媒介、成為了先導。生活在德格的人們對佛教的真心信仰里也有對文化景仰的因子,佛教是一種文化現象而絕不是文化的全部,德格對此也許早有認識。因而對于一切外來的文化,遠離衛藏沒有光環的德格同時也沒有浮囂,以虔誠之心歡迎擁抱了來自內地、來自西藏的文化,以一種大氣和兼容并蓄的大度,讓涓滴匯成大海。德格顯示出超強的沉淀力,在一片神秘的山谷里修煉出了驚煞世人的深厚文化蘊藏,而隨著時代的推移,顯現出了一種可以稱為文化霸氣的氣質。
文化的生命力來自生活,來自永不停頓的發展和創新,而文化的交流必然孕育創新,康巴文化有如今的氣象,沒有人為的努力完全不可想象。于是,就如群星在空中閃耀,當年,德格這片土地上學者云集,人才輩出。也許,他們在世人眼里,都是佛的門生,是傳播佛法的高僧大德,但是他們生命的本質、他們生命的意義,就在于他們都是文化的創造者,他們身處崇山峻嶺之中,卻有飛越蒼穹的渴望。德格寧靜的環境,讓他們深入運思,使他們專注體悟,讓這些才思橫溢的學者,以他們的坦誠和透徹穿過了時空來與今人展開對話。
這些有些拗口、顯得生疏的名字,其實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創造和見證者,而他們自己已經成為了后人們須仰視的一座座高峰。司徒·卻吉迥勒、貢珠·元登喜措、降央·青則汪波、降央·洛德汪布、甲色·彥彭塔耶巴珠、吉美·卻吉汪波、顏嘎、年昭、覺木旁·降央郎吉降措、甲查、尼麥·曲吉翁波、通拉澤翁,等等,等等,他們的著述,除開闡述佛教理論,還涉及到如今所說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和許多方面。這些先哲們的研究和思想推動了藏文化、尤其是康巴文化的發展,其深刻的影響早已超出了青藏高原,成為人類文化重要組成。他們的許多著作不僅是德格印經院里獨有的瑰寶,而且一直發揮著溝通、聯接衛藏地區、聯接內地的作用。
如果說,德格因為有了印經院,才讓德格擁有了以文化雄視康藏、領袖康巴文化的底氣,那么這些文化巨人,則是在經意與不經意間占據了文化的制高點,因為無論是何種文化都需要相互學習,都需要不斷創新。他們的高明在于,引來外來文化的同時,又傳播這方水土特有的文化。不同文化在這里相互碰撞、融會貫通,經大師們的妙語和巨筆,把艱澀變成通俗易懂,又讓天地萬象上升到了哲學高度,如滋潤草木的山泉,漫長的歷史過濾、沉淀,形成的德格獨有的不可復制的文化風韻,悄然而長期地浸潤德格這片土地,成就了德格既作為佛教圣地、又作為康巴文化一個中心的地位。
也是因為有了他們,德格才成為了唯一德格。
是悠悠的歷史讓德格有了文化的深厚,是高山大河的阻隔又讓德格成為相對獨立的民族文化、民俗單元,處于封閉中民族傳統文化曾一度仿佛凝固。遙想曾經的輝煌,發思古之幽情神往而又失落,身處唯一德格的寂寞中,幸好還有思索和夢想。
現代社會信息密集,溝通傳遞快迅簡便,這當然是進步。然而,現代社會的尋常模樣卻是把信息當作了文化的全部。德格和德格印經院,在忙碌的現代人眼里,只不過是曾經文化的里程碑似的象征。試想一下,僅是整理德格印經院的書目,一大群人就在木刻版和書叢中默默一干就是十幾年,而人的一生有多少個十幾年?這還僅是書目,書目拿來何用?一時半會兒還真不好回答這樣的提問。
德格應該如何從深厚走向寬廣?如何既不被現實的浮華左右,又能與現代和現代文化接軌?德格的山還在,水還在,相信屬于德格的文化精魂還在。德格的上空一定有超越時空的、開啟人們心智的先知者的靈魂、還有永遠不會放棄追求的藝術靈魂在尋找落腳地,卻不是輪回意義上的重生,而是按照事物發展規律的一種螺旋形升騰后的新生,德格在等待新一代的文化智者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