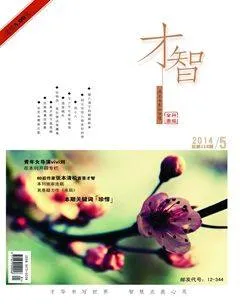我在美國所發現的中國
加藤嘉一
1
2012年的夏天,暫別中國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國波士頓的土地。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國生活,一無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時。
飛往美國的幾個月前,我開始找房子。我在波士頓一個人都不認識,就只好間接地找。我毫不猶豫地通過中國的人脈,找到在哈佛工作的一名中國先生,具體協助我在哈佛開始生活的則是在哈佛讀書的一名中國女子。到達的那一天,他們專門來接我,還在哈佛廣場請我吃飯。這或許是在華十年的積累,很溫馨,與十年前第一次抵達北京時截然不同。
與兩個中國朋友分手,安頓下來后,一個人溜達溜達,我進了一家室外啤酒屋。在北京生活期間,我經常買一瓶啤酒,在街上邊走邊喝,邊喝邊想。這次也習慣性地買了一杯啤酒帶出去,那是波士頓當地的Samuel Adams,喝了一口,特別爽快。一個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樂的瞬間。
下一刻,突然有兩名白人警察走過來,對我說:“小伙子,你在這里干什么?”我不是沒聽懂他們說的英文,而是沒有理解他們表達的意味。
我把在北京生活期間遇到這樣那樣麻煩時老用的招數拿出來,保持冷靜對他們說:“怎么了?我違法了嗎?”
他們倆互相看了一眼,帶著微笑卻嚴肅地對我說:“是,你違法了。”
后來才知道,在美國的公共場合喝酒是違法的且要受罰的。他們說這是法律,是不可以違反的。我在中國期間學會了討價還價,或隨機談判的技巧(這是我在日本的18年期間想都沒想過的),禮貌客氣地對他們解釋道:“警察先生,很抱歉,這是我抵達波士頓的第一天,對這里的規矩一點不熟悉,從今晚起我一定會注意的,所以請原諒我一次好嗎?”他們互相看看,帶著一言難盡的笑容,似乎放棄了對我的盤問。“好吧,就這一次哦。你記住這次的教訓。祝你在美國愉快。”
帶著莫名其妙的感覺與對中國的一點懷念,我從中國來到美國的第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2
2013年7月4日,美國的國慶節。
我在波士頓,跟平時一樣沿著Charles河邊跑步。
突然被堵住了。路被封了,我問警察先生憑什么,他說是“因為國慶”。我心里想:“哦,在美國國慶的時候路也被封的。”我卻沒想太多,這是生活,而非政治。
于是我繞路從劍橋區過河跑到波士頓區。藍天白云,到處能聽到慶祝的槍聲(非鞭炮),我內心進一步產生“這里是美國,而不是中國”的直覺。在河邊遇到了我很熟悉的日本一家人,孩子們也在。我對夫妻倆表示問候。孩子們正在唱國歌,美國的國歌,還把右手緊緊貼在胸部上。
他們唱完國歌,來跟我說聲“你好”。我表揚長子說:“你會用英文唱美國國歌啊,你右手的姿勢很酷,很地道哦。”在波士頓的公立學校上小學的他(12歲)有些害羞地回答說:“哦,每天早上在學校里要唱的,自然就記住了。”
在我看來,美國社會看得見摸得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國旗多。不管是平時還是非常時期,國旗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當地居民既在乎又不介意,自然地面對與國旗共存的現實。而且,美國人在國歌與國旗面前的態度似乎是戰略統一的,至少我接觸過的人里面沒有一個人對此持有消極或負面的態度。他們就是認為自己的國家很偉大,值得認同和敬仰。
想想中國的情況。依我的經驗,中國街頭的國旗遠遠沒有美國多。在天安門、黨政機構、邊境等關鍵的地方都有國旗掛著,但談不上夸張或過分。中國人在“國”字面前的態度既不同于美國,也不同于日本,卻兩者兼有。
來了美國一年多,迄今為止,我所發現的美國社會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愛國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有機結合。如前所述,美國公民對美國這一“國家”的認同度與忠誠心是毫無動搖的,唱著國歌,舉著國旗,365天,24小時,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國”字。但這一注重“愛國”的風氣卻不造成對個人主義的忽略與壓制。美國人的公私觀是清晰的,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該參與的公共空間,該保護的個人空間,兩者之間的界限在哪里,每一個公民都有著很清楚的認識。比如,我在美國跑步的時候(尤其在鄉下),要格外注意,要慎重確認自己跑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煩了,人家認定我在侵蝕他的私人空間,就會舉報。
3
我在哈佛切身體會到“中國”在走出去,美國當地的師生們對“中國”也頗有興趣,會主動跟中國人打招呼,進行交流。我在中國將近十年的經歷是一種福利,能夠給自己帶來圍繞中國問題與西方學者拉近距離、走進圈子的機會;但作為一個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逐漸衰退,心情有些復雜。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間,美國政府因財政問題正在陷入政府關門(shut down)的危機。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員交流,正好聊到美國政府關門一事。我是第一次聽到“政府關門”的情況,表示奇特,對方則帶著嘲諷的語氣說:“對啊,我們本來要跟美國方面開會的,結果對方說因政府關門抽不出買機票的錢。我靠,怎么會發生這種事呢?我善意地說中國方面要不要幫你們解決出行費用,對方堅決拒絕,我就沒辦法了。真是的,美國哪里是發達國家啊!”
回到美國之后,我跟曾擔任過政府官員的一位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國官員的表態。教授嚴肅地回應道:“他表示失望是對的,美國的政府不應該那樣輕易關門,要考慮我們在國際社會的利益和信用。不過,從另外的角度說,我們的政府至少可以關門,有門關,比中國政府連門在哪里都搞不清要好一些。中美都應該相互學習彼此的優點。”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從美國公民的政治態度與參與上得出“在美國,政治歸生活”的初步結論。那么,對于中國人來說,政治到底意味著什么?這才是我真正關心的問題。
摘自《做人與處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