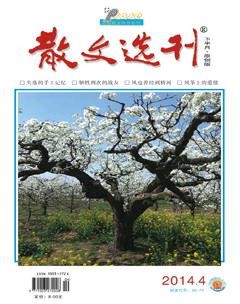守望街頭
蔡勛

打開手機,快速翻到“石摩托”這個名字。打過去,片刻工夫,一輛半新不舊的黑色重慶雅馬哈摩托停在我的面前,它的主人便是我稱謂的“石摩托”。
類似陜西一些農村群眾慣用的稱道:我找李公安,我找王稅務!幾年古城生活有感,就取用這個名字,送給每天開摩托送我上班的石師傅。
“石摩托”比我長兩歲,黑黑的皮膚,肌體粗壯,腰背寬厚,寸寸的短發,坑洼不平的臉透著強烈的滄桑感。戴著一架近視鏡,常留著看上去密匝的胡須。上身老愛穿那件紫紅色的夾克衫,滿是泥土的皮鞋天知道是什么顏色。他住在七里湖街道沿潯村,與水泥船廠不遠,那是他引以為豪曾經工作過的地方,離建材廠也不遠,他妻還在這個要垮不垮的廠里上班,按月領取八百塊錢的工酬。“石摩托”有一個不怎么愛讀書的兒子,讀完了職高又去浙江打工,去年底又受金融風暴襲擊回家,準備學學廚藝混口飯吃。曾經在江西機械工業學校就讀,擁有中專學歷,也許是讀書人出身的“石摩托”愛些臉面,一般不怎么跟我提及他兒子,每聊及家務,我就點到為止,不想讓他涉了面子,壞了心情。其實,平淡的哪里就不好?享受市井生活的裊裊炊煙,擁有平平安安的家庭生活,也不至于被功名利祿所累,專心跑自己的“摩的”,到站后三塊、五塊一揀,一天下來六七十元往懷里一揣。回家后,嘿嘿笑著交給把飯菜端到面前的妻子手中,男人的一份責任盡了,心到手到,這日子又差哪了!
這個城市文明程度也還有不盡人意的地方。凡開出租車跑“摩的”的,甚至開公家車和私家車的,總能看到在本來就不夠寬的城市街巷違規行駛、有章不遵的現象。心情可以理解,對于出租車、摩的、拐的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可規劃就是安全,就是幸福,就是最大的個人和社會效益。大家都能這樣想并這樣做多好!記得三年前我開始把自己交給“石摩托”之初,他老加著馬力跑,在拐彎抹角處,見交警不在就一踩油門滑過去,老被我奚落。現在好了,“石摩托”跑車中規中矩,不超不插,還把后座搞得干干凈凈,讓人放心搭乘。
說起跑“摩的”的事,“石摩托”告訴我,他十年前就從水泥船廠以七百元一年的廉價買斷二十年的工齡,揣著一萬四千元紅著眼睛回家,中專學歷證書上還記錄著他當年淌滿的淚水。一無錢,二無靠,理解國企改革的大氣候,卻不知曉往后怎么養家糊口。想過做生意,沒本;動過出外打工的念頭,又不忍心一家老小離了他這根柱梁。思忖再三,咬牙買了一輛嶄新的摩托,干起了這一行。守望街頭,守望歲月,守望生命,守望家園,日子在年復一年的守望中漸漸透些亮色。他說,跑得最遠是安徽匯口,來回六十公里。跑得最好的一次,一上午被人包車掙了一張紅錢。除了我,他還有一個常客,就是他家附近忙于建廟四處奔走的和尚,從他的口里,我大約知道一點,和尚三十五六歲年紀,貴州人,家窮從小就剃度,十多年前云游九江并在當地落戶,建了自己小小的廟室。近年政府建設城西港區,寺廟被迫征用拆遷,和尚對拆遷費不盡滿意,終日為此忙于交涉,并打算另起爐灶,在南郊一青山隱隱處落定。幾乎每一天,和尚都要坐上“石摩托”的車出門辦事,車錢總是比別人多,出家人總好說話,待人真誠,“石摩托”一說到和尚就有幾分動情,去年,他也動了心念,去廟里領了“居士證”,卻只會念誦一句“阿彌陀佛”。
當下,車子如螞蟻似地爬滿城市每一個角落,出門須百分之百地行走,不經意就看見交通事故,讓人缺失安全,缺失信心。城市的建設未曾停息,路是越來越寬了,可也越來越不夠用了,有車開,沒路開,這已是當下人的困窘。認真想想,為了每天上下班節省點時間,省錢搭乘“摩的”還真是一個較好的選擇。看來,“石摩托”真的是我生活中一個少不了的人,我不僅是他的客人,而且更應該算作他的朋友,畢竟,我坐上了他的車,就有一路話說。
守望時光,守望親朋,平凡的生命因之而覓得幾分趣樂。“石摩托”,好好守吧,用你的善念,用你的善舉,營造生活,營造生命。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