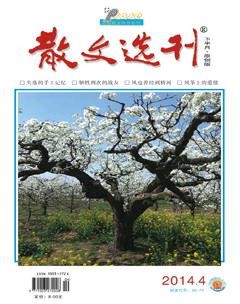失落的手工記憶
此稱

2月,在迪慶藏區是荒蕪的季節,田里的幼苗遭受著乍暖還寒的氣候,農人要費去很大工夫給每一株麥苗澆水,人們面對孱弱的莊稼,像是面對著保溫箱里的嬰兒。村子周邊的土坡一片荒蕪,牛羊在青澀的土坡上輾轉。
大雨過后,灰蒙蒙的田間在陽光里發出清亮的光。
阿主大媽推開新房墻邊的低矮土屋,里面的墻壁都被煙熏黑了,透進屋內的陽光照在墻壁上,發出油亮的黑色光澤,墻壁上橫著的木板就是壁櫥,木板上擺著很多落滿灰塵的古舊器具,有家具和農具,多半是用木頭制成,有木碗、木茶桶、背水木桶、木盆子、土陶茶壺、土陶火盆、皮制坐墊、三角鐵架灶、土陶酥油燈盞……
這里是德欽縣羊拉鄉薩榮村,作為坐落在偏遠山區的小村莊,這里還留有很多傳統生活的遺風,在緊鑼密鼓的現代化節奏里,退守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薩榮村的阿主大媽說:“我家是3年前蓋的新房,這間被熏黑的房子是以前住的。新房子落成后,里面的所有東西都是新購置的,有些以前用的東西被燒了,或者丟了,我對這些老家具和農具有感情,就空出這間暗房留了下來,每當想念家里的逝者時,我會待在這里,看看這些安靜的物什。”阿主大媽家的這間收留著古器具的暗房,在嶄新的新房子面前像一間博物館,從新穎別致的新房里,走進那間暗房,像是走進另一個時空,給人一種怪異的錯位感。
上世紀90年代以前,薩榮村和很多邊遠鄉村一樣,過著古樸的傳統生活,這里的多半東西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大到民居建筑、小到家具農具,都是人們在長期的生活經驗里摸索研制的。這些手工器具種類繁多,農事方面有水磨坊、舂青稞石器、木制犁具、打麥木桿、斬穗木器、鋤頭、一種叫作“薩巴”的木制鋤具、施肥用的竹簍等,家具方面有木制水桶、木茶桶、木碗、木蒸鍋、鐵制灶架、木盆子、土陶茶壺、土陶火盆等,生活用具方面有“薩炯”(花色羊毛毯子)、“彌森”(軟質帶毛毯子)、“斯巴”(壓制羊毛睡墊)、“布董”(羊皮褂子)等,總而言之,生產生活里的多半用具都是手工制品,雖然與冷機器時代的精細做工相比,這些老東西的做工顯得非常粗糙和隨意,但在那些蠻荒年代,這些都給簡樸的生存狀態帶來過極大方便,是凝聚村人古老生存經驗的智慧結晶。“手工”引發了源遠流長的鄉村文明的萌動。
而二三十年后的現在,有些人開始意識到延續的意義,一些村人說:“這些放在墻角的舊東西讓我想到從前,真好!”丟棄這些就是斷除過往,斷除自己唯一的精神和情感退路。在古樸的時代,村人對電器和不銹鋼的渴望是狂熱的,他們已經受夠了被煙熏黑的生活。笨拙的三角鐵架,就是家里的火灶,人們把柴火堆到鐵架下進行炊事,久而久之,整個房壁都會被煙熏黑,在墻壁和房梁上積出厚厚的煙漬。人們坐在青煙四散的灶火邊,流著淚水吃著飯,不是因為生活艱苦,是因為眼睛被煙熏疼了。人們對這種生活條件有些厭煩,急于擺脫。新世紀初期,各家都有了不菲的經濟收入,腰包撐鼓了,村人深藏在心底的生活理想可以實現了。爭先恐后拆著房子,爭先恐后購置家具,人們先把家里的三角鐵灶搬了出去,換成做工精美的鋼皮火爐,彌漫在房內的煙不見了,再也不怕房壁和家具會被煙熏黑了。就這樣,隨著不斷購置的新家具,那些老家具一個一個被請到僻遠的山洞里,暗黑的房間里,甚至付之一炬。而在薩榮現代的生活里,還有一些“老東西”被村人使用,有經得起任何考驗的現實價值,其中最典型的是“薩炯”。薩炯是一種純手工的花色羊毛毯子,在村里,幾乎每家都會有三四條。這是農村居家必備品,不管家里買了多少棉被和毛毯,薩炯依舊被村人看成是至寶,在以前,薩炯甚至是衡量兩家人貧富差距的重要杠桿。
在薩榮村里,還有很多人會紡織薩炯。57歲的阿主算是薩榮村薩炯紡織技藝的鼻祖,上世紀70年代大集體時期,阿主是生產隊的紡織員,她說:“我是從鄰家的一位奶奶那里學得的紡織術,那時在其他人看來,我簡直算是現在的‘國家工作人員,我的勞動算是很輕松的,一個月能織上兩三條薩炯,然后交到生產隊,可以掙到比其他人更多的工分,那時的很多紡織用具都是自己織的。生產隊里會有馬幫,去其他地方以糧食換取一些羊毛,拿到村里讓婦女們開始粘毛,捻成毛線,染色后,開始紡織一系列用具,包括睡具、馬背墊、衣服都要自己編織。在薩榮村里,現在還能見到一些由薩炯裁制的藏裝和雨衣。”說到薩炯的紡織技術,阿主大媽的臉上洋溢出自豪的笑容,她說:“在我們村里,很多人的紡織技術都是我教的,現在我老了,身體不再像以前那么靈活,一年紡織一條都會覺得吃力,紡織薩炯是個復雜的工作,從剪羊毛到編織毛線,制作織機,一般情況下,4個多月才能織得一條。以前在勞動之余著手紡織,會有很多小姑娘圍攏過來,然后請求傳授她們紡織術,村里的姑娘,如果掌握紡織術,會被年輕的小伙看好,成為萬花叢中一點紅。”
阿主的老爸以前是個牧人,常年上山放牧,老人在山上時,會制作一些木頭家具聊以消遣,老人最拿手的是制作木盆子和木箕、水桶、家畜的食槽等,阿主說:“每年都要到山上給老爸送東西,送東西時能帶回很多木制家具,比現在買到電冰箱還高興呢!”有一年,阿主老爸到離村20里遠的山里放牧,有一天清晨,他帶著斧頭上山砍可以制作家具的木頭,到山上時,他發現一棵長在陡坡上的杜鵑木,看上去應該可以做個很好的馬鞍,于是他撥開灌木,一斧頭砍下去。砍了幾下后,斧頭被橫在杜鵑木前的灌木鉤住,不慎砍到自己的腳,開了好大一個口,血從傷口汩汩流出,阿主老爸連忙從衣服上撕下一塊布條繃上,血還是流著,他便從地上抓來一把灰土撒在傷口上,然后匍匐著走向牧地。這時阿主正好上山給老爸送飼料,到牧場時已是傍晚時分,牛都及時歸圈了,站在自己的拴柱前,卻不見老爸,石砌小房的門口掛上一條薩炯,又用一些粗大的木頭叉擋著。阿主一下急了,跑到牧地上四處呼喊,也不見老爸。她哭著走回村里,跟村人說老爸不見了,村人一下奔走相告,聚集了100多號人上山尋找。當他們再次來到牧場時,還不見阿主老爸回來,都以為他死在山里了,可能是跌于一處懸崖,又可能遇上野獸了。全村人在山里分頭找,一邊喊一邊找,直到深夜時,還不見阿主老爸,有些灰心喪氣了,斷定阿主老爸已死,掉下惋惜的淚水。當凌晨全村人都聚集到牧場時,還不見阿主老爸回來,親戚都哭成一團了,把阿主老爸牧房里的東西馱回村里,把牛全部趕回村里,村子被死亡籠罩著,阿主家里開始操辦后事。過了第三天,全村人聚集到阿主家里料理后事時,阿主老爸卻一歪一瘸地走進家里,一進家門就是對家人一頓呵斥,說是不是瘋了,把牛和東西帶回家。全村人一陣驚怵,都瞪大眼珠子看著阿主老爸,最后在一陣笑聲里結束這場誤會。直到阿主老爸過世前,每逢聚會,村人都以此事說笑阿主老爸和家人。阿主說:“簡直像是看見已死的人復活,之后對老爸百倍孝敬,第二年就給老爸織了一條薩炯,這條薩炯現在還在,跟了我老爸20多年,我老爸經常說,在山上,吃的可以沒有,隨便進一次山也不至于餓著,但絕對不能沒有薩炯。”聊起薩炯,阿主一臉的專家嘴臉,她說:“薩炯既有良好的保暖功能,也能防水,在民間傳說里,聽說它還可以避夢魘。”
大集體時期,匱乏的物質條件讓人們飽受饑寒,那時封閉的山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買到,阿主學得紡織術后,先后給家里的每一個人紡織了一件薩炯二次裁縫的上衣,這些上衣阿主家人一直穿了20多年,到現在有些上衣的主人已經過世30多年,薩炯上衣還擺在阿主家的衣架上。以前沒有質地綿軟的毛毯,人們就寢時只蓋一條薩炯,薩炯只適合做御風保暖睡具蓋在后層,因為它質地非常粗糙,摸上去像是在摸豬鬃。阿主說:“不過那時沒有其他辦法,薩炯是最奢侈的,蓋上后睡一陣就暖和了。”
20年前,阿主的丈夫猝死于一個傍晚,給活潑的阿主帶來難以承受的打擊,阿主持續難過了一整年,人立馬憔悴下來。到第二天,她重整放在角落里的木織機,開始捻毛線……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紡織薩炯上,她說:“那一年我除了吃飯睡覺,基本都在紡織薩炯,它能讓我忘記很多,把注意力和情緒放在手頭的針線上,有時候在紡織間隙,會突然掉下一連串的淚珠,我甚至把晚上的時間都用在紡織工作上,那一年我紡織了四條薩炯,現在都放在衣櫥里。”打開凌亂放置的睡具柜,三條被洗好的花色薩炯被阿主大媽疊得整齊,放在最上面,當她看著這些薩炯時,眼角露出溫柔而又靜謐的笑意。
上世紀60年代,村里的魯榮老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捕后押至麗江勞改服刑,他媽媽哭著請求押送人員給他帶上一條薩炯。魯榮老爺在麗江服刑了16年,在這期間,他學得正骨法、煉制技術等多種實用技藝,回鄉后他給村里的病人看病、正骨,村里的農具基本都出自他的小煉坊里。魯榮老爺說:“時代發展了,人們干活都比以前方便,我的小煉坊早在幾年前就歇工啦,被我孫代人鏟平后建造了一個小的洗澡室,現在沒人會學這些東西了,因為不實用啦!”魯榮帶我去看他的冶煉工具,有大錘、木制吹氣筒、大鉗子等等。不知道這些東西能留到什么時候,誰也沒有具體清晰的理由,讓村人對這些東西視若至寶,它們在锃亮的不銹鋼家具和上著鮮亮色彩的農用器械面前低下了頭。正如村人在另一種常年相望著的生活面前低下了頭,只有時間,會讓人們意識到這些東西除了現實價值以外的存在意義。古家具和農具們,跟著一群群老去的人們,在熱鬧的小村子里走向邊緣,與之一同走向邊緣的,還有它們所承襲著的生存記憶、生活習慣,乃至思維方式或生存理念。
“文化大革命”時期,阿主大媽還是個小姑娘,在“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的政策背景下,全村多數人加入“革命運動”,把山間小廟里的宗教藝術品、把自己家里的工藝品毀于一旦,只有少數東西被有心人藏到山里,藏到洞里。這種無知運動的跡象在薩榮至今隨處可見,在老學校,或在山廟里,到處都是摧毀的爪痕,山廟里精美的壁畫被熏黑,山廟的柱子被斧頭砍,并用灰泥在壁畫上刷出一塊,寫上正楷的時代標語。魯榮老爺說:“‘文化大革命之前,薩榮村的薩帕山廟里有很多宗教藝術品,還有一尊高達20多米的泥塑佛,壁畫、泥塑藝術品、宗教法器都是一流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人們瘋狂地摧毀著一切,如抱抗議態度,還有被公然批斗,批斗方式是把反革命分子吊在眾人眼前……”這是多么大的劫難啊,讓歷史在無知中自絕,沒有物證的歷史,都會變成傳說,特別是對一個彈丸小村來說,拿什么去證明自己的生存歷史?1990年,薩榮村民自發組織,開掘被摧倒的山廟,出土了一大批銹跡斑斑的宗教工藝品,有泥制佛像模胚,有各種宗教法器,被村人堆到山廟的一角。到現在,據村人透露,已經少了很多了,有些被丟在地上,被踩碎,有些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對這些東西的管理很零散。只有懂藏文的“安曲”才會提醒村人保護這些東西,他們似乎發覺到這些東西的文物價值。如今,從一個家庭到山廟,很多老東西都在人們灼熱的現代意識里搖搖欲墜,時間會過去,生活會改變,這些都毋庸置疑,并且值得稱贊。但是,對這些東西的無視和冷淡,就是對自己生存歷史的無視和冷淡,多年之后,會不會都變成一群精神嬰兒?這是值得多方留意、關乎鄉土精神文明構建的一個大問題。
2月22日,一輛白色的轎車駛入薩榮村,車子到了村中央時從車里下來一位中年男人,帶著墨鏡,挨家挨戶收購“古董”,村人現在都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東西算是“古董”,老板耐心地解釋說:“就比如我去年在你們村里買的骨制桿秤,一些老的,做工精細點的都可以。”于是有一家人出售了一條薩炯,賣方家人在近半小時的估量后,開出600元一條的價格,中年老板摸摸胡須,帶著一些照顧性的口吻答應收購了。老板走后,幾個村人又湊到一處討論薩炯價錢,有人說600元算高,有人說不高,說高的人說薩炯反正沒人買,600元不錯了,說不高的人是從成分上分析,比較細致。阿主大媽說:“薩炯從剪羊毛、捻羊毛、編織毛線、染色、紡織,一般都要30多天時間。”這樣一算,600元確實少了,但是很多類似的東西,在民間的交易里都有尷尬的價值定位。
薩炯在以前用處廣泛:子女出嫁時,薩炯是上好的嫁妝;親朋送禮,薩炯也是最好的禮品。在機械紡織品充斥的現代鄉村,薩炯也依然被村人視若至寶,它的生命力第一源自它的實用性,第二也是源自它獨特的保暖功能和便攜功能。薩炯重量一般有2公斤左右,但折疊起來,可以挎在腋下帶走。因此,薩炯一直是牧人和外出做工者的必備品,牧人會在遷場時把薩炯當作牦牛的背墊,然后上了木鞍后馱運東西。至今,每年的蟲草季,村里的年輕人上山采蟲草時,薩炯仍是每個人不可缺少的東西。在高寒潮濕地帶,薩炯兼備防潮、防雨、保暖等多種珍貴功能。在薩榮村,如今也有很多人會紡織薩炯,年輕的姑娘會在農活清閑時,開始著手編織,會有更年輕的姑娘前來學習。魯榮老爺說:“薩炯因為它的實用性強,村里很多年輕姑娘愿意學,但其他的木制家具和農具現在會制作的越來越少,再過些年,年輕人可能連個木犁都不會制作了,不過現在還好,什么都可以靠機器,但機器也是要運氣的,現在買進來的多半問題百出,比如一個犁地機,隨時要拿到城里維修換件,幾年下來,維修費都已經超過購置費了。”
在現在的薩榮,到處看到敞亮的客廳,锃亮的家具,以及接近西式風格的室內設計,在對村民現有生活之便利的驚嘆之余,似乎少了些什么,作為一個生長在這里的人,對這里的一切感到一絲陌生,找不到更多留在這里的記憶線索。在冷機器時代,很多東西不能承載太多故事,走到田間地頭,只聽到犁地機的馬達聲,聽不到農人悠揚的犁地謠,聽不到悅耳的打麥歌、聽不到……進步是需要代價的,我們不能為了一己的懷舊和不痛不癢的審美需求,而要求鄉村一直保持簡樸的生活以供觀賞,但是,在一些自發的組織、覺醒,或有意的提醒、引導下,應該可以讓歷史和傳統延續到當下的生活細節里,與歷史保持一種聯系,才不至于迷失在毫無來頭的時間里。至于散落四處的手工制品,在效率至上的當今鄉村社會里,確實不再具備可靠的現實價值,但它們也有其隱秘的文化價值,能夠補償人們的一些情感缺失,也可以成為一種記憶或歷史線索。當我們在活到一個完全蛻變的新世界時,借此憶苦憶甜,在物質文明相對充裕的年代里,有必要留意這些難以把握的小細節,為使我們能有一個更適于生存的多重環境。
2月24日,薩榮村的年輕人安布打電話說,他有一個小DV,想拍個關于制作水磨的紀錄片,他打算請來村里的石匠,詳細拍攝從選石料到雕鑿磨盤、制作水輪、磨軸、構架引水道等所有制作細節。薩榮村有三個水磨坊,有些磨盤已經被磨成輕薄了,再過幾年,就會斷裂。現在每家每戶都有磨面機,但多半人家只用磨面機磨飼料,炊事面粉都用水磨來磨,村人曲品說:“水磨里磨出來的味道很好,有很誘人的麥香,沒有菜也能下口;磨面機里出來的面粉,像在吃灰泥土,一點味道都沒有。”村人安布的想法是覺得應該把制作水磨的技藝留下來,不然現在村里只有一人會制作磨盤,而水磨在這個村子里永遠都不會過時。安布和村里其他幾個年輕人,還想把一些手工技藝拍攝下來留著,他們的這種自覺地對手工藝的重視,也從側面反映了年輕人對傳統手工技藝的新的認知和覺醒。
記得在一本書里有這么一句話:“在我看來,只有個體記憶優先于集體記憶,地方記憶優先于國家記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值得信賴的集體記憶與國家記憶,而這也正是鄉土記憶的價值所在。”新的生活正在鄉村脫胎而出,舊的生活方式已漸漸退幕,讓我們留住些什么吧,以便記憶、反思、比較、紀念,也給自己留條精神或文化意義上的退路和選擇。
責任編輯:蔣建偉